「我八歲。我殺死了一個孩子。」
在明媚燦爛的春天裡,一個小女孩犯下了駭人聽聞的罪行。這是南西.塔克(Nancy Tucker)的第一本小說,《春天的第一天》述說了一個年幼殺人犯的故事,黑暗、驚悚且扣人心弦。擁有心理學背景的她,用精準細膩的文字摹寫年幼女主角克莉絲的心理狀態,極有說服力。讀者或許對克莉絲的「至惡」產生恐懼與不安,但也不禁同情她幼年時期的遭遇。
透過過去和現在兩條時間線的交錯,南西.塔克為我們展示:「她是一個魔鬼,但她也是一個母親」的複雜圖景。並且細細追問:若你的母親不知道怎麼做母親,你該如何愛她?而一個殺害孩童的兇手,是否有資格成為母親?她會怎麼做一個母親?
《春天的第一天》作者南西.塔克 © Edward Gr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皇冠文化 │ A=南西.塔克(Nancy Tucker)
Q:您的第一本小說《春天的第一天》甫出版便深受矚目,想請問您的寫作起點是什麼?您期望藉著這本書帶給讀者什麼樣的思考?
A:我寫《春天的第一天》靈感來自幾個實際的事件。在這些案件裡,孩童殺害了其他孩童,理解孩童做出這種可怕事情的背後原因非常有意思。我也很感興趣的是,做出這種事情的孩童會長大,他們不會停格在那個時刻。我們對他們的認識就是罪行發生的時候,但他們會繼續生活,隨著時光流逝,我好奇他們會如何度過這些歲月。特別是這些孩子長大後有了自己的小孩,他們的親子關係會是怎樣?
至於我想帶給讀者什麼樣的思考,我希望讀者在遇到這種案件的時候,不要秉持非黑即白的想法。因為我們很容易陷入「一個加害者/一個受害者」的思考模式,但這是處在灰色地帶的案件,其中可能牽涉到多位加害者與多位受害者。我們不見得只能覺得一方可憐,而對另一方憤怒。也許在思考上多一點彈性、多一點諒解,是我希望鼓勵讀者的。
Q:「春天的第一天」這個書名很有意思,既象徵了燦爛美好、萌芽新生的春天,但最殘酷的事情也在春天裡發生。而書中主角們走過漫長的歷程,彷彿歷經了飄雪的寒冬,再次盼到了春天。想請問您命名的初衷?
A:書名我想了滿久,我不喜歡想書名,我最討厭想書名了,感覺要想出一個好書名壓力太大了。但我覺得這個書名很適合這本書。它點出了這本書的重點,本書一開始的確展現出某種燦爛與希望。我想這也能鼓勵讀者在思考上多一點彈性,可以用不同的眼光觀察同樣的狀況。
而在克莉絲的故事裡,一開始的確很黑暗,她有過很黑暗的經歷。但隨著她長大,她有了茱莉亞這個身分,一切開始有了希望,特別是她與女兒莫莉之間。我不會透露太多內容,但在結尾的地方充滿光明與希望,的確就是我希望這個書名帶出來的感覺。
Q:《春天的第一天》裡,您用了小女孩的視角和口吻,來描述她人生崩毀的第一天,深刻地刻劃角色的心理。想請問您專攻的心理學研究對小說創作有什麼影響?
A:這是個好問題。我大學念的就是心理學,也正在受訓成為臨床心理學家,我在心理機構工作,所以可以說心理學是我的另一種生活、也是我的正職。心理學的確明顯影響到我的寫作,因為我對人的心理運作機制非常感興趣。我跟許多有心理障礙或創傷經驗的孩童與青少年合作,因此對創傷對於孩童的影響很有感觸,這些掙扎也影響到他們長大之後的人生。心理學讓我能精確地描寫出人內心的狀態。
Q:那麼您選擇小女孩和成年女性兩種視角交錯敘述的理由又是什麼呢?
A:我本來不覺得我會寫出兩種視角的敘事,我一直以為我只會寫克莉絲或茱莉亞的故事。後來在編輯的過程中,我才把這兩個故事交錯在一起。我猜我一直想把這兩個部分的故事說好,因為我很好奇克莉絲小時候與她長大之後視角的改變,這兩個部分一起寫有助於步調與張力。
我覺得這兩個聲音互補搭配得很好,從克莉絲的角度看一件事,再從茱莉亞的角度看類似的事情,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她的成長與改變,這兩種敘事一起搭配的確很有幫助。而我們又能從整體的角度,看到克莉絲與茱莉亞的聲音非常不一樣,長大真的協助她改變,磨去了她尖銳的稜角,讓她成為能夠在世界上好好運作的一個人,當我們讀到她與女兒茉莉之間的互動時才會覺得充滿希望,因為我們看到她的成熟,知道她現在可以成為一位母親。
Q:母親和女兒的關係是小說中的重要主題──該怎麼做才是一個好媽媽?母愛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小說透過克莉絲很多的自我質問,以及母女的日常對話來呈現這些問題。想請問您如何思考母職、母女關係?
A:我覺得母親及母女關係的確是本書最主要的主題。對於這個問題,我沒有答案,我不見得是最適合回答這個問題的人,因為我不是一位母親,我是人家的女兒,所以我懂我跟我媽之間的關係,但我不曉得養育小孩子的感覺。我猜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想探索這種感覺與其中的焦慮感。如果我有一天成為母親,我會遇上哪些挑戰?
我覺得如何成為好媽媽是大哉問,不過我們能在茱莉亞身上看到好媽媽的某些特質:她犧牲自我,把女兒放在第一位,她很在乎莫莉的感受,她覺得莫莉是最重要的人,她覺得莫莉是一個個體,有自己的思想與感覺。
相較之下,克莉絲的母親就是完全相反的例子,她從來不把克莉絲放在第一位,她似乎不把克莉絲當成一個真正的人。所以我想,又回到前面的問題,我希望克莉絲與茱莉亞的聲音形成對比,比較克莉絲與母親相處的感覺以及成為母親的茱莉亞,特別是她與女兒莫莉相處的經驗。我想特別強調其中的對比,表現出成長與成熟以及從創傷經歷中走出來的主題。
Q:小女孩克莉絲是非常特別的女性角色,為了填飽肚子,她很擅長弄到免錢的食物吃,一般道德觀念對她來說比不上求生的本能;而也因為飢餓和憤怒,最終使她到了某種崩潰的臨界點。想請問您何以會塑造克莉絲這樣的角色?是否有原型人物存在呢?
A:的確,克莉絲很會保護自己,在本書一開始的時候這種本能的確壓過了道德觀念。我覺得這是很真實的狀況,孩童的確有保護自己的強烈本能,特別是遭到忽視的孩童,他們必須發展出這種本能,不然根本活不下來。我們可以看到克莉絲擅長從別人身上取得資源,得到每天活下來的所需,如果她不擅長,她很可能就會死掉了。因為沒有人讓她得到應有的照顧。
說到她很堅強,她這個角色的靈感來自我接觸過的一些青少年個案,他們在幼年時期經歷過困苦,因此做過一些可怕的行為,所以有一些我從心理學工作裡放進書裡的元素。前面也提過,我研究過一些犯下同樣罪行的孩童,所以她雖然是虛構的角色,我希望她也非常真實,而真實的孩童也有過類似的經歷。
Q:《春天的第一天》可說是一個「餘生」的故事──既是被捕後在監獄存活下來的「加害者的餘生」,也是承受母親虐待(從生理到心理)而活下來的「受害者的餘生」。在尖銳而衝突的設定背後,我們讀到了寬容和同理心,與發生傷害之後,承認救贖的可能。您如何看待「救贖」呢?
A:又是一個大哉問。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對救贖保持開放的態度,我不希望這本書譴責克莉絲,或是完全原諒她,我希望能夠呈現出這兩種同時存在的可能性。讀者一方面會覺得罪行非常駭人,也能同理犯下這種罪行的孩童,思考背後的原因。
我們在茱莉亞身上看得出來她跟克莉絲是很不一樣的人,她看起來不像會威脅其他人,我猜也許這就是救贖的意思,因為她過起了贖罪的生活,其中的關鍵來自她在機構裡遇到的正面影響。所以對我來說,救贖的確是可能的,真正的救贖就是活出來的生命,並不是能夠提供別人什麼,而是當事人自己能夠體現出來的生命。
Q:想請問您為何開始寫作?是否有啟發您開始寫作的作品?
A:這個問題很有趣,我從小就讀很多書,但沒有人啟發我寫作。寫作並不是我的人生目標,我沒有辦法指出某本特定的書讓我想寫作,但我有很多很喜歡的童書。當作家對我來說有點意外,因為我寫的第一部作品《中間的時間:飢餓與希望的回憶錄》(The Time in Between)是關於飲食失調的自身經驗。那是很私密的作品,我寫的時候並沒有想著要出版,那只是個人的抒發。透過那次書寫,我才曉得我多喜愛寫作,之後我又寫了另一本非文學類的作品《那是人們開始擔心的時候:年輕女性與心理疾病》(That Was When People Started to Worry)。
寫小說是因為我很喜歡先前的寫作經驗,我也很好奇自己能不能寫虛構作品。那時我已經有書寫非文學類作品的經驗,但完全沒有寫小說的經驗,我想看看自己能不能辦到。我一開始動筆,就發現我很喜歡寫小說,我喜歡小說帶來的自由,充滿各種可能性。相較於非虛構作品,小說充滿彈性,我想朝哪個方向前進都可以。寫小說對我來說是很刺激的過程。
Q:在寫作路上,影響您最深的一位作家或是創作者是誰呢?
A:我可以想到幾位我特別喜歡的作家,我最近很喜歡奧戴莎.莫思斐(Ottessa Moshfegh)還有克蒂絲.希坦菲(Curtis Sittenfeld)這兩位作家的作品。我沒辦法說他們對《春天的第一天》有什麼影響,因為我是寫完初稿之後才讀他們的作品。
我想我受到愛瑪.唐納修(Emma Donoghue)的影響很深,她寫的知名作品《房間》,是我讀到第一本全部由孩童視角描述的作品,《春天的第一天》同樣有孩童描述的角度,也許可以說《房間》啟發了我。
Q:您的第一本小說選擇寫懸疑推理小說,往後是否還想嘗試什麼樣的類型創作呢?
A:有趣的是我在寫《春天的第一天》時,並沒有覺得自己是在寫懸疑小說。一直到進入編輯與出版流程時,我才發現這本書很適合這個類型。寫書的時候,我覺得我寫的是心理虛構或大眾小說。
我想我不會繼續朝犯罪與懸疑類型方向寫作,而會朝大眾小說的方向去寫。我目前正在寫的作品比較類似浪漫喜劇。不過我保持開放態度,寫什麼都可以,這也是寫小說這麼刺激的原因,可以從任何角度切入。
Q:最後,請您再和台灣讀者說幾句話。
A:我很興奮《春天的第一天》能在台灣出版,我希望你們喜歡這本書,我很想知道你們對這本書的感覺。我覺得這本書有解讀的空間,能夠提供讀者許多不同的思考方式。對於讀者的詮釋,我也抱持開放的態度。我覺得寫作最有趣的一點在於,看到不同讀者的不同感受。我很期待你們讀這本書,也希望你們會喜歡。
延伸閱讀



 《春天的第一天》作者南西.塔克 © Edward Grant
《春天的第一天》作者南西.塔克 © Edward Gra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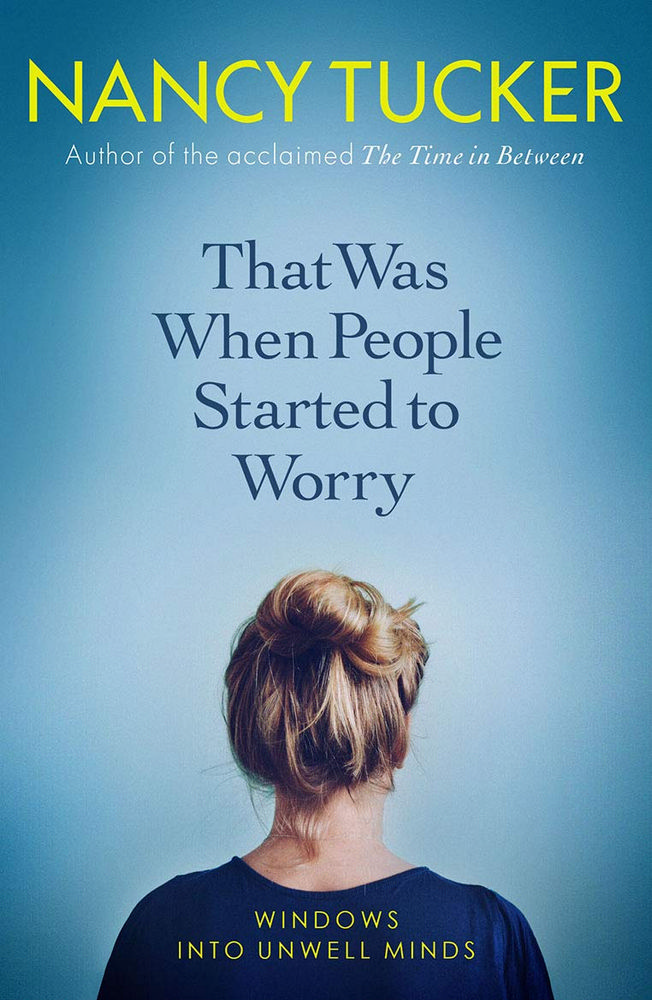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