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小說」並不是我特別研究過的專題——但陳育萱的《那些狂烈的安靜》,讓我止不住地想起,這個值得更多討論的文學傳統。
「學校小說」的新樣貌
台灣曾經一度存在過力度非凡的「學校小說」,比如收錄在洪範1985出版《茨冠花》中的〈花冠與茨冠〉(許台英著),經常被置於「人權文學」領域的林雙不——儘管對後者的語言是否過於直白,時有爭論,但不可諱言地,「大學女生莊南安」這七個字及其留下的眾多作品,都曾作為無法忽視的象徵與文學記憶。在在提醒我們,在「家庭」與「社會」兩個場域之間,「學校」不該是被輕易遺忘的時空。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從朱宥勳的《湖上的鴨子哪裡去了?》中,仍看得到對此傳統的重拾與致意。如果我們更細心一點,也可看到王文興的《剪翼史》,一定程度,正是全力暴露威權時代大學殿堂庸凡、虛幻與屈辱的文本。陳柏言的〈雨在芭蕉裡〉,雖是帶有牛刀小試感的短篇,但其中多樣的企圖與輻射,也確證了「返校」的大有可為。而啟明出版的《史托納》(約翰.威廉斯著)中,更是只以幾個教職員與學生的恩怨情仇,就構築出足以見證歷史與社會變遷的不朽經典。收錄在《那些狂烈的安靜》中的七篇力作,既與上述文學遺產交相呼應,也有迥然不同的成績締造。
〈彼端〉結尾的意象,令我想到「一個沒有自由的自由女神」——但主角仍高舉起手。那不是單純的反抗,還包含深刻的諷喻與精確的喊話。語言是直樸易懂的,感情是溫和真摯的,切入點卻將荒謬、悲憫與洞見,一併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
當代藝術與社會隔離的危機:再訪「監視器事件」
小說很可能是從「嘉義代課老師抗議裝設監視器」事件脫化而來。在原始事件中,新聞在老師自殺、校長辭職後,就淡出了媒體——儘管當時不乏「不能讓事情不了了之」的聲音,但也有不少失焦的討論。報導中,該名小學老師認為教室裝設監視器「違反教育意義」而辭職。在她的說法中,捍衛學生權益的意味大過對監控的反對(「如果是拍我,我會到鏡頭前面比個ya」)——我在看到當下,就感覺複雜。因為如果老師已能認知到監視器對學生的不妥,不可能完全沒想到「拍我」也屬不當,「比ya」的說法,應該是反映了降低衝突的意願與教師的弱勢處境——只有弱勢到一定程度,才會有委婉的必要。而根據教育部的說法,監視器的議題,其實是「已多次討論而無共識」。所以,這個事件想必也只是「冰山一角」。小說將背景從國小改成高中,老師也非代課,是剛考上資格的正式老師,雖然仍保留了一部分「職場霸凌」的痕跡,但在這大幅改寫社會事件的小說中,「校園監視器」現象,無疑是小說家更針對的靶心。而現實中的自殺,小說換了「黑色幽默」上陣。
但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陳育萱有效地「將當代藝術拖下水」。「批判監視器」幾乎可以說是當代思潮與藝術的主流。如果追溯更遠,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也已開章明義。然而,那麼多的論述,那麼多的作品,難道與校園竟是完全的「絕緣體」嗎?兩者老死不相往來地「動如參與商」嗎?社會是否已建立起新的隔離制度:一個世界流暢地訴說監視器的墮落,一個世界沉默地陷入監視器成癮症?除了監控的政治意涵,這「兩個世界」的鴻溝,難道就不是危機嗎?
接下負疚感,也接下隱隱的性欲
〈彼端〉,並不是《那些狂烈的安靜》中,唯一一篇貌似平和,實則凌厲的小說。〈人偶遊戲〉的首尾濃麗,中間卻疏淡——一個家傳紙紮業的大一女生筱棠,離家到東部求學,因為家庭經濟突然窘迫,在打工民宿裡,遇到謎樣的女主人與她對女生情竇初開的國中女兒星媛。故事有種鬼故事特有的鬆鬆感——「應該沒什麼好緊張反倒令人更緊張」。故事的表面看起來與邪教有關,但細讀之下還有其他。筱棠的表意識集中在不忍星媛的寂寞無依,但某次前去檢查星媛安危的夜裡,筱棠不但留下「過夜」,早上醒轉後,還懷疑兩人已有親密接觸。「以為昨夜睡得像蛹。」——小說出現這一句,其他時間裡,我們都以為「俑」字與筱棠家的「人俑」有關,筱棠也把星媛與人偶相比——這使得我們可能誤以為「俑」都圍繞在星媛身上——但這個「睡得像蛹」像是冒出的線索,突然指向了筱棠——「沒有知覺、不能言語」的「俑 / 蛹」其實也是她?
故事不只關於家教女學生是小拉拉,也關於「直女」既拒認又揮不去的同性情欲。結尾的一疊三唱,在極快的節奏中,就讓我們體驗到從負疚感的釋然,再訪與諦觀——頭髮間「燃燒過」的小紙片,不只是無法燒化的靈屋殘餘,也是「一夜結髮」,從「不信物」到「信物」的化身。這是我近來讀到最美又最有深意的段落。
陷落的世界與不陷落的人:致目睹兒們
在讀這些小說的過程中,「陷落的世界與不陷落的人」這句話,不時浮上我的心頭。
陳育萱攫住的,是一個「陷落得很快的世界」:父母不合或一方外遇、成績不佳或一場打鬥,坍方速度都是快的。目睹兒(目睹暴力的兒童)——未必直接受到暴力虐待,但直、間接接觸到暴力場景的兒童——應該是陳育萱小說中,最常出現的人物。
〈停留在一無所有的浮標〉中的朱冠群,父母鬥毆中,父死母入獄,在與同伴嬉遊時,仍會聽到母親的尖叫聲,是「具有侵蝕性的絕望」——這一篇還寫了三個青少年打「噴農藥」工的情景,在很容易被負面標籤為「高風險」的成長過程中,冠群保存著釣魚以及與同伴跑步的歡愉。
〈禮物〉中,因為疫情改成線上課程,也使身為老師的Dora意外目睹學生家中的暴力事件,而相反於一般以為老師就是無甚風浪長成的,Dora本身也是擦拭過父母鬥毆後血跡的目睹兒。在處理學生受傷同時,Dora也無法避免兒時創傷浮現——但她幸有救起過的小黑貓反來守護。
〈唯獨剩下安靜〉觸及的是更禁忌的一面,「我被迫成為那一幕的活標本」。如同〈彼端〉,這篇小說也不迴避與校園發生過的事件對話,但著眼點並非「拼湊真相」。它們有最好的「社會新聞小說」的特點——如同斯湯達爾的《紅與黑》或李昂的〈殺夫〉,只從社會新聞借取若干元素,在小說家認為值得注意的切面上,重新「說一個不同的故事」。在〈唯獨剩下安靜〉中,教師自殺與學生目睹牽涉的創傷是被關注的,但陳育萱賦予了悲傷更錯綜的結晶形式——那些再也無法支撐自我的人,曾是支撐他人的少數希望:無私指導音樂的同志學長之於芳伃,芳伃之於愛唱歌的原住民學生萬曉浪。陳育萱寫萬曉浪蓋著臉「哭」是「任宛如被咬一口的熱燙暖流沿著指節處一節一節地滑動」——曉浪不只「變靜」也「變慢變敏感」,這些都是哀悼中的人會體會到的「不同的身體」。
回到樹下的教育
所有的喪失幾乎都是喪失「另一個身體」,而再「壞」的身體,對生命來說,也是「好身體」——比如〈運途〉中「始終要依伴著楓葉鼠而冒犯教室威權」的國小女生,或是〈一閃一閃亮晶晶〉中,容易被側目的「星星兒」肢體語言——在情節上,這兩篇我們並不會覺得那麼不熟悉。但是,作者在轉譯「身體性遭遇」上投入的高度技巧與「身語言」,都使它們成為別具一格、意味深長的文本。
如果重新回到「學校小說」的尺度,《那些狂烈的安靜》還有幾個特別值得提出來的東西。在〈停在一無所有的浮標〉裡,少年並非真的不愛學習,但他們與學校的關係,經常剩下「跑給老師追」,這不是一般的「頑皮有趣」而已。對教育的「抵制融入」,作為「中輟」或「逃學」的相似身影,他們有更迫切的自我修復需求,那包括了我們在《學做工》中,可以看到的對「階級與教育」的討論,也包括了「階級」未必完全觸及的「關係匱乏」暴力——對他們身體處境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他們的「經濟資本」——或說「經濟無資本」。小說裡對此有非常細膩的紀錄,而這通常卻是教育體系不夠正視或率先歧視的層面,所以「追不上他們」。
建築師路易.康(Louis Kahn)曾定義教育是「一個不覺得自己是老師的人,與一個不覺得自己是學生的人,在樹下交換想法」,在讀到《那些狂烈的安靜》之前,我從未注意到「在樹下」這三個字的重要性。在陳育萱的小說裡,山、海、河流與動植物始終有強烈的存在感,大自然不是背景,它也是人的身體庇護與依附——陳育萱已將我們帶到了「樹下」,是時候,讓我們開始交換想法了。
作者簡介
1973年出生於台北木柵。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及視聽研究所碩士。早期作品,曾入選同志文學選與台灣文學選。另著有《我們沿河冒險》(國片優良劇本佳作)、《小道消息》、《晚間娛樂:推理不必入門書》,長篇小說《愛的不久時:南特/巴黎回憶錄》 (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短篇小說集《性意思史》。散文《我討厭過的大人們》《感情百物》。
OKAPI專訪:「我不願意說一些雞湯與金句,告訴你如何做人。」──專訪張亦絢《我討厭過的大人們》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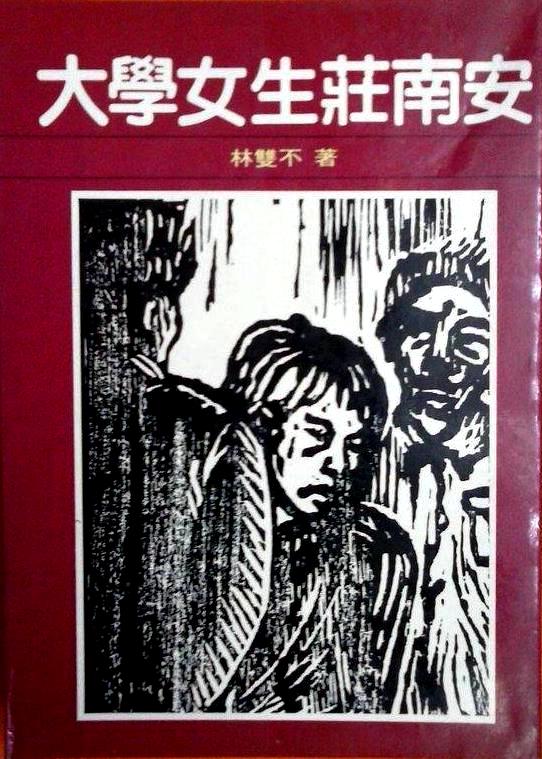 大學女生莊南安
大學女生莊南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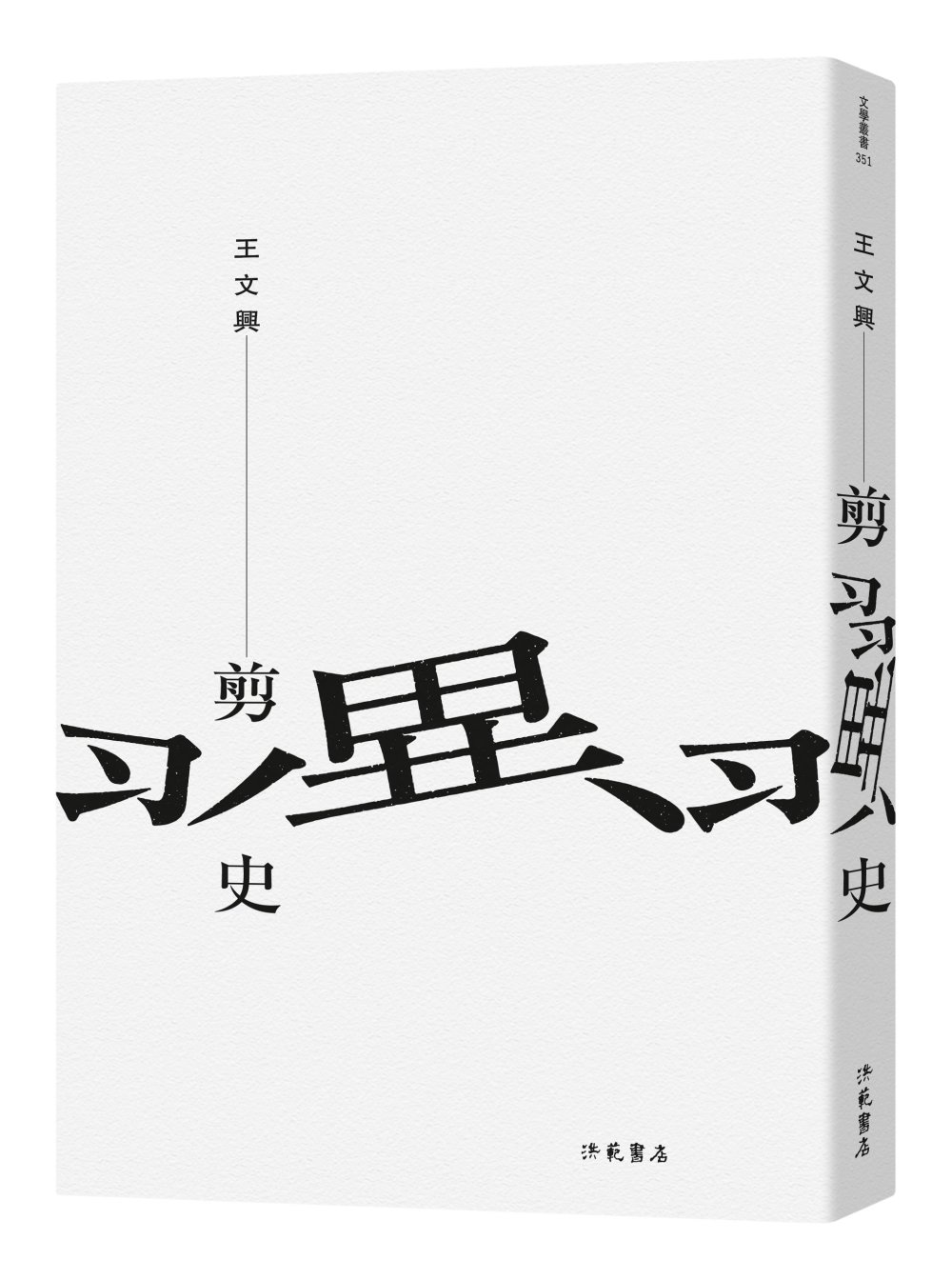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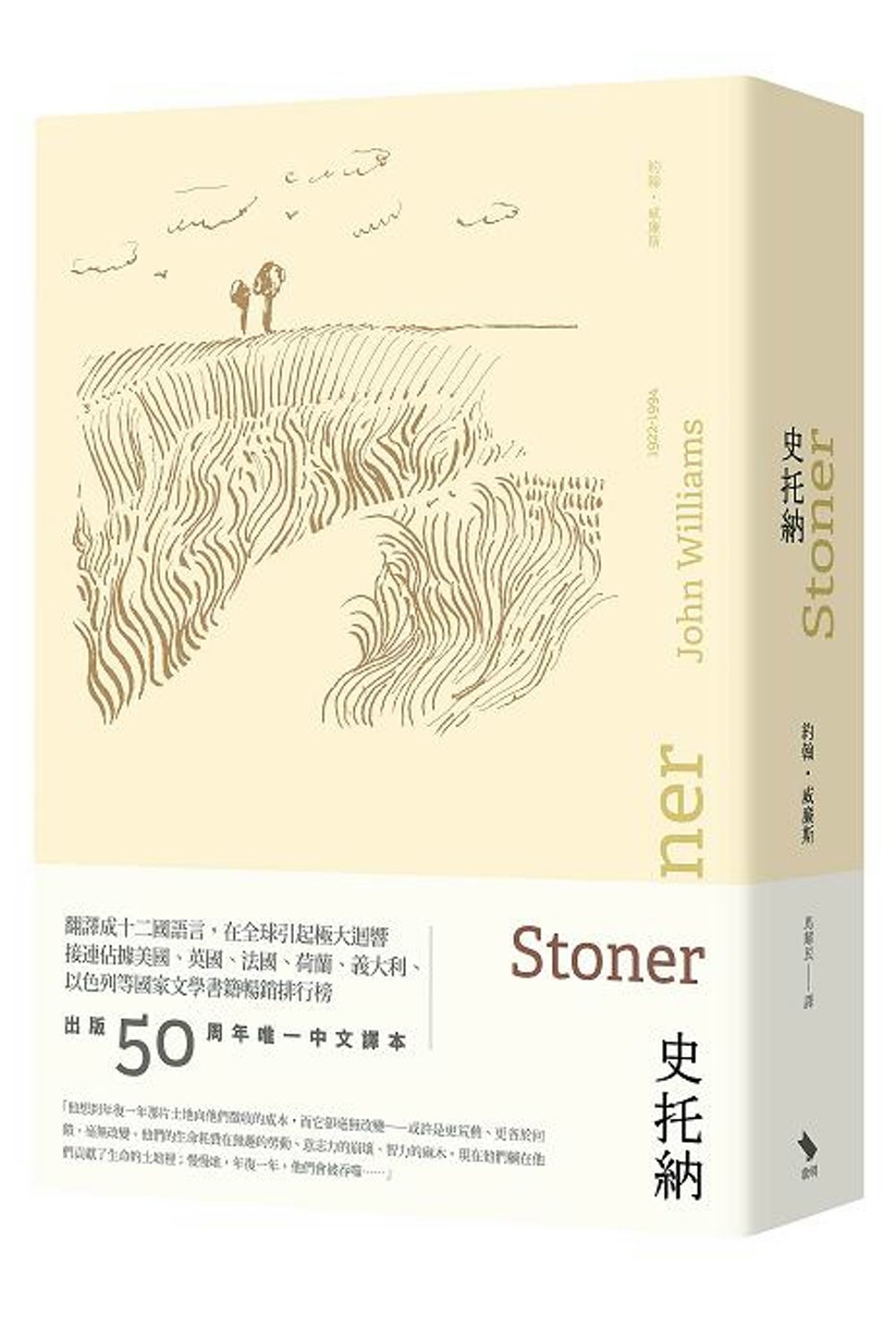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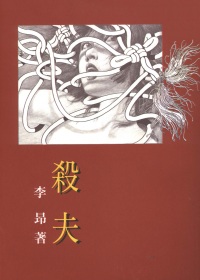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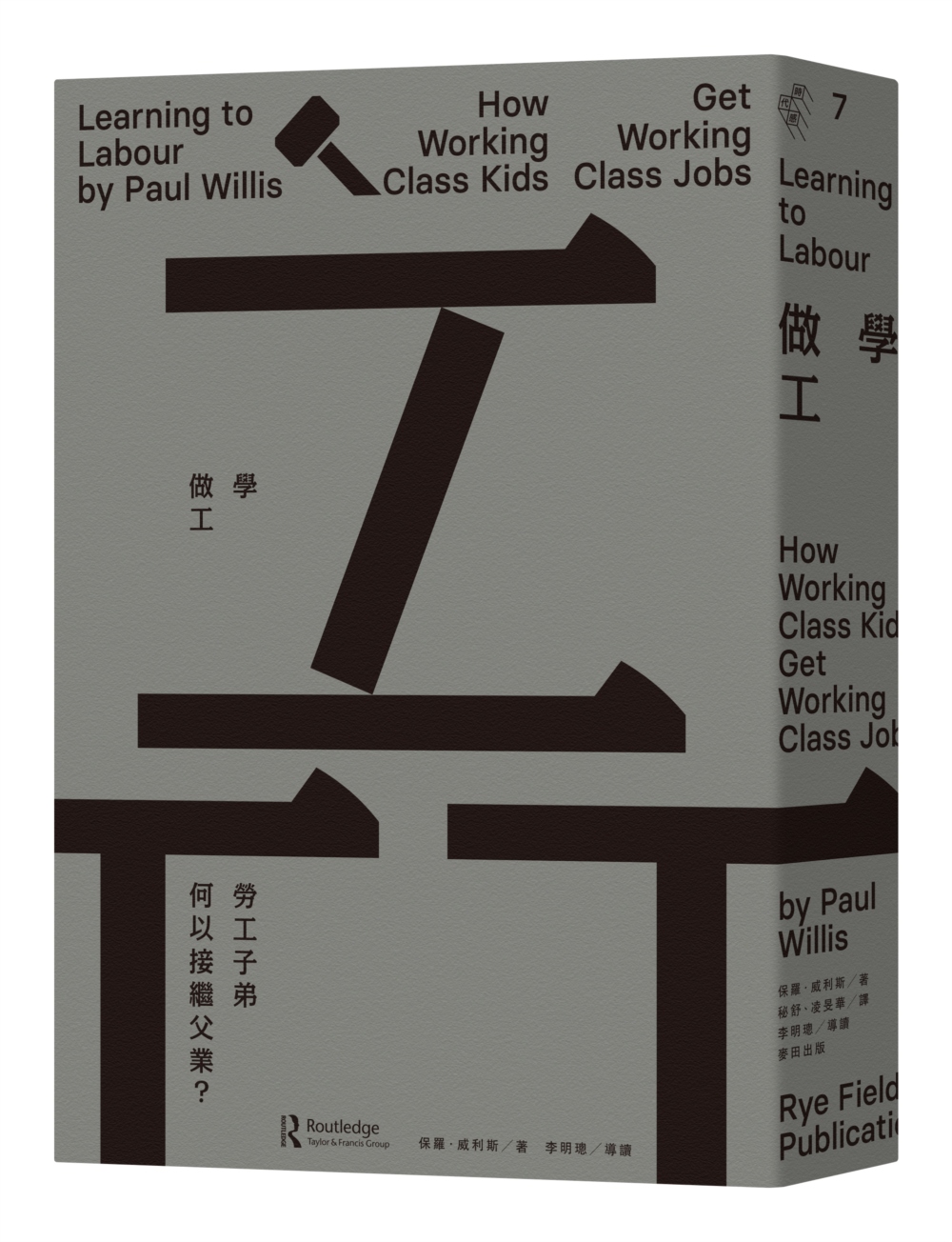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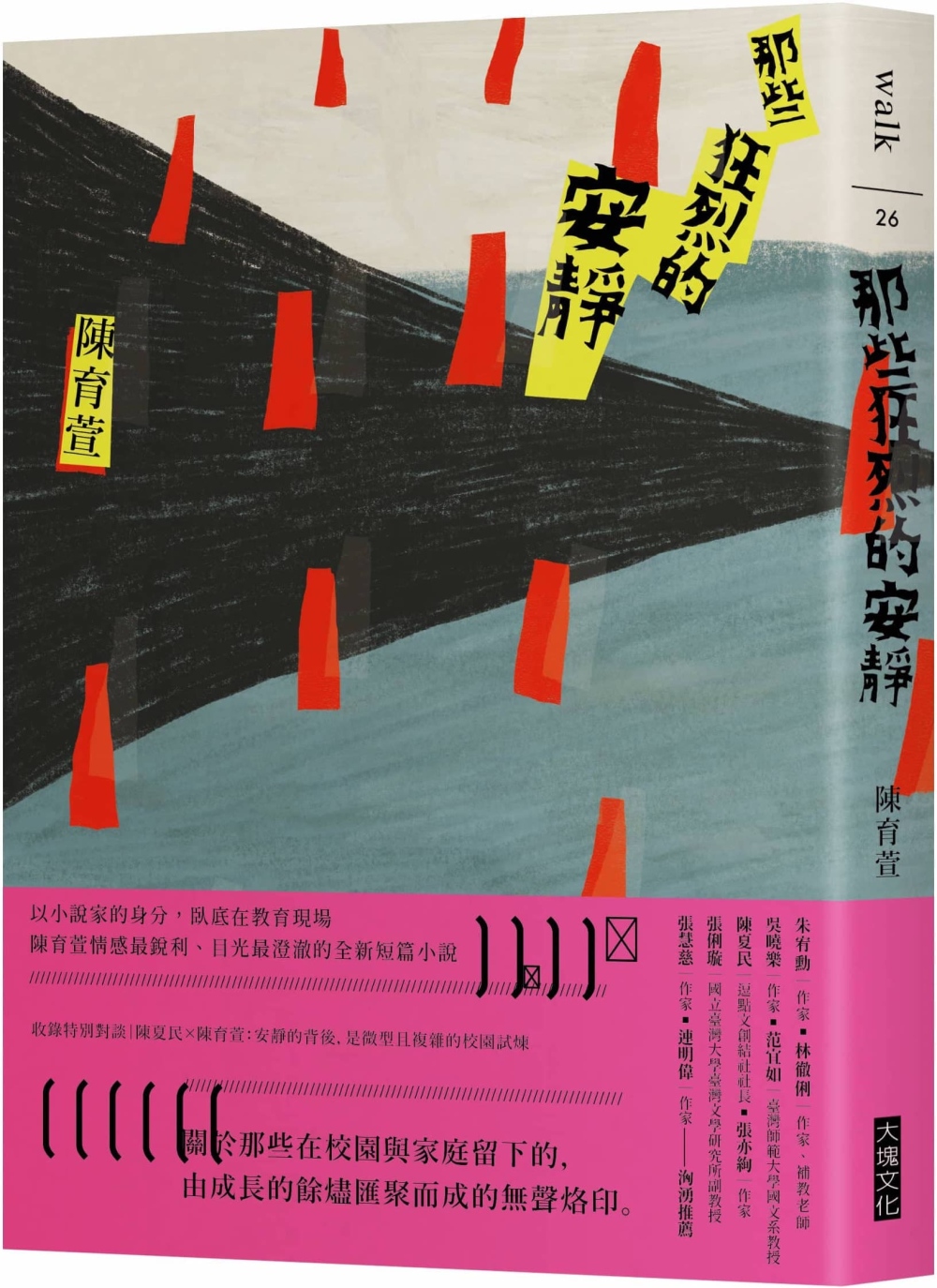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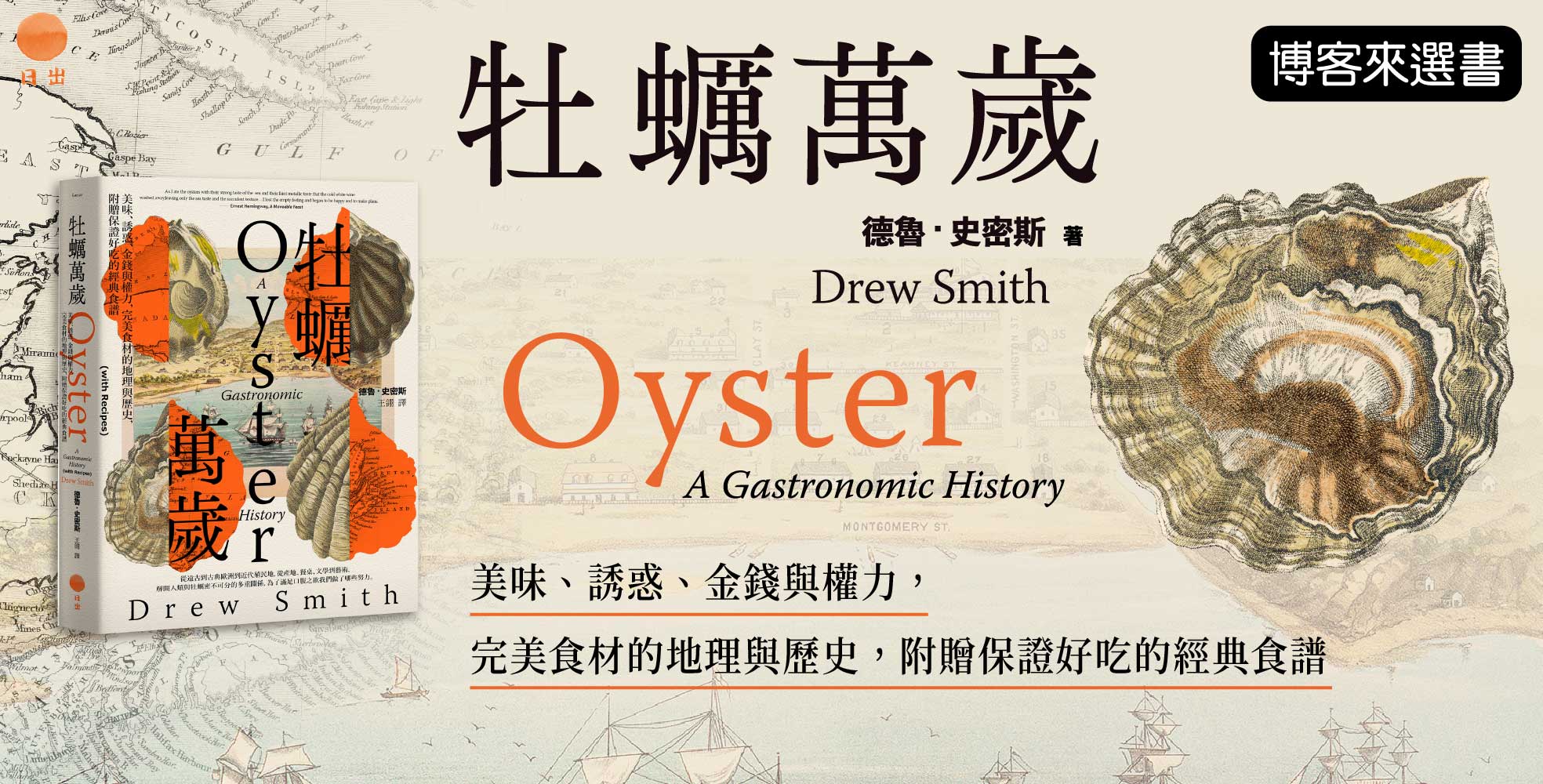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