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一首歌,聽在不同的人耳中,有些人會想念起某個人,有些人會勾連出某處場景,有些人會掉進某種回憶。而聽在臥斧耳裡,會讓他說出一則故事,寫出一篇小說。與其說他的新作《沒人知道我走了》是部短篇小說集,毋寧說這更像他自己的定義:一張概念專輯。
身為出版業內人士,從前端編輯(甚或更前端的審書與翻譯)到後端通路行銷,入行十多年來,臥斧幾乎都接觸過了一輪。有人認為身在出版產業,是躍升為作家的主場優勢,卻不是臥斧拿來運用的理所當然。「我是一個很積極的寫作者,但並不是很積極努力在找出書的機會。」從2003年第一本書《塞滿鑰匙的空房間》,起先還固定著一年一本的頻率,不意到了2006年的《舌行家族》後,卻又中止至今。問他這中間都沒寫嗎?「有啊。我要求自己每個禮拜都要寫一篇極短篇。」
或許熱愛寫作的人多數早慧,然而從國中就開始塗寫的臥斧,最初是為了替自己畫的漫畫編劇,才構築起小說的世界。「後來因為畫漫畫很麻煩,寫小說比較簡單,就比較常寫。」這一寫,寫出了臥斧對文字的熱情。雖然念的是理工,到了大學,他還是滿懷期待地進入校刊社,希望能更了解編輯與出版領域,卻遭遇到極大的衝擊。「那時在社團裡遇到的每個人,講的東西都言之有物、很厲害,但是我都沒聽過。」認為自己讀的東西不夠多、說自己「被刺激到」的臥斧,在那半年裡發奮圖強,每天讀一本小說,短短時間內,讀了一百多本。
讀得太快、太急,卻塞住了。
「一下子讀很多的壞處在於,你會發現很多人都很厲害、很多人都用不同的文字方式告訴你一些事情;但自己要寫的時候,反而不知道應該怎麼寫才對。而且怎麼寫好像都有別人的影子,又不可能寫得比人家好,那何必再繼續寫?」
大學四年,臥斧回到單純的讀者與閱聽者的位置,大量吞食各類書籍、音樂、電影,寫作卻一路空白。畢業後,他回返家鄉高雄等兵單,每個下午的例行公事,就是陪父親去爬山。某一天,在往山上走的路途中,臥斧突然想起Marianne Faithfull翻唱的〈碎夢大道〉(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前面幾句歌詞,旋律在腦裡揮之不去。「回家之後,我突然覺得,我好像可以寫東西了。」
說是那幾句歌詞裡,彷彿有個奇怪的故事,「我講不清楚,但覺得自己應該把它寫出來。」他花了一個晚上,寫成一部三段式的短篇,從未正式發表過。「再回去看那個故事是很奇怪的,有點喃喃自語,又不太完整,有時候我也不確定自己那時候到底想要說什麼。」〈碎夢大道〉的詞曲,就像某種「大師兄回來了」的暗號,一舉扭開臥斧阻塞數年的水龍頭,推他重新站上說故事的舞台。
多年來,臥斧的小說,多半都由音樂中萌芽。「我寫的短篇小說,每篇都用某一首歌來當主題。」爵士風格的〈What a Wonderful World〉曾經也是種子;重金屬、搖滾、東洋西洋台灣,都可能是一次觸發;就連他的《舌行家族》,都是從聯合公園(Linkin Park)的〈Crawling〉生出來的。但你要說他只是延伸歌曲的內容、自己多事去幫原創加油添醋?其實並非如此。
「我必須承認,有些純粹是自己『想太多』。」例如〈Crawling〉,歌詞描繪的是汗水從體內冒出、沿著皮膚流下,臥斧說,聽起來挺像藥癮發作時的禁斷症狀。但他的想像並未就此打住,而是放任成長,長出了自己想要的模樣。「我總是認為,當我接觸到一個作品,應該要有自己的看法,這比不斷探究創作者原來的想法還重要。」一個故事出了手,創作者便無任何掌控能力,但讀者有沒有能力去做出新的詮釋,是一場閱讀的考驗。
是以臥斧從來都很討厭寓言後面的啟示。「有趣的東西不會只有一種解釋方法,給了啟示,只會限制讀者的想法。」他從不覺得在〈北風與太陽〉裡,太陽用的是溫和的致勝方式。「太陽讓大家熱得非得將衣服脫光不可,那是非常高壓、非常慘烈的手段。而且這個比賽一開始就對北風不利──你怎麼可能用吹的把人身上的衣服吹掉?」他說。
「創作者給的東西不見得都是可以相信的。但如果讀者能從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創作就有意義。那個意義在於:它讓你去想了某些事情。」於是他從別人的歌裡,長出自己的故事;期盼閱讀的人,能從他的故事裡,再長出自己的東西。「今天我想講的某些事情,假如與某首歌有所互通,我就會想把這兩者扣在一起。但把它變成一個單純的故事之後,讀者是否能夠或必須從故事連回原來那首歌,不是那麼重要。」對臥斧而言,假若讀者又能夠有自己的新角度、新看法,在不同的形式上,找到自己幫這個主題化妝的方式,那他就說了一個最好的故事。
〔臥斧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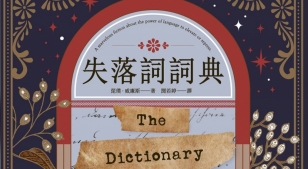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