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余英時傳》的周言來自中國,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現在是清華大學社科學院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早在先就已撰寫過陳寅格、王國維兩位重要人物。《余英時傳》可以說是粉絲追星的最高等級,由仰慕而生進而完成一本如此重要的著作,讓讀者從家族到生平與成就,瞭解這位當代學術史與思想史的重要人物。
後人可以從談話錄與回憶錄直接理解余英時的思想,但卻從未有相關著作完整記錄余英時的一生,作者多次在普林斯頓與余英時見面,也讓他看過本書書稿。余英時的學術貢獻與通才身分,其實從出生就注定,他身處的世代更是造就他的其中原因。透過跟周言的十問十答深入理解《余英時傳》的書寫動機與筆後秘辛。
1、1949前後離散海外的學者很多,選擇為余英時老師作傳記的原因為何?
答:因為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尤其是二十一世紀以來,學術界基本上公認英時先生的學術地位最高,影響最大。文史哲領域沒有統一的評判標準,許多專門之學都出了一等一的大學者,但是余英時先生的著作已經超越了學術界,在學界以外也擁有廣泛的受眾,余英時先生在八十年代的臺灣即享有大名,八十年代末以後,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在中國大陸影響越來越大。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大約2011年,我曾聽說,有一位大陸四川大學的何姓本科生,因為仰慕余先生的盛名,不遠萬里從四川坐飛機到紐約,隨後換乘各種交通工具到達余英時先生所在的普林斯頓,他通過輾轉打聽,居然找到了余先生的住所,並且得到了余先生善意的款待。他和余先生素昧平生,也沒有任何介紹,純粹是追星的想法。我想我選擇余先生作傳,也有一些類似追星的想法,試圖去解釋為何余先生的成長歷程如此坎坷,卻突破了自身和國家、社會的諸多限制,成為一個享譽世界的史學大家,可以給我在內的許多年輕的後學一點小小的啟示。
2、是在如何的契機和背景下和余英時先生相識?
答:在認識余先生之前,我周圍有許多認識的學術界的老師和前輩都和余英時先生比較熟悉,拜訪余英時先生是我2011年去美國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前的想法,我想很多人那時候都讀過余先生的書,但是都沒有見過余先生本人,我只是恰巧認識余先生的朋友,通過前輩的引介才得以拜訪余先生。但是據我所知,只要有正當合理的理由,余先生都會接待,尤其是年輕人。余先生早年曾有拜訪胡適之的想法,並且有著太多的熟人可以引介,但是始終緣慳一面,所以我想這件事可能在他心中種下了一個心結,所以他願意以更多的善意來接納學術界的年輕人。從那次拜訪之後,我只要去美國,基本上都會到餘府去拜訪,平時通電話的次數也不少,但是很遺憾,他九十以後,我考慮到他的身體原因(余先生晚年聽力堪憂,需要余太太轉述),很少給他去電話了,成為了我現在追悔莫及的一件事,很多傳記裡的疑點我還沒有展開問他。
3、余英時老師畢生著作甚豐,並且跨越多種語言,在採集資料或者寫作過程中是否有印象比較深的挑戰和困難?
答:余先生的寫作語言主要是中文和英文,有一些著作是相對比較淺顯的文言文寫的,這對我來說都不是困難,所以我在傳記中引用了許多余先生在美國學術界的同仁用英文寫的對余先生著作的評論。我面臨的困難主要是因為中美間隔,很多余先生執教過的大學裡藏有的余英時先生的檔案許多還沒有開放,查找起來也很不方便(只有哈佛時期的授課資訊和耶魯時期的履歷表我曾經查到)。另外哈佛大學的東亞系所藏楊聯升日記有余先生大量的資訊,我曾經仔細讀過並且寫過文章,但日記裡還有更多內容值得進一步挖掘,這一方面的挑戰主要是日記本身是用比較淺藍色的鋼筆寫的,年歲日久字跡比較模糊,即便是臺灣中央研究院藏的原本也不太清楚,而且哈佛燕京藏的複印本也存在著字跡不清的問題,包括一些英文學者的名字有連筆的情況,需要一一辨別,這都需要未來花大量的時間和經歷去做。
4、和余英時老師生平相關的著作不少(如《余英時回憶錄》《余英時談話錄》),《余英時傳》和它們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答:余英時回憶錄據余先生所述,是根據李懷宇整理的《余英時談話錄》擴寫而來,但是據我所知,李先生做了一些很初步的整理,大多數還是余先生本人的回憶,如他回憶從潛山到北京這一路的漂泊,曾經住過南京、天津、瀋陽等地,這些都不是訪談者能夠問出來的。我15年曾把《余英時傳》初稿給余先生看過,余先生曾對裡面幾個細節用所採用,如余先生在中正大學讀書時,曾受教于清華國學院畢業的高亨,這一點余先生做了進一步的回憶;再如我在傳記第一章便寫到了余先生的叔父余誼密(余英時父親余協中的族兄)被滿門抄斬之事,余先生在回憶錄中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寫到了這件事,類似的細節還有很多。新近出版的李懷宇整理的《余英時談話錄》,我看過,大部分內容我都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不多,比如費正清參加鄧小平晚宴的事,這個事倒是很新鮮,以前我沒有聽說。
《余英時傳》主要還是立足於文獻,比如說對余先生家族、包括余先生父親、母親、岳父的描寫,以前較少有人涉及,我是為數不多的親自做過余先生早年生涯田野調查的,尤其是潛山老家的一些小學同學和北平居住時期的一些鄰居,這個是寫作傳記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另外是對於《潛山余氏族譜》的引用,我似乎是學術界比較早的,族譜中一些不準確的內容,余先生也曾經和我交代過。而對於余先生經歷過的一些歷史大關節,也補充了許多新資料,如關於陳寅恪的論戰,我披露了錢鐘書和金庸參與其中的兩封信,再如中大改制,也引用了陳方正先生的一些新說法。還有一些細節,許多人以前不知道,如余先生大概很早就認識張愛玲(五十年代在香港),但真正來往密切是八十年代張愛玲讀到余先生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主動給余先生寄書。以往學術界對余先生有一些學術上的批評,我也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加以引用。另外有一些我還沒來得及寫進書裡,比如中國學社的一些幕後的故事,我採訪了一些當事人,和目前通行的說法有所區別,另外還有關於余先生哈佛畢業後為什麼去密西根大學教書,此事缺少一個相對恰當的解釋,而《余英時談話錄》對此也沒有說到點上,未來我會寫文章解釋,希望在余先生一百歲的時候出版一個修訂本,回答這些問題。
5. 《余英時傳》中有相當程度的篇幅記述了余英時老師在香港求學與任教的往事,香港這個地方在余老師生命中的意義與特殊性是什麼?
答:香港開闊了余英時先生的視野,也是他學術和作為公共知識份子的起點,香港在五十年代所處的環境很特殊,這一點陳方正先生在追憶余先生的文章中已經說的很詳細,此處就不展開了。余先生早年讀的很多西方的書,都是在香港讀的,他積極投身公民社會,用言論影響社會,也是在香港作為起點。
6. 余英時老師自其廣闊的知識體系中提煉出「知識人」的概念,這與過去人們所稱「知識份子」有何不同之處?
余先生大概很不喜歡“分子”這個詞,覺得“分子”這個詞在革命敘述裡和“組織”這個詞擺脫不了關係,所以他更強調知識份子作為“人”的特性,我覺得余先生喜歡用“知識人”這個概念,很有可能是從傳統文化中引來的“立人”的這一思想資源,並且“知識人”這個概念在中文學界已經引起了很大的認同,有時候我寫文章談到知識份子,還會遵從余先生的敘述方法,改為“知識人”,余先生曾用毛筆給我寫過這三個字,我一直掛在書房,永志不忘。
7. 余英時老師於香港新亞書院時期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哈佛時期授業於楊聯陞先生,二位先生分別在其學術上有何啟發與影響?
錢先生主要給了余先生通史的大視野,楊先生給了余先生精湛的考據功夫,這兩者結合,成就了余先生從古到今的歷史研究既有歷史大脈絡的把握,也有精妙入微的考據部分,如《論天人之際》、《方以智晚節考》,最經典的,還得是《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8. 余英時老師在美時期陸續執教於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名校,他對西方漢學帶來的影響為何?
西方漢學按照余先生自己的說法,其實已經衰落,取而代之的則是費正清為代表的中國學,後來中國學也日漸式微,更多的強調“區域研究”(area study) 。現在的學術界更強調自己的研究和世界學術界的對話,許多西方學者的研究如今已經得到中國學術界的廣泛認同,尤其是歷史學。余先生的學生中,目前來看學術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是中央研究院的王汎森院士,他也是學術界公認的可以繼承余先生衣缽的傳人。
但未來西方學術界要出一個余英時很難,這是時代背景和學術界的環境改變造成的,現在西方學術界更看重一個學者在某個領域的造詣,而不太重視這個學者是否是“通才”。
9. 余英時老師從八○年代起,便為臺灣民主發展趨向撰著一系列的政論文章提供建言,臺灣民主社會的演進與實驗對他的意義為何?
余先生其實一直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大抱負,可惜學術界的平臺太小,所以八十年代他曾經對臺灣民主社會的演進提供了不少的意見,可以看作余先生對於政治“遙遠的興趣”。臺灣坊間傳言蔣經國曾經召見余先生談話,並以此非議余先生,我沒有看到相關的談話記錄,無法判斷,我想余先生本質上還是個學術界的人士,對於政界的許多事情他提出自己的看法,給出合理的建議,也是盡了一個知識人的本分。
10. 依您長期的近身採訪與觀察,在學術以外的余老師是個怎麼樣的人?
生活中的余先生淡泊名利,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余先生真的對錢沒有任何興趣,也沒有任何概念,他許多出版的書都不要稿費,只要求出版社多給他寄書,他好送人。我對字畫有點研究,從余協中到余英時,字畫收藏一直是這對父子的一大愛好,我曾經看到過很多余協中先生的舊藏,都是余英時先生捐掉的,比如文徵明的手卷,市場價值不可估量,按照現在的市場價大約要幾個億,但是余先生說捐就捐。生活上他也很簡單,晚年也很少在外面吃飯,都是余太太做一些簡單的飯菜,余太太的甜點是一絕,我曾多次有口福嘗到。余先生原來還有抽煙的愛好,晚年生了大病,從此戒煙,這需要很大的毅力。余先生余太太待人春風化雨,無微不至,余太太曾經和我開玩笑,說我結婚以後體重暴增,可見婚姻幸福,他們二老還曾問起我太太的情況,非常體貼周到。
作者簡介
我1989年出身在中國大陸,少年時代一直在江蘇,後來在復旦大學讀書,早年的興趣點在中國近代史,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後,曾經主編出版過《辛亥百年:回顧與反思》,同時關注研究辛亥以後的清遺民,曾經專門研究過王國維,出版過《王國維與民國政治》,並且以王國維研究為契機,加上寫作《余英時傳》的機緣,研究另外一位文化遺民陳寅恪,主編有《陳寅恪研究》兩種(陸續會繼續出續集)。近年來興趣有所轉移,著重研究上海1949年之後對於文化界的改造以及上海的文革運動等相關問題,有兩本相關的書待出。
學術之餘,我的主要愛好是古董車和京劇,我是上海古董車藏家中專門收藏日式jdm車型和俄式4x4越野車的玩家,擁有包括豐田世紀、豐田第五代皇冠、uaz452、uaz469在內的諸多車型,亞洲著名越野車藏家馬大立,是我在汽車收藏界的老師。我對於京劇的愛好是從小到大一直有的,我少年時代癡迷於老生藝術,曾經和周信芳大師的長子周少麟先生有過來往,也曾經向楊派京劇大師楊寶森先生的得意門生汪正華先生問藝,這是我幼年時代難得的機緣,成年之後,我癡迷譚派藝術,譚鑫培譚富英的唱段,我基本上都會唱。專攻老生藝術之餘,我曾經長期向四大名旦尚小雲先生的公子尚長榮先生學習花臉藝術,曾向尚長榮先生學習《取洛陽》、《曹操與楊修》等花臉名劇,我也曾自己組織堂會,邀請北京京劇院梅蘭芳京劇團赴上海演出《群英會》、《借東風》、《打侄上墳》、《春閨夢》、《將相和》等劇碼,我在《南方週末》長期開設“梨園瑣談”專欄,專門談看戲演戲的心得。
學術之餘,我的主要愛好是古董車和京劇,我是上海古董車藏家中專門收藏日式jdm車型和俄式4x4越野車的玩家,擁有包括豐田世紀、豐田第五代皇冠、uaz452、uaz469在內的諸多車型,亞洲著名越野車藏家馬大立,是我在汽車收藏界的老師。我對於京劇的愛好是從小到大一直有的,我少年時代癡迷於老生藝術,曾經和周信芳大師的長子周少麟先生有過來往,也曾經向楊派京劇大師楊寶森先生的得意門生汪正華先生問藝,這是我幼年時代難得的機緣,成年之後,我癡迷譚派藝術,譚鑫培譚富英的唱段,我基本上都會唱。專攻老生藝術之餘,我曾經長期向四大名旦尚小雲先生的公子尚長榮先生學習花臉藝術,曾向尚長榮先生學習《取洛陽》、《曹操與楊修》等花臉名劇,我也曾自己組織堂會,邀請北京京劇院梅蘭芳京劇團赴上海演出《群英會》、《借東風》、《打侄上墳》、《春閨夢》、《將相和》等劇碼,我在《南方週末》長期開設“梨園瑣談”專欄,專門談看戲演戲的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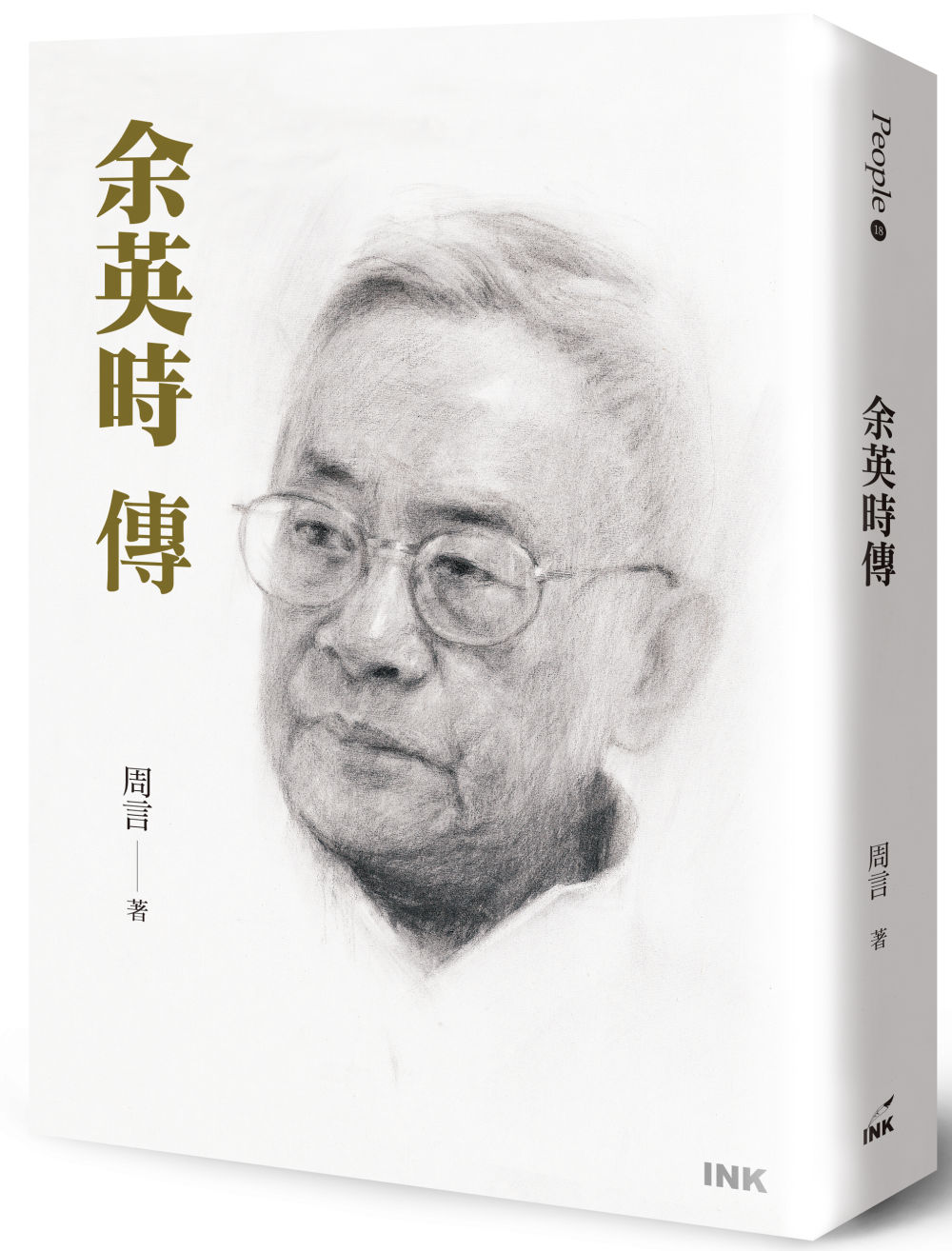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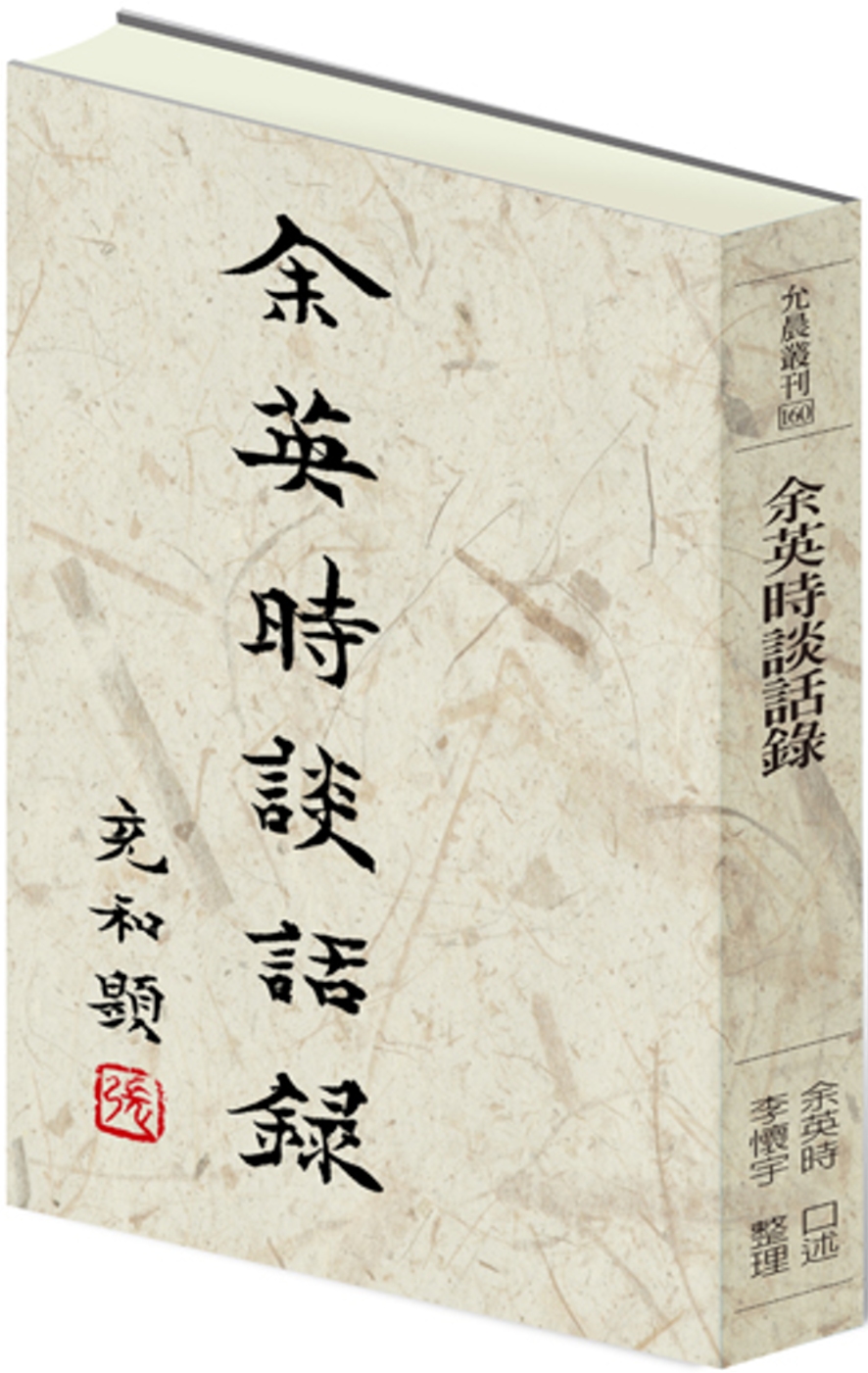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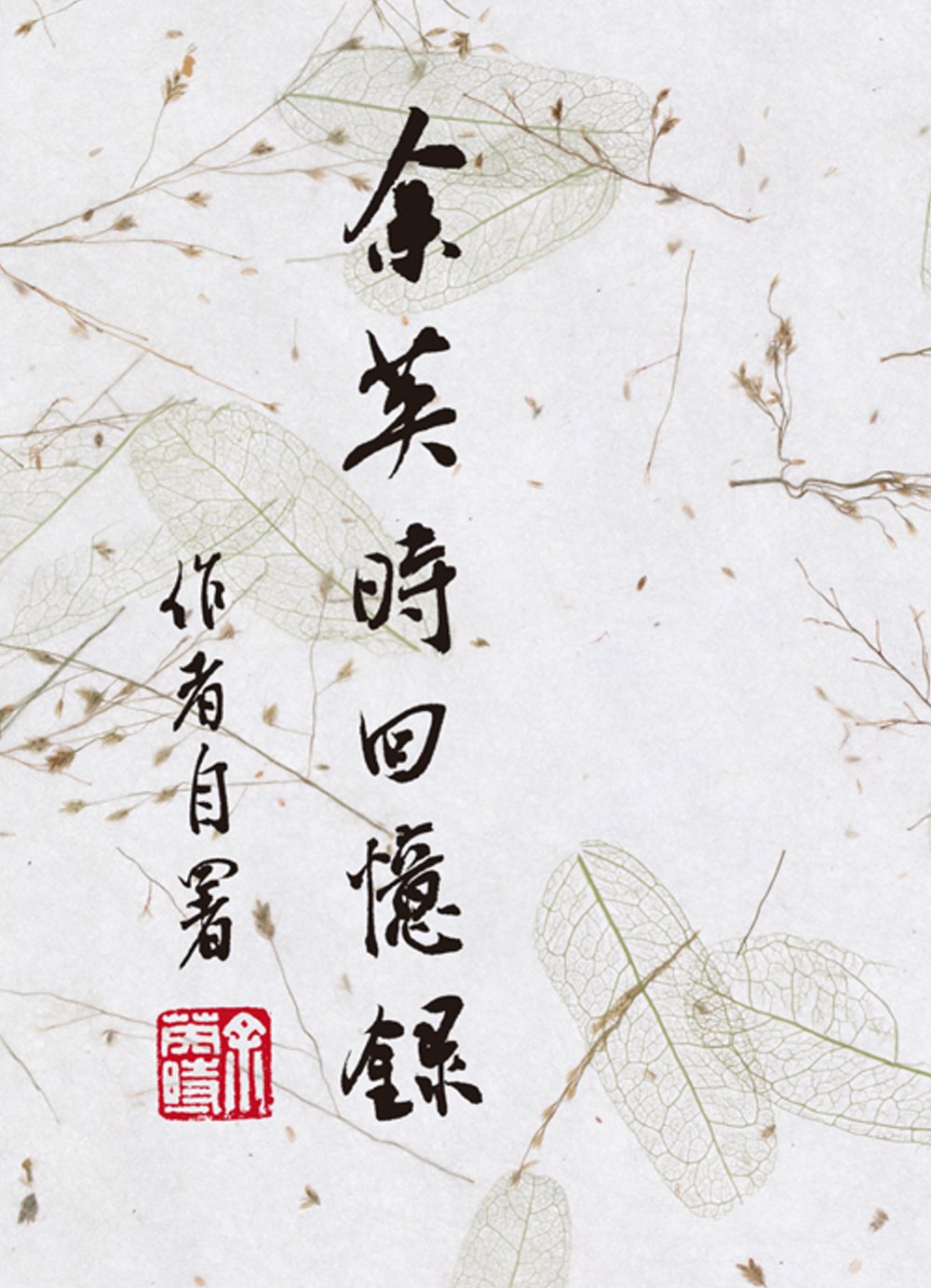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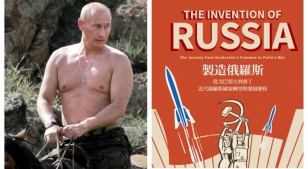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