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燒一年多的疫情,讓人只能在島嶼裡探索,既然不能去遙遠的地方旅行,那就往遙遠的過去走去。萬華,就是我的過去。我的小學在萬華區、第一個職場也在萬華、我的父親則在茶室林立旁的小學任教30年。我們沒住萬華,但幾十年來的謀生都和萬華有關。就算這幾年的生活圈已經離開萬華,但還是會週期性的回到萬華。
去年週期性的回萬華是為了在就業服務站辦理失業救濟金,每個月和承辦員見面就是一趟結合拜拜與小吃的祈福之旅。萬華的小吃和巷弄常民不做作的風景,淡化了我的失業焦慮,就這樣養成每個月去萬華的「習慣」。就算後來停領失業給付,每個月還是會去一趟,到龍山寺走走、到廣州街吃碗肉粥配燒肉、豬肝和涼筍,然後再沿著昆明街往西門町的方向走,這一路會經過我小時候學游泳的YMCA,路過第一次當志工的柳州街辦公室,然後就是電影街了,還記得小時候全家大小常在中國大戲院排隊看電影,那時候天橋還在。
(延伸閱讀【黃麗如專欄】失業者的艋舺紓困半日行)
有時候拜拜完會走萬大路,路過幼時常跟媽媽一起等公車回板橋的公車站、經過小學的校門、然後轉到長泰街,一路走到青年公園。沿途當然會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小學同學、不曉得三十年後大家怎麼了,就算是迎面走來,也應該認不出來。這一區的國宅變化很大,甚至路名都改了,以前很多同學住在「克難街」,後來改成了「國興街」。這條散步路線會走到南海路、穿越植物園,終點是和平醫院旁的咖啡館。春天時,咖啡館外的櫻花總是開得特別燦爛。
若時間有限,週期性的拜拜完會選擇和平西路一段的路線,先吃一碗蚵腸麵線再走到店員總比客人多的書店,買了幾本書之後,穿過一排鐘錶批發店,看看大理街上的那棵氣根茂盛的榕樹。樹後方的報社早已人事全非,還好樹仍在。
我父親已經從萬華的學校退休十幾年,可是他和萬華的關係沒斷。他總是大老遠從三峽搭公車去萬華的銀行辦事、去萬華買純牛皮的鞋子。近期因為要幫我媽媽去台大醫院領處方籤藥物,他藉機每三個月去萬華一趟。領完藥,便搭著捷運去龍山寺站,先拜拜然後又是一輪懷舊小吃巡禮。肉粥、碗粿、麵線,全部掃一輪以確認這個世界沒有太大的改變。
我五月初又去了萬華。這次不只是拜拜、吃小吃,還順道去看剝皮寮的「尋城記」展覽。本來只是貪婪地到室內吹冷氣逛逛,結果記憶之海一波波的襲來。這個標榜「私的台北」的策展裡,竟然有「挪威森林」的店招、「女巫店」的物件、「地下社會」的氛圍、還有ROXY……人生走馬燈凝聚在展間裡。戶外火辣的太陽下是我的小學街區,室內所陳列的空間則是我18歲以後的精神庇護所。在這個五月,他們不尋常的聚在萬華。那個午後,展場沒有人,我幾乎以為眼前的一切是為我而展出。


 「私的台北」展有「挪威森林」店招、「女巫店」的物件、「地下社會」的氛圍。(攝影/黃麗如)
「私的台北」展有「挪威森林」店招、「女巫店」的物件、「地下社會」的氛圍。(攝影/黃麗如)
兩天後,就爆出了茶室風暴,接著萬華成了從早到晚都會聽到的名詞,病毒、疫情、難堪、獵奇都跟這裡有關,平時不被大家注目的萬華成了聚光燈下的標本、被道德魔人強烈檢視的對象。我們的敵人是病毒,而不是住萬華、去萬華的人。我的記憶之旅聖殿,成了獵巫的焦點。
由於我的足跡和所謂的疫區過於接近,疫情爆發後自己也覺得不安,擔心會不會就這樣走著走著就「中標」。莫名的乾咳、暑氣帶來的頭重昏沉都讓我疑神疑鬼,尤其打開電視看到名嘴們各式各樣對於症狀的發言,讓我更加焦慮。晚上睡覺時還會想著「萬一染疫要怎麼辦」之類的問題,想著想著都頭顱發熱、險些氣喘。懷疑自己染病,但體溫怎麼量都是36.3,我甚至還找出另一支溫度計來雙重確認。我,一個只是某個午後路過萬華的人,反應就如此緊張了,何況是住在那裡、必須在那裡工作、必須24小時守護在醫院裡的工作人員……這些和萬華緊緊相關的人,身心壓力的龐大豈是我們可以體會的?後來我就不怎麼看電視了,和疫情有關的網路新聞也盡量不點開,尤其標題重口味的。
居家自我健康管理滿兩週,我好好的。但是萬華是一個箭靶,快被輿論講成了壞掉的地方。我知道萬華不會壞掉,壞掉的是那些充滿歧視、惡意批判的人心。病毒擴散是我們要一起面對的現狀,不幸染疫的人不是瘟神,他或她極可能是我們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與其攻訐別人為何那麼不小心染病或把病毒擴散,不如靜下心好好整理自己、好好待在家盡量不與人接觸,這時的酸言冷語不會讓病毒消失,只會瓦解我們對彼此、對社會的信任。如果你已經對台灣失去信任與信心,可以想見活在這裡會多麼痛苦,比染病還痛苦。病毒有一天會消失或被克服,但失去信任感的人,會永無止盡的疑神疑鬼,這個病永遠不會好。
萬華經歷過SARS,經歷了此刻的肺炎,就算如此,我還是愛萬華,以後也會去萬華。待疫情緩和,再重新啟程,在記憶的地圖裡張望舊的和新的風景。
作者簡介
個人部落格:享樂遊牧民族
Fb:享樂遊牧民族
※本篇文章由作者個人創作授權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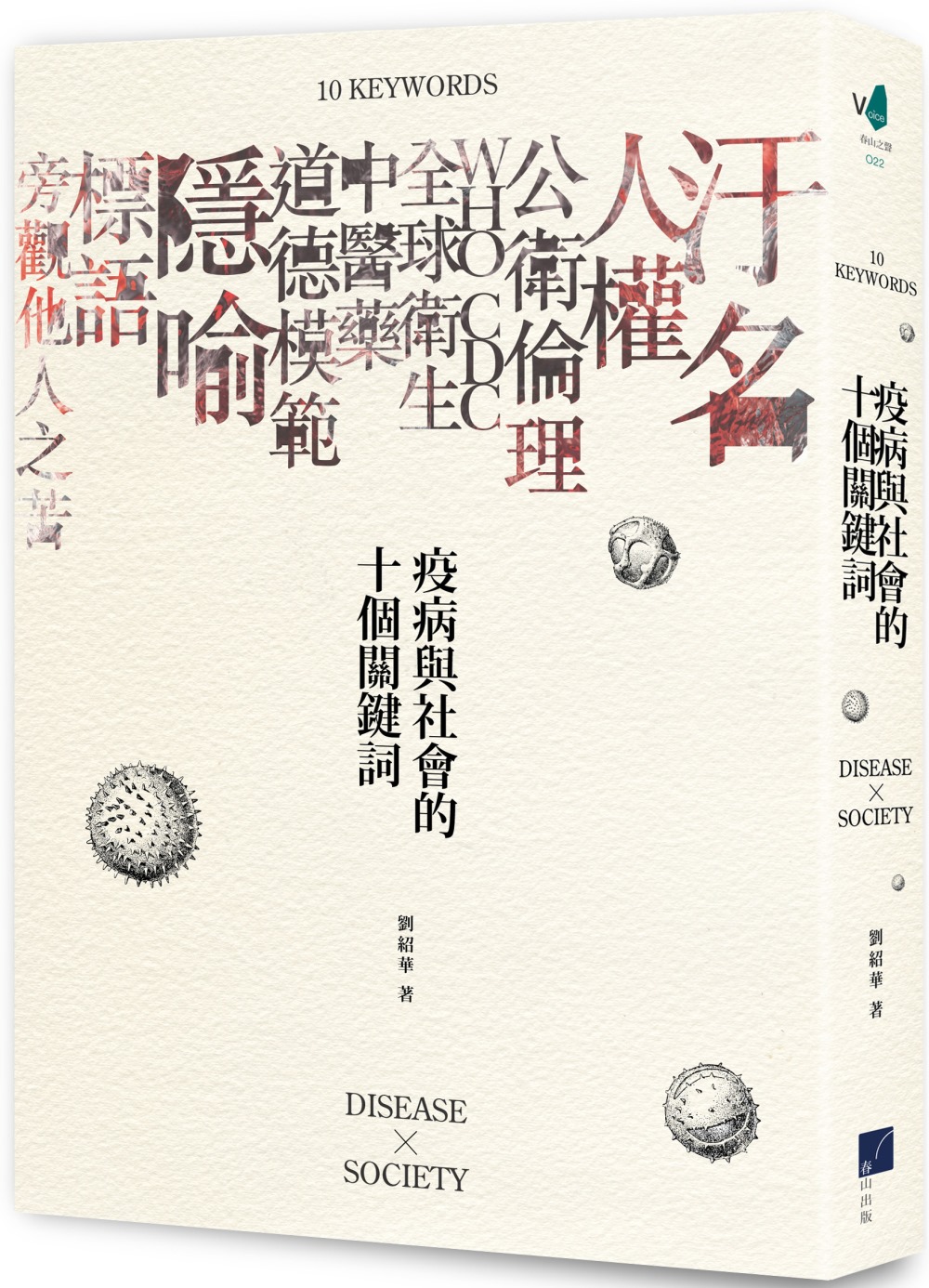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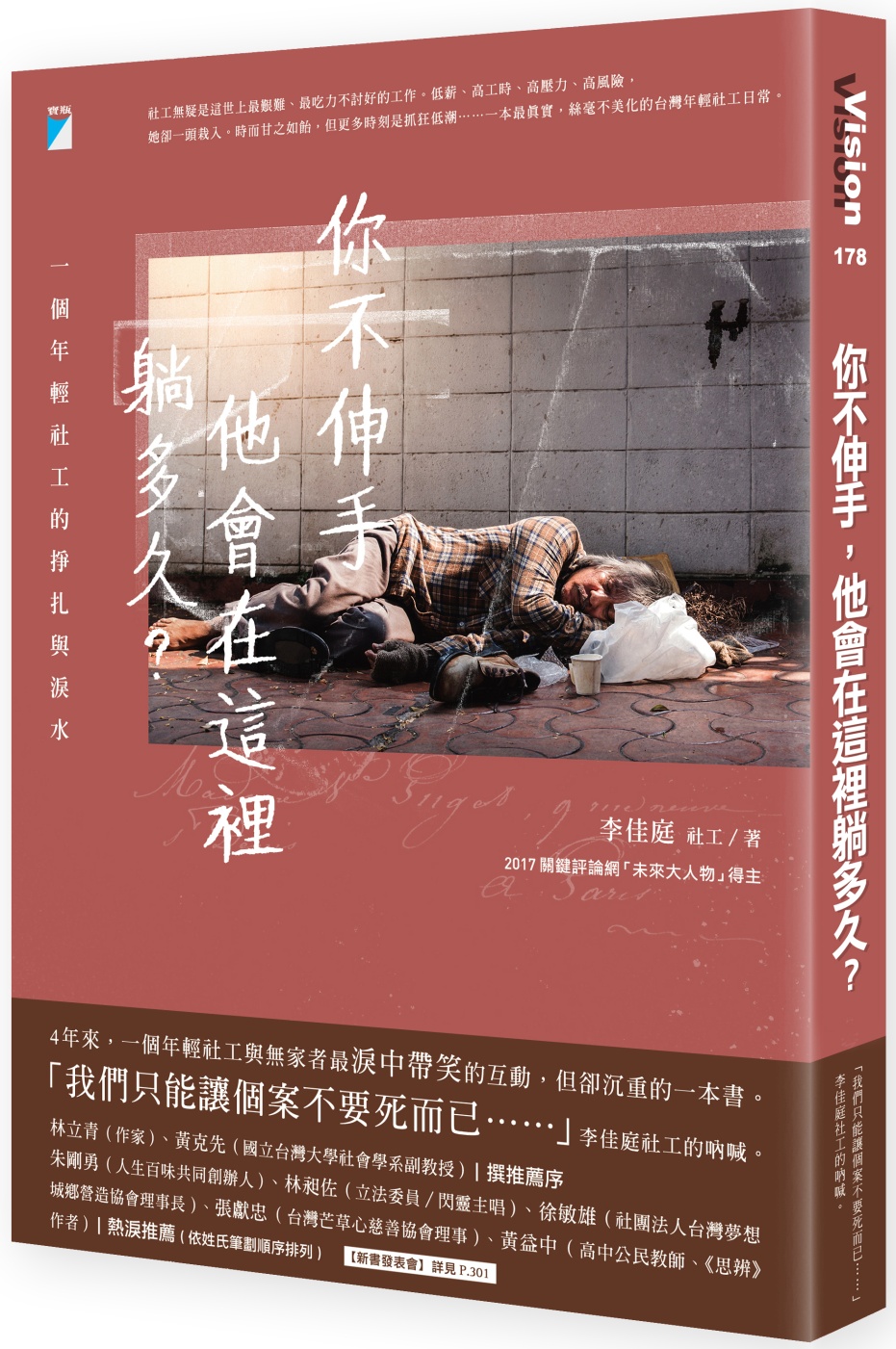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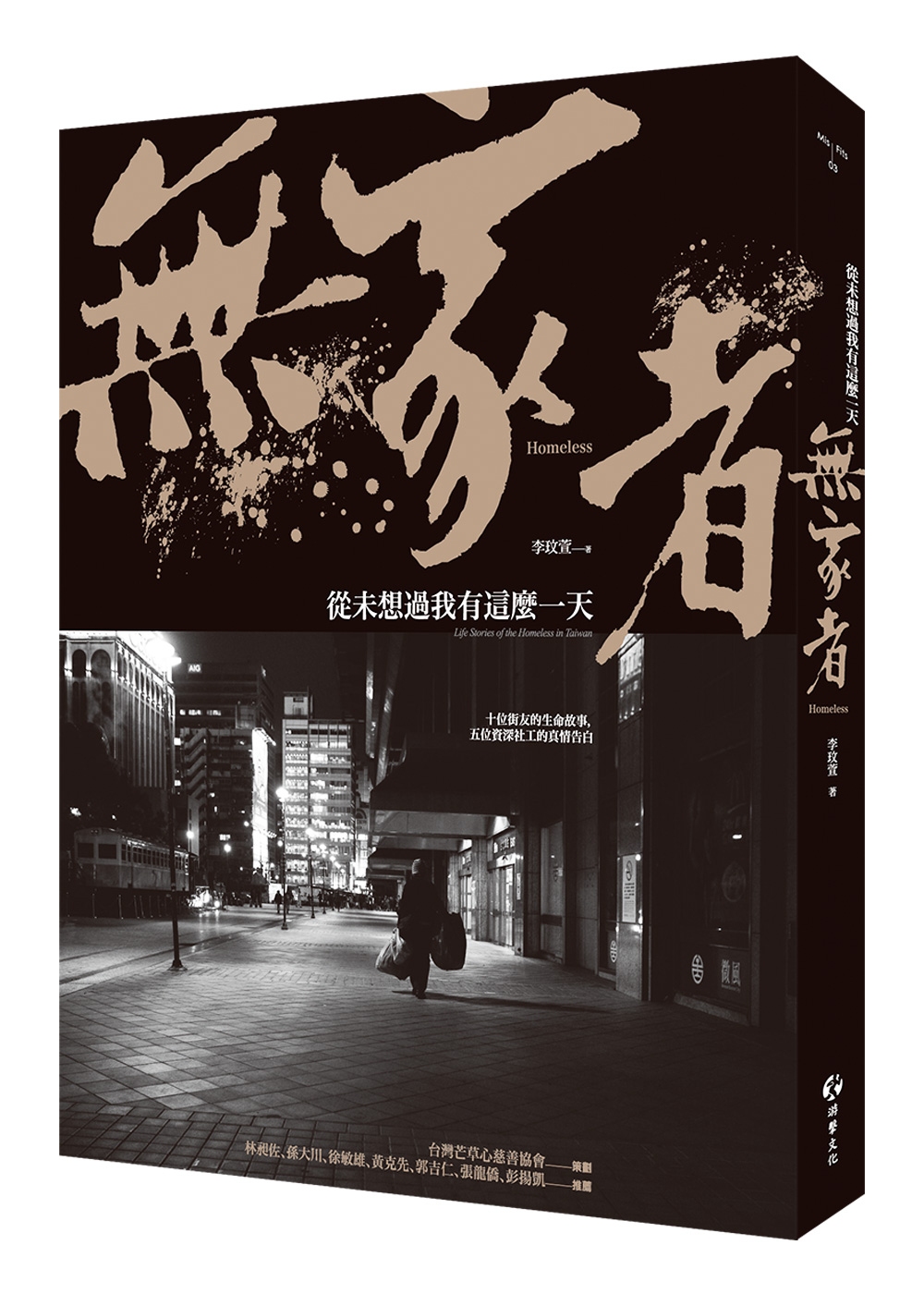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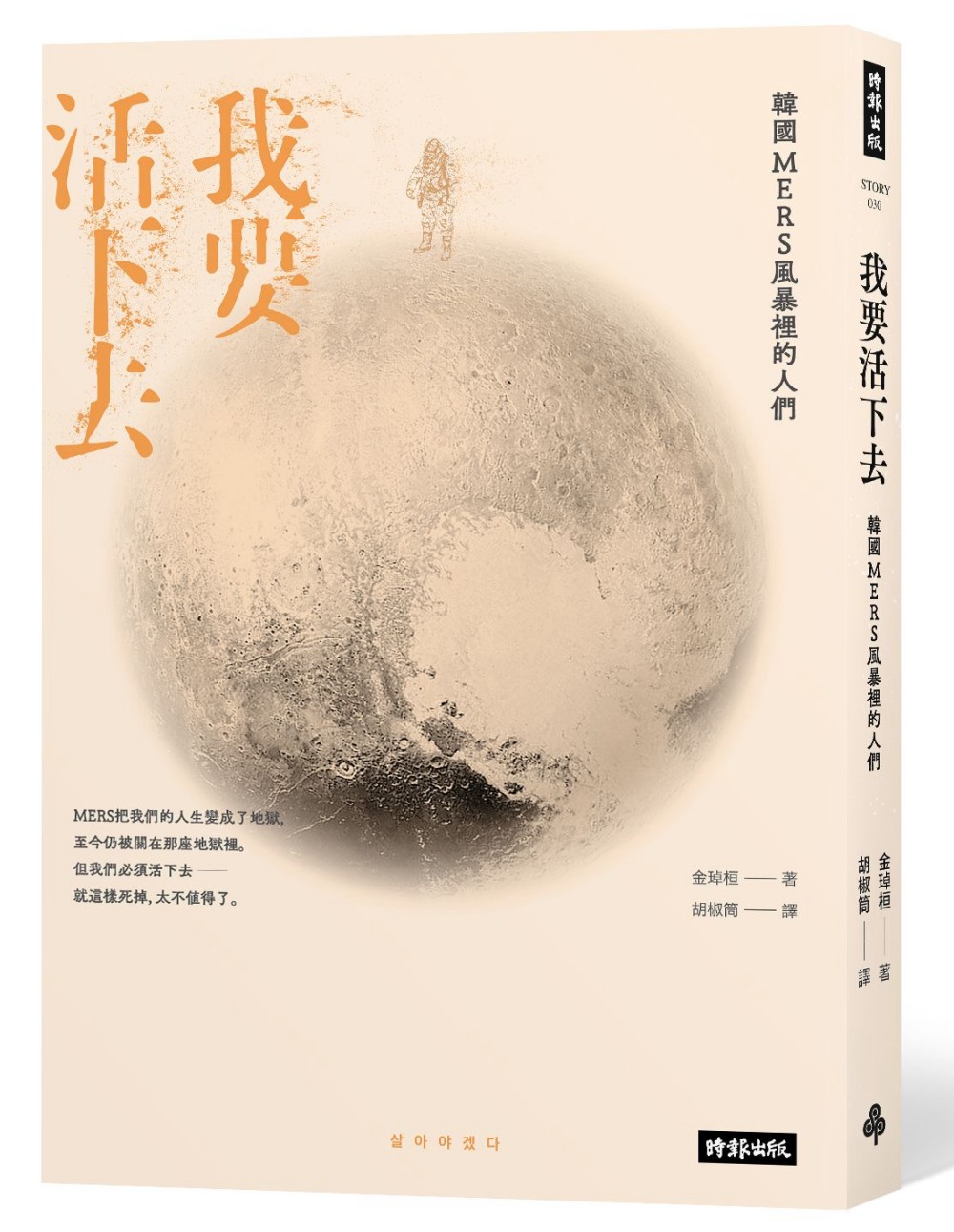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