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豹,一身白灰色皮毛,鑲點黑色斑點和短條紋,颯爽英姿中夾著些許貓科的萌態,牠是亞洲高海拔山區的特有物種,有「雪山之王」的美譽。你可知世上有多少人願意千里跋涉、耐著性子等待,只為一瞥雪豹身影?
在我面前的徐振輔,就是其中之一。
為什麼對雪豹這麼執著呢?他眼神有光的說,「對一個自然生態愛好者來說,『看雪豹』有無上的魅力。雪豹是很神祕的動物,非常稀少、非常難見,生活在一般人根本到不了的地方,就跟看恐龍的意思一樣,所以自然而然,牠就成為一個旗艦或標誌性的明星物種。」
徐振輔的第一本書《馴羊記》寫的就是「尋找雪豹」這件事。只不過,尋找雪豹就像個線頭,輕輕一扯,就牽引出更多交織其中的關於西藏的一切,涵蓋人類學、文化、政治、歷史、宗教和生態。本書雖是一本小說,讀來卻像是散文集與人文科普的集成。
「小說沒有邊界,我想把很多超過自身經驗的東西都放進來。」於是對徐振輔來說,《馴羊記》只能是小說,夾藏著他想以「一本書寫盡西藏一切」的企圖。大三那年,當時就讀台大昆蟲系、一心想當昆蟲學家的他,前往廣州中山大學當交換學生,因緣際會之下,一趟前往西藏拉薩的觀光旅程,讓他動了寫短篇小說的念頭,更開啟了長達數年的寫作計畫。
寫作的慾望一發芽,生長的態勢便無可阻擋。決定寫書後,甫入學台大地理研究所一個月的他便決心休學,為了雪豹、為了書寫,先後前往藏區四次進行田野考察。「當我開始動筆,自我經驗跟寫作目標會同時一直成長,愈寫愈覺得自己的東西還不夠,所以就又跑去那邊。當經驗、閱讀多了之後,才長成現在這樣一本書的規模。」
這項小說寫作計畫先是以《西藏度亡經》為題,在2020年獲得第21屆台北文學獎年金類首獎,而後歷經兩次砍掉重練、每篇章節反覆修改十遍以上,而得以長成《馴羊記》這部作品。

有趣的是,在寫書的時候,徐振輔沒有看到過雪豹,一次都沒有。
他回憶起後來真正看到雪豹的那次經驗。那天,他以為又是個日覆一日、重複期望又失望的一天,他早已不期不待。那時他隨著牧民的步伐,揹著重重的裝備、爬上海拔四千多公尺的山頭,突然,他聽到牧民哎了一聲說:有雪豹!「我們距離雪豹大概有三四百公尺,但我大概找了快十分鐘,什麼都看不到。他都已經告訴我在哪裡了,我還是看不到,」只見牧民將徐振輔的相機拿了去,拍下雪豹後,徐振輔再依據相對位置終於朝聖了他夢寐以求、心心念念的雪山之王。
早在徐振輔親眼看到雪豹以前,雪豹早已發覺了他們一群人,牠停下吃食犛牛屍體的動作,又緩緩往另一山頭走去,隨即另一隻雪豹從反方向出現,兩豹耳鬢廝磨一番後,雙雙消失在遠方的山洞。徐振輔的快門狂按了千次後才心滿意足地停下。沒想到一下山,戲劇性般地,他不小心跌進水裡,相機也跟著遭殃。不過,人生足已,夫復何求。
「其實看到雪豹後,過了幾個月,我突然渴望沒看到比較好,『沒看到』好像比較有文學性。」他笑說。

尋找雪豹之於徐振輔,之於《馴羊記》,或許從來都是找尋某種精神性意義的過程。
他是一個昆蟲迷,從小就常在野外與昆蟲為伍,家中的昆蟲圖鑑倒背如流,現在更復學專研螢火蟲。這自然也影響了他書寫的題材。早從高中時期,他的寫作才華就展露無疑,積累無數文學獎。對他而言,除了海明威、馬奎斯的短篇小說之外,影響最多的便是吳明益的作品。「吳明益老師的《蝶道》抒情性滿強,又滿足了某種知識性,既跨過自然科學背景的門檻,又把文學藝術的東西呈現出來,我非常認真的讀了好多次。我會把自己在野外的一些經驗寫下來,試著複製風格轉成自己的東西。」
做為一個被貼標為「自然文學」(或「自然導向文學」)出道的作家,徐振輔認為自己的自然經驗與寫作經驗是各自獨立的。「因為很早的時候,我覺得這標籤好像是一個影響著我的東西,比如說,好像被覺得要寫自然題材,或我寫的東西被視為自然書寫,我就會去想,什麼是『自然書寫』?所以我看一些約翰.海恩斯(John Hains)的書,」徐振輔不諱言地說,「其實大部分這領域的書我都沒得到啟發,我只是想要知道別人寫的內容。我認為自己最受啟發的,絕大多數是來自人文地理學和人類學的領域,簡直是受到巨大的衝擊。」
他體認到的是,現在要談自然書寫的價值,已和過去不同,不在於純粹的經驗描述,而是在於觀點。「現今的自然書寫,應該要放在當代的、21世紀的範疇去討論人與自然的關係。我們所面對的處境已經跟約翰.海恩斯、梭羅或瑞秋.卡森那時候完全不一樣了,像《末日松茸》就是在討論當代,我們會講一些像新自由主義這些詞。現在處於全球化,我們面對的人跟自然相處的難題就不一樣,甚至人跟自然這種二分的範疇,現在都會被挑戰。」

徐振輔想做的是試圖消解自然書寫的邊界,往外去去抓取更多養分,看看其他領域是怎麼討論人與自然的關係。他提到了推翻「人類獨特主義」,世界上的任何一個現象都不只是屬於社會的範疇,也不只是人的現象,但歷史進程一直以來都以人做為描述的主體,「我認為的環境文學或自然文學,其實是我們在觀看任何世界上的現象或是歷史發展時,都要把『非人』(Non-Human)的角色納進來討論,因為它們同樣是歷史的行動者。」
就像雪豹,徐振輔說,其實也有一個歷史軌跡把牠形塑成所謂的明星物種,「牠是被社會建構成一個超級有魅力的象徵,延伸來看,牠也是全球保育運動的一個政治行動者,牠影響了該地方是否能成立國家公園,以及這背後的全球政治角力過程。」隨著抽出雪豹這一線頭,背後關連的千絲萬縷也跟著牽動,這是他所關注的。
徐振輔想為自然書寫領域新闢一條路徑。西藏之後,下一個或許是北極、蒙古、婆羅洲,也或許,是螢火蟲。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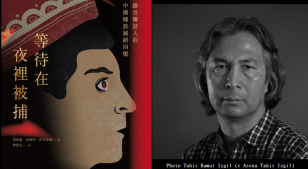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