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村上春樹也要開始歇斯底里了嗎?
說真的,在打開《棄貓》之前,我是憂慮的。不,我對歇斯底里並不盡然抱持負面的想法。如果把歇斯底里定義爲「憶起難以憶起之事的能量亂流」——那麼,歇斯底里未必不是言語的源頭,或說文學與真誠的源頭。不過,村上春樹在我的理解裡,一向是這種樣態的克服者,而非嗜好者——如果他歇斯底里,不論結果好壞,讀者面對的,至少會是種「村上的消失」。

「只有更小我,沒有更大我」——這是我在村上書寫裡一貫看到的姿態。其中存有會退化成最保守反動的心智,成爲如英國柴契爾夫人名言「社會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的註腳 ; 但另方面,從「小小我」守衛起,也可看作,對「小我」備受威脅的警覺。是拒絕進入空洞大我之集體主義惡夢的抵抗。從這個角度來看,村上文學的戰鬥意義,也可說是「個人這種東西不是不存在的」。 不過,無論如何,此類作者接手承載過多歷史意味的符號,若非作繭自縛,搞砸的機會也很大。
因此,我讀«棄貓»,是從一身冷汗開始,結束於大氣呼出:沒搞砸,沒媚俗,沒有老來瘋。法語中有個表達很適合:le boucle est bouclé。直譯是「環已扣上」,也可譯成「該完結的完結了」,或「大功告成」。另一個可比較的是鈞特 · 葛拉斯的«剝洋蔥»——我對葛拉斯的責備不在他犯錯或拖延,而在他「以爲交出自己可以取代交出文學」——也許村上春樹真如他本人所說「不擅長觀念性的思索」,可就是因為「別無依恃」,使他能單刀直入,問答:「那是什麼?那是......」。
這個一生無法迴避的題目,容我無趣地將它濃縮,那就是,「我的父親曾經是個反人類嗎?」
«棄貓»一度讓我熱淚盈眶,就在於村上春樹並沒有選擇輕易的「是或否」。——這是「驚人勇敢的懦弱書寫」。「棄貓」出現了兩次,「海邊奇蹟」與「小貓上樹」,是典型的村上故事。鮮明的意象,令人想起,很難超越的新美南吉經典,《小狐狸阿權》。也是坂口安吾在《墮落論》中談童話時,述及的「清澈的殘酷」。然而,最可注意的,還有貫穿全文的「與最糟擦身而過」的「僥倖感」。

僥倖的簡化版是「幸運」,然又有差異。僥倖比幸運彷彿更值得欣快,運氣得來不易,且自己本身有什麼東西,是配不上的。「僥倖」顯露的笑臉,隱藏著最深的淚眼。
«棄貓»最核心的「僥倖」就在以下情節中:村上春樹一直以為父親曾參與南京大屠殺(南京攻略),這使他提不起勇氣探問父親的歷史,但在調查過程中,意外發現父親至少,沒有參與37年的南京戰。作者「忽然鬆了一口氣」——這是很難堪且「並不十分得體」的「hó-ka-tsài」,但也是「人之常情」。沒有讓良知蒙蔽了「其他真情」,這是文學可貴之處。
試想,村上是抱著就算父親參與過南京戰事,也要去面對的心情,這種煎熬緩刑,大概是百萬箭穿心與萬箭穿心之別吧!「最糟」並非消失——自己的父親沒打南京,總也有別人的父親打了。
如果翻過«昭和史»(半藤ㄧ利著),對於日本戰後如何在國際勢力強壓下服從,從軍國主義轉向和平,卻在戰爭責任與國家歷史問題上,像「辦家家」一樣,表面工夫充斥—— 應該會印象深刻吧。在日本速成民主的過程中,還有「十二歲少年無責論」[1]出現,這都相當不利歷史的思考。
我自己的「中日戰爭」印象,最多來自童年讀物《四世同堂》。這使我讀到日人言及戰時苦,仍會直覺拌嘴:沒讀老舍?而我並不贊成自己這種直覺式的反彈。儘管反彈無關民族主義,只是對「奪食之恨」耿耿於懷罷了。在台灣,對日本人的情感,往往受到多種情結干擾,因爲不同身世傳承了不同記憶。但是,記憶不該作爲封閉的理由。台灣做爲中國與日本文化延長線的交叉點,像龍瑛宗等,「在民族主義之外思考」,可説起步甚早。只是這條台灣文學的生命線,太受壓抑。
我一直覺得,最能代表村上的,是彷彿「小說家業餘」的《地下鐵事件》與《約束的場所》。其中寫出「災難的非同質性」,與«棄貓»併看,會有更深體悟。«棄貓»起點是父子關係,其實在這個概念的內涵上,做了「離合不斷」的「換藥不換湯」,可說是深心所在。在這一點上含糊以對或隨便嫁接,就有可能錯失«棄貓»最根本的暗湧與地平線。讀者不妨留意些,切莫以爲那些只是抒情口吻——就像他筆下流露的幸運,不能只以幸運解,筆下父子,亦復如此。
這人穿過了歇斯底里的風暴,是更回歸村上春樹的村上春樹。他憑藉的不是自苦的揭秘或告解,而是,文學的初心之力。

[1] 代表盟軍的美國麥克阿瑟在回答美國參議院質詢時表示,德國是在意識之下發動戰爭,日本人則似「十二歲少年」,對國際情勢毫無概念。由此衍伸出「十二歲少年無責論」。針對美國帶領的性別與種族歧視,可參考澀沢尚子的文化批判,《美國的藝伎盟友》。
作者簡介
1973年出生於台北木柵。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及視聽研究所碩士。早期作品,曾入選同志文學選與台灣文學選。另著有《我們沿河冒險》(國片優良劇本佳作)、《小道消息》、《晚間娛樂:推理不必入門書》,長篇小說《愛的不久時:南特/巴黎回憶錄》 (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短篇小說集《性意思史》。散文《我討厭過的大人們》。
OKAPI專訪:「我不願意說一些雞湯與金句,告訴你如何做人。」──專訪張亦絢《我討厭過的大人們》
【棄貓特別企劃】當他們談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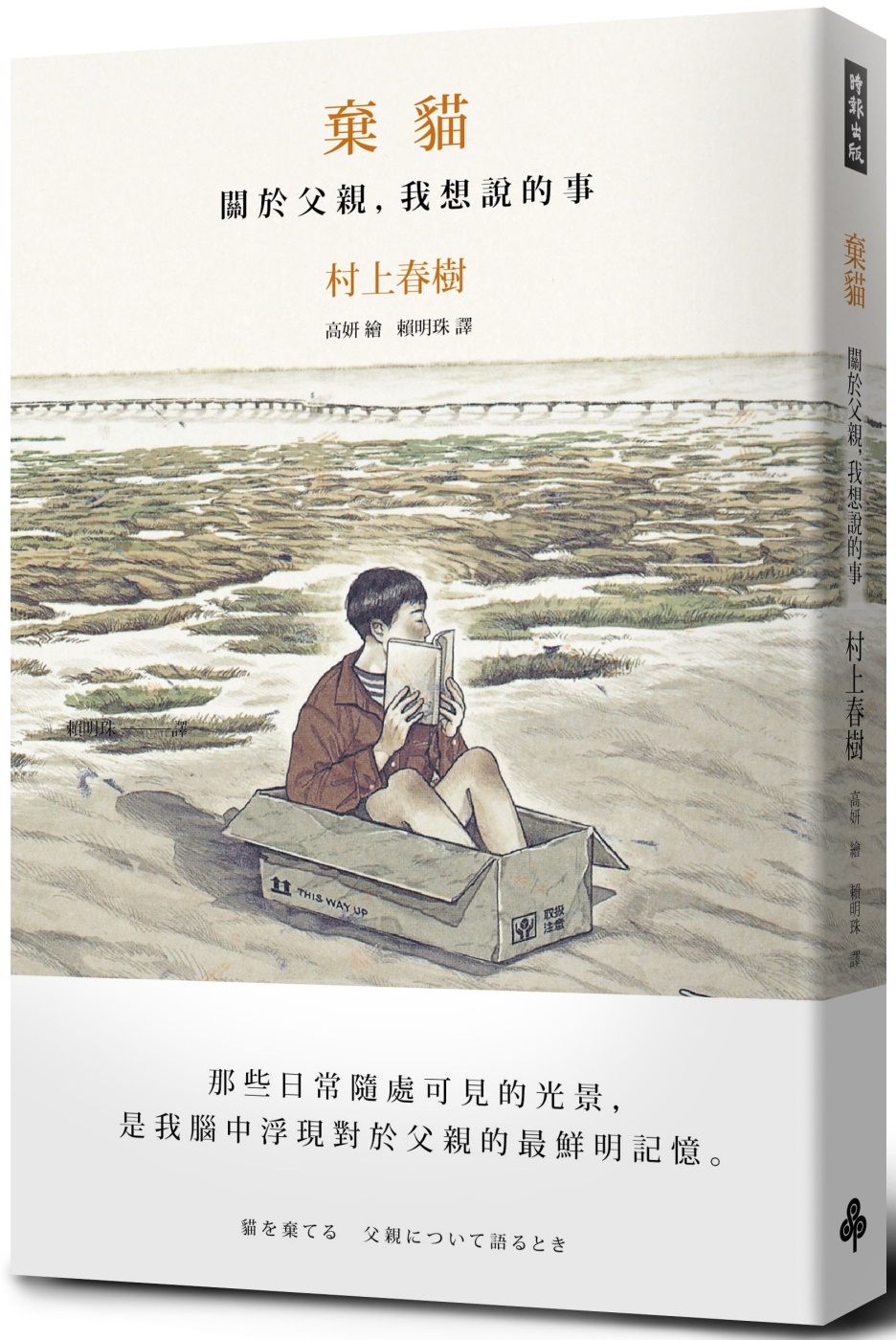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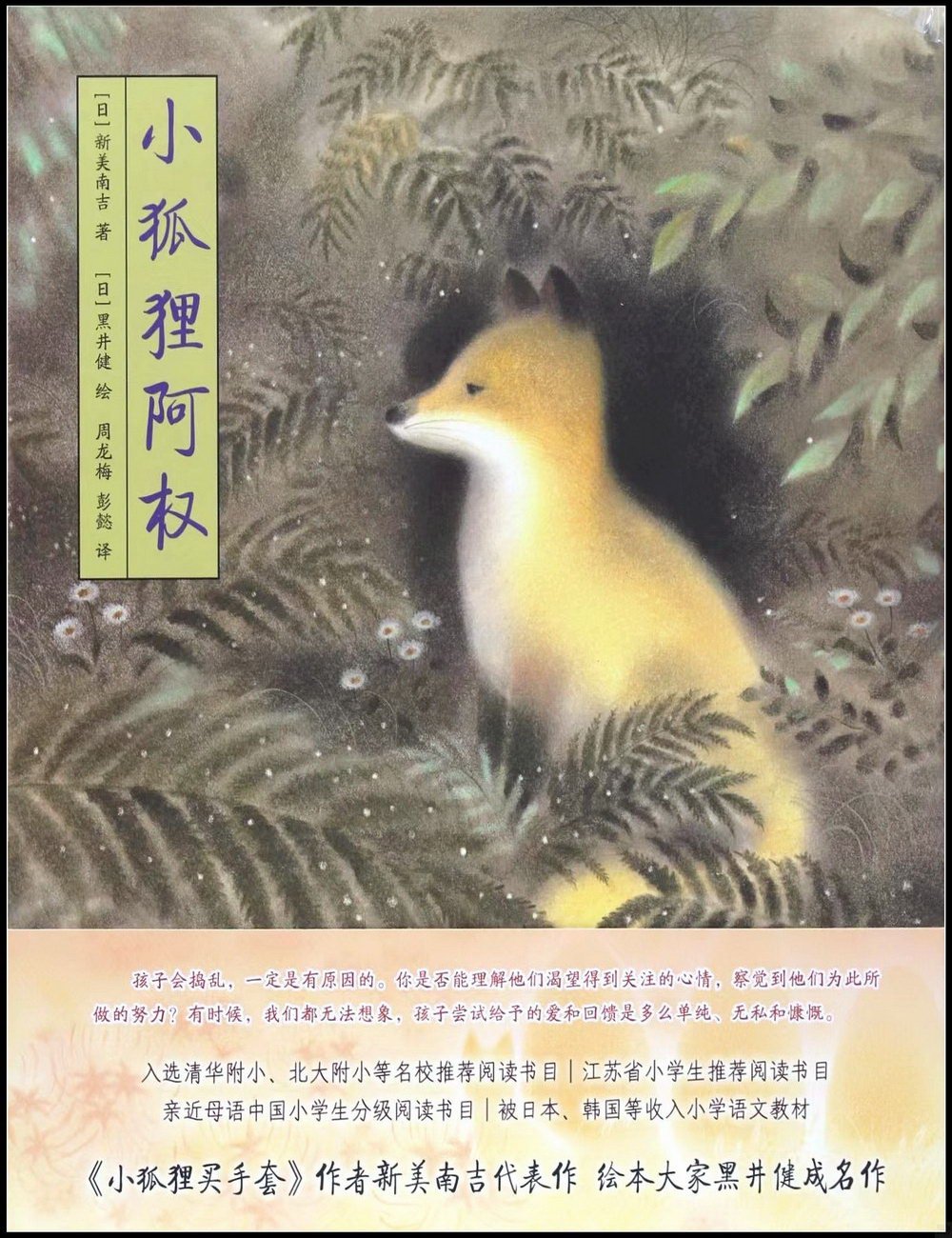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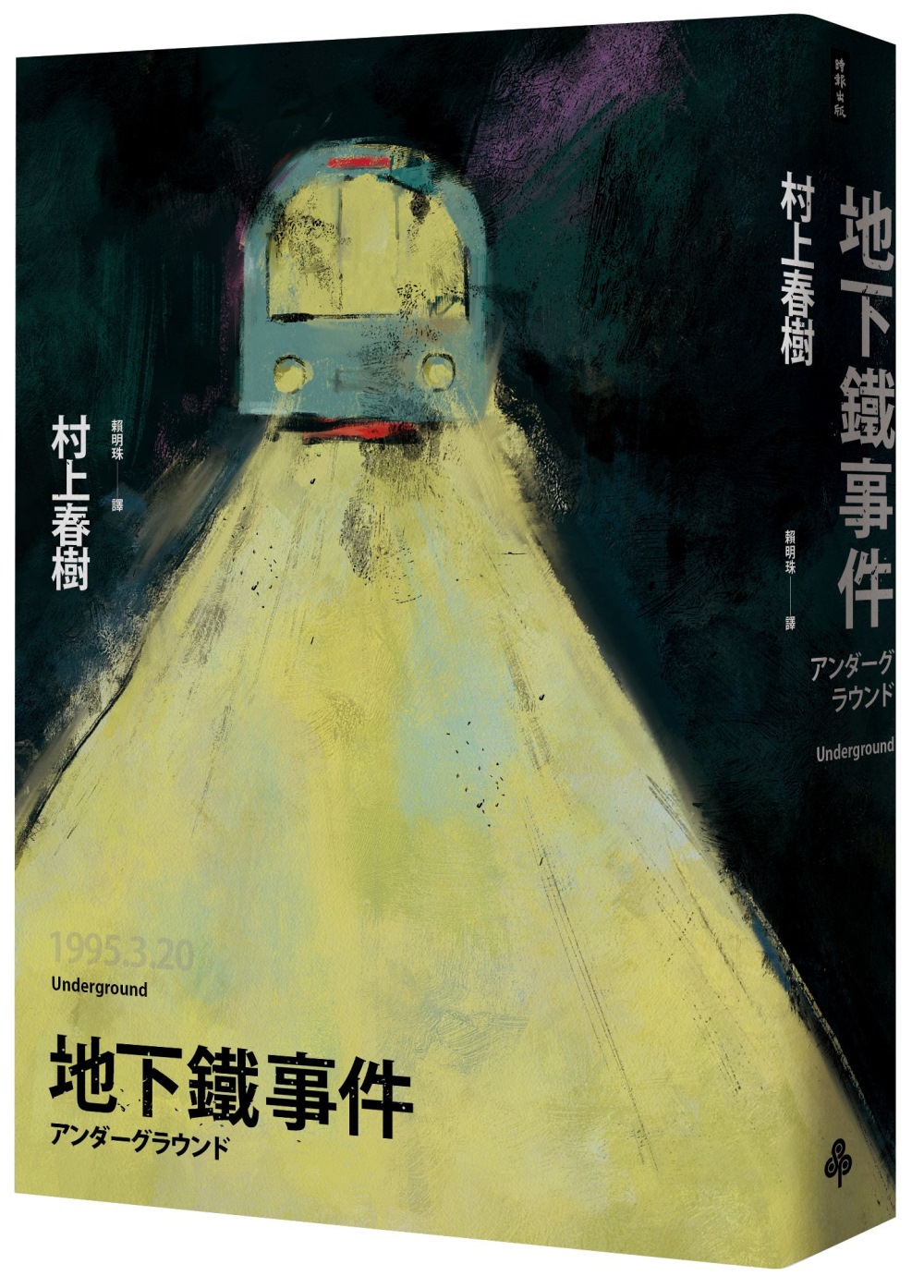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