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科幻大獎雨果獎的最佳小說獎,頒給了中國作家劉慈欣的《三體》(The Three-Body Problem),這是雨果獎史上第一次頒發給「中國」作家。《三體》獲獎之後,在全球引發熱潮,迅速賣出多國版權,總銷量據傳高達九百萬套,不僅使世界科幻文壇注意到來自東方的科幻小說,也讓劉慈欣一躍成為中國最炙手可熱的作家之一,頻頻出席中共官方活動,作品也被收錄至學校課本以及高考考題之中,舊作《流浪地球》的改編電影更成為中國影史票房第三高的作品。
中國媒體的宣傳無不將焦點放在劉慈欣的「中國」身分,頻頻以「中國科幻小說」、「征服」等字眼描述《三體》的成功,西方主流媒體的接受也相當類似,將所謂中國科幻小說的崛起,和現實世界中國的崛起以及世界局勢互相連結,塑造中國即將「入侵」西方的形象。用《三體》法文版譯者關首奇(Gwennaël Gaffric,也是吳明益小說法文譯者)的話來說,《三體》在西方世界獲得接受,很大一部分受「東方主義」以及「自我東方主義」的影響。

除了《三體》法文版(圖右),法國譯者關首奇也翻譯吳明益小說《複眼人》、《天橋上的魔術師》、漫畫家小莊《80年代事件簿》和夏宇詩集《Salsa》等台灣作品。(圖片來源 / babelio)
然則,在這樣的現象背後,大多數媒體卻忽略了作家、乃至譯者本身的敘事及立場。即便劉慈欣被譽為「單槍匹馬將中國科幻提升到世界水平」,仍是需要依靠優秀的譯者,才能跨越語言隔閡,將高水準的作品譯介至世界舞台。而《三體》英文版譯者的特別之處,在於他最為人熟知的身分其實並非譯者,而是和劉慈欣同樣身為科幻作家、更早在2011年就以短篇小說〈摺紙動物園〉(The Paper Menagerie)獲得雨果獎、星雲獎、世界奇幻獎等大獎的劉宇昆(Ken Liu)。
劉宇昆出身於中國,年幼時移民美國,因此精通中英兩種語言,或許是出身背景使然,劉宇昆靠著結合科幻與東方元素的作品,漸漸在科幻文壇嶄露頭角,並橫掃多項主流科幻大獎,可以說他本身在西方科幻文壇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至於劉宇昆的翻譯生涯,則是起於另一名中國科幻作家陳楸帆,他在讀到劉宇昆的作品後主動聯繫,科幻作家才踏上了譯者之路,並對中國科幻的譯介產生深遠影響。

《三體》英文版譯者劉宇昆的代表作為《摺紙動物園》。(圖片來源 / 劉宇昆官網 © Lisa Tang Liu)
劉宇昆除了翻譯劉慈欣的《三體》、陳楸帆的長篇小說《荒潮》(Waste Tide)、以及郝景芳的〈北京摺疊〉(Folding Beijing,2016年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也翻譯並編輯兩本當代中國科幻短篇選集《看不見的星球》(Invisible Planets)及《碎星星》(Broken Stars),不僅收錄以上作家的作品,也有其他中國科幻作家如馬伯庸、夏笳、韓松等人的作品。

而針對上述這種聚焦於「中國」標籤,而非作品本身的詮釋,劉宇昆在選集《看不見的星球》前言〈中國夢〉(Introduction: China Dreams)一文中,便大大駁斥了以地緣或國籍詮釋科幻小說的看法(以下引文為筆者翻譯):「只要提到『中國科幻小說』,西方讀者總會問:『中國科幻小說和用英語寫作的科幻小說有什麼不一樣?』我的回答通常讓他們很失望,因為我總回答他們,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中略)……試圖為這個問題提供簡單的答案,只會產生無謂的過度簡化,或是再度強調既有偏見的刻板印象。」
此外,在其他訪談中,劉宇昆也曾多次重申類似觀點,談及作品中的東方元素時,他表示:「我認為我們生活在『全球』文化中,所以我不特別關注『中國的』、『芬蘭的』、『法國的』、『古希臘的』、『日本的』,或『盎格魯薩克遜的』等等的分野。我寫作是為了自己,我是人類的一份子,所以我挖掘全人類曾發生過的故事,用我的筆展示世界的樣貌,以及世界未來可能的變化。」而被問及政治相關問題時,他則回答:「其實,我著墨的不是這些主題。我寫的是人類的處境,和所有與之攸關的事,包括:科技、歷史、哲學、政治、科學等,是這些構成了人類今日的生活樣態」、「我寫的是具有人性的小說,不論讀者透過哪一個標籤找到我的作品,我都希望他們能看到使我們結合在一起的、人性中有著光亮的部分。」他在《三體》英文版的譯後記也提及,在翻譯時「我也試著盡可能避免將西方的詮釋,套用在書中和中國歷史及政治有關的段落。」
其實這樣的看法,和劉慈欣的觀點不謀而合,即便劉慈欣時常出席中共官方活動,在中國也相當受歡迎,但談及自己作品時,他大都避談政治相關議題,僅表示身為作家,最重要的就是「試著把故事說好」。劉慈欣在《三體》英文版後記中也提到,「身為一名從科幻迷開始的科幻作家,我寫的小說並不是一種批判眼前現實的方式。」並認為,「科幻小說是屬於全人類的文學,描繪和全人類共同利益相關的故事,因而應該是最能受到不同國家讀者理解的文學類型。」
而從《紐約客》雜誌的專訪〈劉慈欣的世界大戰〉(Liu Cixin's War of the Worlds)中,或許可以稍微推測出劉慈欣對中共的真實態度,該文作者為一名華裔記者,於2018年陪同劉慈欣到美國華盛頓的亞瑟.克拉克協會領獎,這篇文章即是當時的訪談內容及過程記錄。這名記者深知劉慈欣大多避談政治,但仍找到機會詢問劉慈欣針對中國政治議題的看法,使劉慈欣說出,「中國人根本不在乎這些(人權和自由),對一般人來說,他們關心的是看病要花多少錢、房地產市場、孩子的教育,而不是民主。」但他之後也表示,「如果中國真的變成民主社會,那一定會是一場大災難,我隔天就會馬上跑去美國或歐洲。」
先前也有傳出《三體》在中國發售單行本前(《三體》原是在科幻雜誌《科幻世界》連載),為了規避審查,而將故事開頭和文化大革命有關的情節移至中段。或許創作科幻小說,和現實世界之間的關係,也正如劉慈欣所述一般曖昧難辨:「然而,我也不能完全脫離並拋棄現實,就像我無法拋棄我的影子一樣,現實為每個人烙下無可抹滅的印記,每個時代都替生活其中的人們戴上看不見的鐐銬,而我也只能戴著鐐銬跳舞。」
總而言之,劉宇昆和劉慈欣所要強調的,無非就是科幻小說之中所彰顯的人性或普世價值,背景可能設定在東方、主角也可能是中國人,然而故事要探討的,絕非只是政治如此簡單,也不是用「中國科幻小說」或「東方科幻小說」這樣的簡單標籤就可以概括。
像是《三體》的背景雖是設定在文革期間,由於中國科學家葉文潔向外太空發射訊號,使人類文明將在四百年後面臨浩劫,但這部長達近百萬字的巨著,探討的其實是「人類」做為一個群體,面臨生存危機時該如何自處,倫理道德又會如何發展,結合扎實的科學理論與劉慈欣壯麗恢宏的敘事風格,使其有別於一般的「硬科幻」小說。
而劉宇昆的短篇小說集,《摺紙動物園》中所收錄的數篇作品,也都是藉由東方的背景設定,來彰顯全人類共通的人性。例如〈測字〉(The Literomancer)描述一名在60年代隨美國父母來到台灣的女孩,如何於鄉下結識國共內戰後逃難至台灣的逃兵,情節夾雜有關中文象形字的軼事,最後則以戒嚴時代的悲劇收尾。而〈跨海隧道〉(A Brief History of the Trans-Pacific Tunnel)的背景則是設定在架空的歷史,那個時代對日抗戰沒有發生,日本順利躋身強國之列,為了因應美國隨後發生的經濟大蕭條,日本政府提出了建造橫跨太平洋海底隧道的計畫,敘事者是來自台灣的工程師,隨著故事進展,挖掘隧道時隱藏的祕密也逐漸揭露……。〈終結歷史的人〉(The Man Who Ended History: A Documentary)則以紀錄片方式,描述日裔及華裔美籍科學家夫婦,發現了能夠讓人回到歷史事件發生當下的粒子,本意原是揭露二戰期間日本731部隊在中國東北的暴行,卻引發一系列有關「歷史」為何,以及浩劫受難者生命史的辯論。
近來也出版了不少東方背景的科幻作品,例如台灣科幻作家許順鏜的《傀儡血淚及其他故事》、葉言都的《海天龍戰》(新版書名《綠猴劫》)都重新出版,也有來自日本,描寫人類與海洋關係的《華龍之宮》等,台灣作家高翊峰的科幻作品,例如《幻艙》及《2069》等,也由前文提過的法國譯者關首奇譯介至法國。可見「科幻小說」的書寫,並不受時空或語言所侷限,如同科技始終來自人性,科幻也始終描寫人性,因而這個疫情當頭、考驗人心的時代,或許也正是最適合閱讀科幻小說的時代。
楊詠翔
目前就讀於台大翻譯碩士學程筆譯組,喜歡讀奇科幻跟偵探小說,每天都要聽重金屬音樂,還在畢業跟成為自由譯者的路上跌跌撞撞。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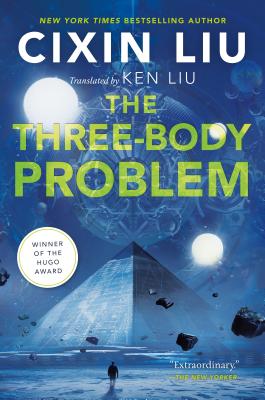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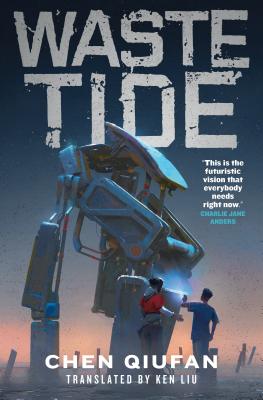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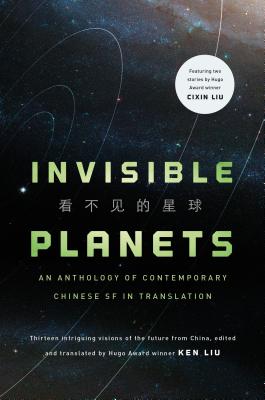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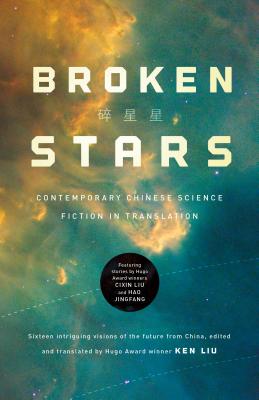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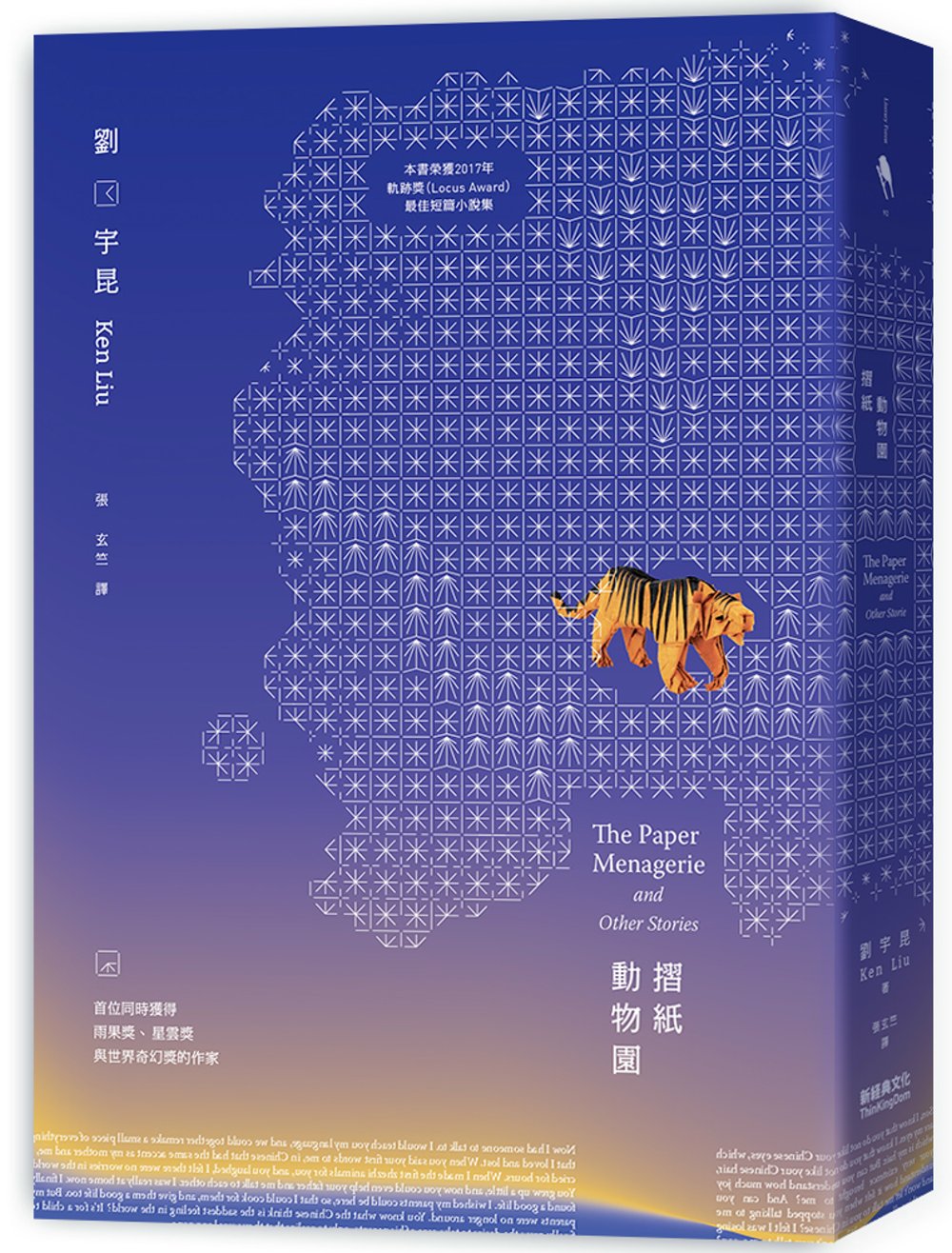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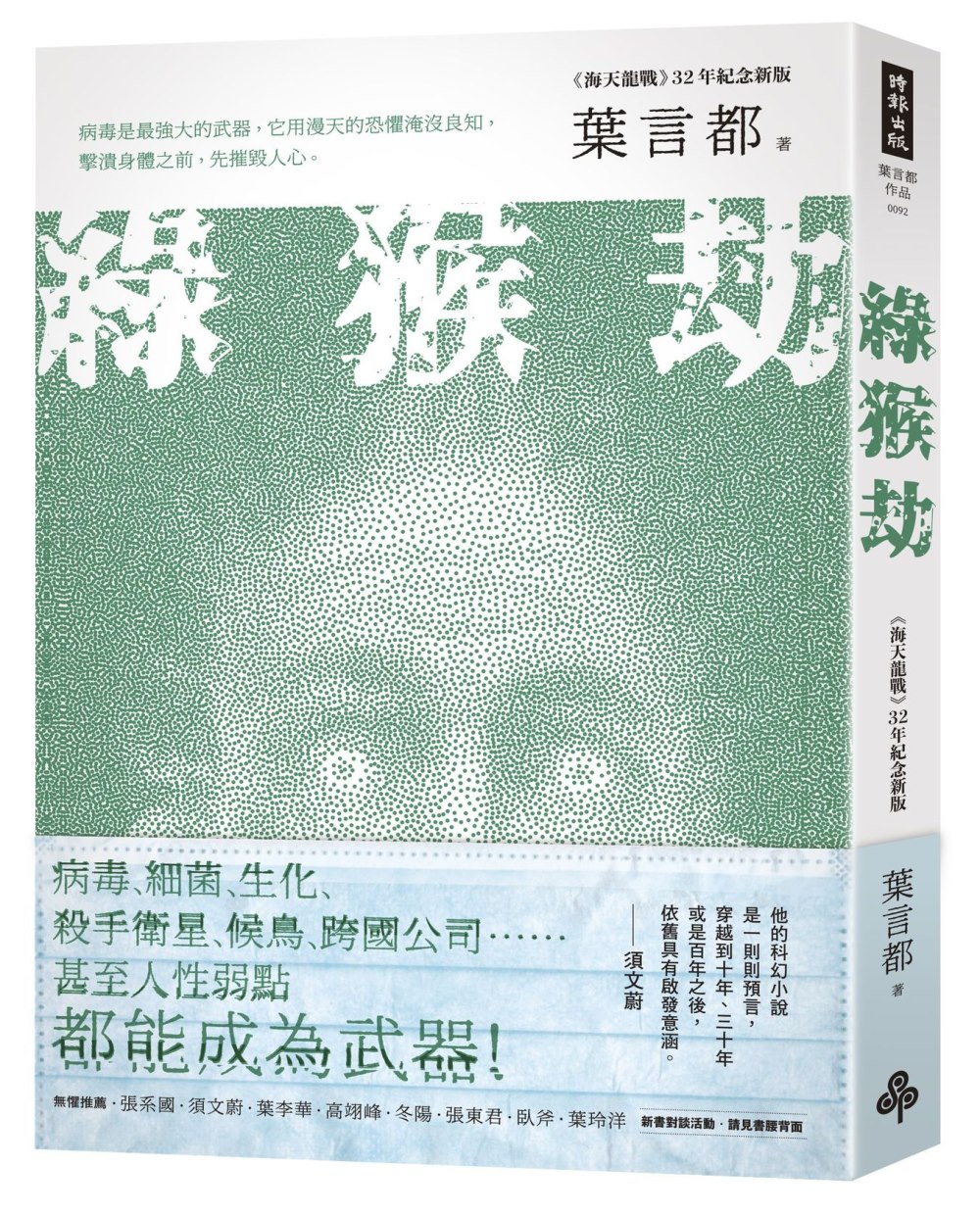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