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電影散場後,它會在你的記憶裡繼續演下去。
有時只是一幕景色、有時是個角色的身影。
看似人走茶涼的一幕,卻讓你也活了進去的燈火未滅、溫度仍在,角色隨時可以回來,你總感到似曾相識。
如《新天堂樂園》膠捲中的一格,記錄了太多意在言外。
為什麼?因為它照亮了你人生中的一瞬之光,相信它是永恆,而你的心仍有星火不滅。
※本文可能有劇透,請斟酌閱讀 當人置身戰場有如被放諸於異境,那種異境感只有在文學家如布魯諾舒茲的筆下,你才能感到那「異境」是如何改變了人所看到的、所感受的、以及心靈所被摧殘的。《1917》則拍出了人記憶與現實的交互扭曲,導演山姆曼德斯,如在下士史考菲內新裝了內視鏡一般,以文學的細雨下遍了他內在的深淵與山丘。
當人置身戰場有如被放諸於異境,那種異境感只有在文學家如布魯諾舒茲的筆下,你才能感到那「異境」是如何改變了人所看到的、所感受的、以及心靈所被摧殘的。《1917》則拍出了人記憶與現實的交互扭曲,導演山姆曼德斯,如在下士史考菲內新裝了內視鏡一般,以文學的細雨下遍了他內在的深淵與山丘。
人的一生,或是他的記憶,往往是像張桌布打開於五月的陽光下。窗外的光朗朗而至,那布面有著亮面也有著縫隙,人們只顧著瞧它在光下的花色,但縫隙中才藏著更多未露臉的真實。
當人在面臨極大的考驗與悲劇時,所見所思都進入一種疑幻似真的畫面,記憶也跟著扭曲。命運來得措手不及,人總還記得那天早餐的味道,也總以為這只是尋常的一日。如《1917》兩小兵去見將軍前,他們還在吃著偷藏的火腿麵包,布雷克仍說著:「這吃起來像破鞋皮。」當時的布雷克還在想著下周的休息日被取消。
這是這部電影不同於其他戰爭片的原因,兩小人物無意當英雄,他們心念的是小日子,布雷克當兵是以為可以吃飽點,史考菲埋怨為何這送信的倒楣差事要輪到他。沒有烈士的熱血,只有在關鍵的一刻,他們在當下選擇了良知。
 身負重任的兩個小人物無意當英雄,他們心念的是小日子。
身負重任的兩個小人物無意當英雄,他們心念的是小日子。
人置身戰場有如被放諸於異境,這是李安在《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想法傳達給觀眾卻功虧一簣的。那種異境感只有在文學家如布魯諾舒茲的筆下,你才能感到那「無人知曉的時空」是如何改變了你看到的、你感受的、以及你心靈所被摧殘的。
如一個人置身那無法呼喊也不可能求救的無人異境中,李安試圖用科技來傳達,而山姆曼德斯則以傑出運鏡,將故事去蕪化地放諸於滿滿戰火的邊緣,讓人在瘋狂的懸崖旁,感受到所謂人心的荒境是什麼。如芥川龍之介《地獄變》裡的畫師在發現陷入火海的是他女兒時,他看到的已非現實的那一面,而是走入癲狂境界。這比炮火四射與血流成河,更能讓人感同身受。

曼德斯在繼《美國心玫瑰情》的塑膠袋飛舞之詩,又一次以畫面讓人感受卑微與偉大的接近。他作品的文學性仍然強大。
主角史考菲人腦子生生被切斷了線路一般真空,這是曾失去過摯愛或是面臨巨變的人才知道,砲火就在眼前,自己也在殺人,尤其在夥伴布雷克被刺死之後,他的眼耳口卻如被綁入無人之境裡,發出不存在的尖叫。這種記憶與現實的交互扭曲,是電影《1917》在美學上最大的成就。有人說這故事簡單,但大道至簡,人心的傷痕是深掘,導演山姆曼德斯與攝影羅傑迪金斯,如在下士史考菲內新裝了內視鏡般,以文學的細雨下遍了他內在的深淵與山丘,讓戰爭片進入一種新層次。下士史考菲不曾求救,他在上了其他連兄弟的車後,並沒有因此放鬆一點,那一幕演史考菲的喬治麥凱演得好,眼神的火光熄滅,一顆心相對於身體的堅持,早已飄零如破褸。
也如他在一陣襲擊後,跑到埃克斯特小鎮那一幕。攝影狄金斯用他的光影,呈現出一種魔幻寫實的效果。有時心靈就像是個投影機,每個人投射出來的景象都不一樣。史考菲到達一個被轟炸到只剩斷垣殘壁的古老教堂,那幽夜中黃光與十字架,讓他看傻了眼,那看似是有一個極美的夜空,與片頭的花海呼應,人的心好像可以得到一點安慰,戰火就襲來。

 光影下的場景極美,對比戰爭更具衝擊。
光影下的場景極美,對比戰爭更具衝擊。
他與布雷克都不像是都市人,兩人來自單純的地方,看到那曾經響起鐘聲的地方,是鎮上人的重心,他在自己日常的記憶中混淆著,那一點點類似太平盛世與家的溫暖,讓他不知現在與過往何者更真實。
那一幕除巨大的廢墟,更多的是歸人之心,「家」有時是很抽象的,可能是一點飯香,可能是因他看到一婦女帶著嬰兒的畫面,那婦人為他清理傷口,讓人想起想家之心,哪怕是表明討厭回家的史考菲,也對「家」有了停靠的想像,至少他想起了別人的家,想起了一群人曾有的家。
於是他穿過了小河與裡面的浮屍,到了岸上時會放鬆警戒痛哭失聲,太漫長了,那記憶被撕裂,那日子被破壞,每一刻都是扭曲變形的時間(如諾蘭《敦克爾克大行動》的配樂),當時間具象了,自己的生命就像沙漏一樣,無法靜止的心靈恐懼,是近代的戰爭導演所想掌握的。
 他穿過了小河與裡面的浮屍,到了岸上時會放鬆警戒痛哭失聲。
他穿過了小河與裡面的浮屍,到了岸上時會放鬆警戒痛哭失聲。
這趟送信之旅,被導演拍成心的速寫。除槍林彈雨與德軍的機關重重,還有任務的倒數計時外,「心」才是導演要傳達的,史考菲大可以因惜命而放棄傳信;讓二營的人踏入陷阱而死,但每一次的死裡逃生後,他都沒逃,仍去完成一個可能無人追憶的英雄事蹟。他沒有豪情壯志,只是這大戰殘酷得近乎魔幻,讓史考菲從他說他不想回家,到他因此知道「家」真正意義是什麼。
不是指家庭的破裂與否,而是他那顆磨損不堪的心有了安放的地方,無論是大到一個城鎮,還是小到一個玄關的記憶。
因此迎來了這部電影最經典的一幕,他在樹林裡聽到熟悉的英國老民謠,起先那歌聲很稀微,像個不可能的幻象,失神的他跟著歌聲走到一批英國軍人中間,那群看來20歲不到的小兵們聽著〈I Am a Poor Wayfaring Stranger〉,歌裡唱著:「我是一個可憐的流浪者/獨自穿越這個世界/在我所去的那片光明的土地上/沒有疾病,辛勞或危險/我將回家去看看母親/還有我所愛的人」那時是在開戰前夕,男孩們疲累不堪,那一幕是「家」的記憶暫留;是自己所剩不多的相信,這幕讓人想起影集《冰與火之歌》的好,世界愈不堪與對「家」的執念愈強大,如凜冬的火苗,成就了史塔克家族後來的倖存。

史考菲不斷喊著要送信,穿過人牆,每晚一步就多一人喪命,那一條沒有路的路,正是這男孩回家的路。「家」代表著人仍所相信的事物。《1917》不只是部戰爭片,它更是魔幻寫實中對「存在主義」的呼應。
《1917》是一部2019年英國和美國合拍的戰爭片,由山姆曼德斯執導並與克莉絲蒂克倫斯共同撰寫劇本,故事主要描述兩名年輕的英國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穿越槍林彈雨,傳達重要情報,試圖阻止一場對數百名士兵的致命攻擊──其中包括布雷克的親兄弟。《1917》在第77屆金球獎上獲得最佳戲劇類影片和最佳導演。在第73屆英國電影學院獎上提名了9個獎項。成功奪下最佳電影,最佳英國電影和最佳導演。在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獲得10項提名,獲得最佳攝影、最佳剪輯、最佳視覺效果、最佳混音4個獎項。此片爛番茄指數也高達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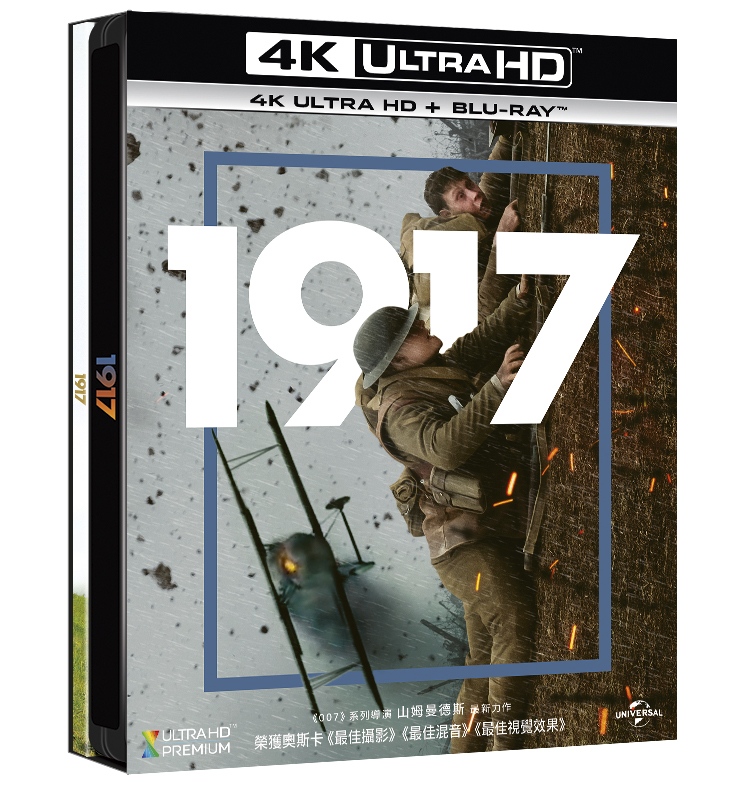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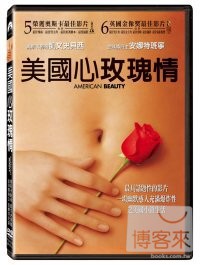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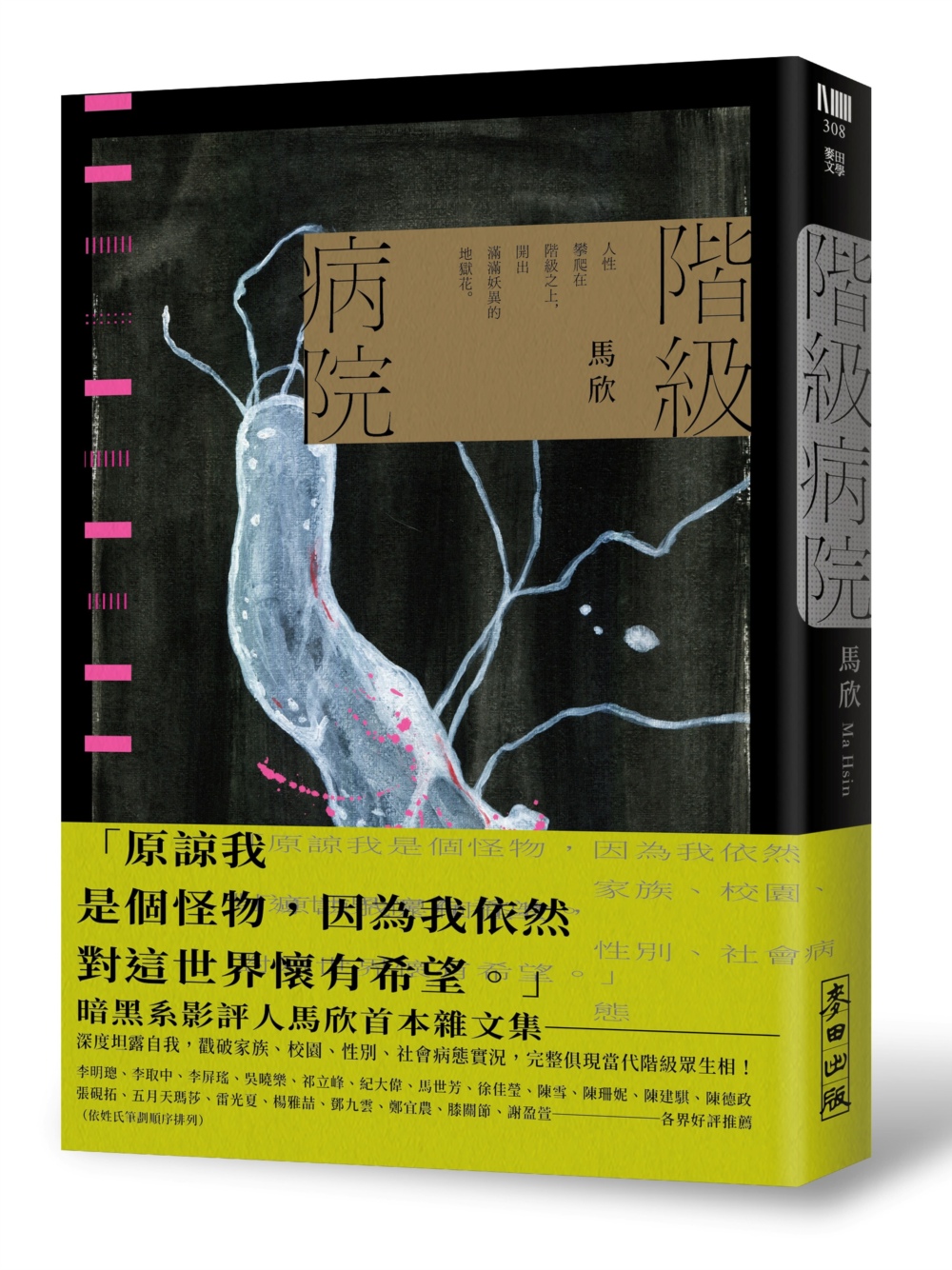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