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讓人以最快的速度走向刀鋒,承受真實的銳利和虛幻。詩人並非欲望書寫,他欲望揭露真實,觸探事物和人心的邊和縫,才戒慎、狂喜地寫下他的涉險。
涉險躍入存在的深淵,直面真實。書寫的文法和邏輯,不過是為了追獵刀鋒上的生機和暗影。大多時候,舊有的羅網遠遠搆不著繁複、細膩、不斷變動的美麗生物。
就像義大利詩人、作家羅大里(Gianni Rodari)在《想像力的文法》尖銳地批判:「在看兒童作文時,學校都把注意力放在拼寫/文法/句法正確與否,連『語言學』層次都稱不上,更不用說對內容的複雜世界進行探索。問題出在學校看孩子的作文只是為了打分數、評斷優劣,不是為了理解。一味追求『正確』的結果是留下了糟粕還大力讚揚,卻讓金子溜走……」
我們的閱讀和書寫教育,沒有教我們直視真實所需的敏銳、耐性和勇氣,而是教我們編織一只粗糙、網眼空泛的網子──造詞、構句、布局章法、獻出合乎常理的情懷和價值選擇──這承襲而來的匠化之網,無法捕獲我們自己的心,也無法捕獲閃逝流動的細節、透過細節呼之欲出的真實面貌。我們在學校課堂練就了怎樣縱橫交織一幅假面,蒙蔽我們對真實的探看、逼近和追尋。每一個落下的字,都在逃離自己的心。
然而,要怎麼在課堂上為孩子揭來「真實」?「真實」要怎麼在眾人的目光下現身?文字如何再現「真實」?這是我十年來在實驗教育現場最急迫的追索和嘗試。如果,詩無所不在,真實也無所不是,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帶孩子「凝神細看」,因為目光凝聚之處,就是自己的每一次降生之地。細看之後才有更深的觸動、理解和對話,而後若動用詞語來書寫,是為了替感覺和思維找到棲居之處,找尋牢固精準的詞語來讓事物和情感再次鮮活地流動。

義大利兒童文學家、詩人羅大里 (1920-1980),1970年獲頒安徒生大獎。(圖片來源 / 羅大里百年誕辰紀念官網)
走向刀鋒,鍛鍊書寫的技藝才有意義。《想像力的文法》為了找回孩子指認和命名事物的熱情,為了將他們帶回刀鋒,羅大里提出幾種遊戲式的書寫引導:
- 拆解一個詞彙的所有字母,運用那些字母聯想出新的詞彙,串成語意完整的一個句子;
- 以一個詞彙做為故事發想的引線;
- 沿用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藝術家玩的剪字遊戲,拼貼組裝一首詩;
- 任孩子在字典上隨意指出兩個不相干的字詞,例如「燈」和「鞋」,編造二元相生的想像故事;
- 透過異想天開的假設,回應現實問題或搭建新的生命邏輯,例如,如果西西里島的釦子掉了,會發生什麼事?如果有一隻鱷魚在你家門口,想跟你要一點迷迭香,會發生什麼事?
文法不是書寫的目的,而是通向真實、引出真實的途徑。羅大里實踐的寫作遊戲,盡可能打破寫作的框架,解除孩子因襲而來的規矩和恐懼,讓孩子「不以日常角度思考詞彙意義,而是將詞彙從平時的語言鏈中解脫開來,被疏離、被錯置、被拋進從未見過的天空裡互相碰撞,找到最好的狀態生出故事。」他認為,「扭曲」詞彙是讓想像具有生產力的方式之一:「孩子會因為好玩這麼做,但這種『文字遊戲』的本質很嚴肅,可以幫助孩子探索詞彙的種種可能,支配詞彙,迫使詞彙往未曾嘗試的方向傾斜,同時激發『言說者』的自由,讓他們擁有個人詞彙,鼓勵他們不再墨守成規。」於是,孩子的心思不斷發散、動盪、開闢新路,在遊戲中感受「字」的身世和份量,他們自身的經驗也進駐到「字」的體內,撐起它來。
我的閱讀和寫作課,也是帶孩子走向刀鋒的一再嘗試。每一堂課,從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開始,我們書寫一張小紙片,寫完扔進一個空瓶,答案不被看見也無須分享,因而能夠誠實地攤開自我:羞恥是什麼?安全感是什麼?活著有意義嗎?活著的意義是什麼?什麼時刻或狀態讓你感覺到自己是一個「人」?什麼樣的時刻或狀態讓你感覺自己不是一個「人」?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你最不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前面這兩個答案有著什麼樣的關聯?
我們也會述說那些湧現在生活之中的詩意時刻,那些與生命對決的時刻。例如,15歲的男孩洗澡時,望著白霧蒸騰的鏡子裡自己漸漸被抹去,他不確定霧氣散逸,自己還在不在?某個夜晚,16歲的男孩獨自走過樹林,突然浮現一種不是美好也不是邪惡的感覺:「像是大自然伸出它的一隻手抓住我,它的本意不是展露可怕。」16歲的女孩說:「我最近蠻累的,什麼話都不想說,一直隔閡別人。星期一我走到黑暗的樹林那邊,坐著一直望著月亮,看著看著我就哭了。哭出來就好多了。」
我努力撤除課堂的框架,以及孩子對創作的想像,他們才能全然忽視我,來到一個信任的親密空間,如實袒露自我,不斷回到意願之中,不斷回到心靈的家屋。若以傅柯的觀點來看,我們只在事物具有意義時才擁有事物的知識,所以只有話語(而非事物本身)才生產意義。沒有任何形式的思想能夠在話語遊戲之外聲稱擁有絕對真理。於是,我設想各種寫作練習,令孩子走向刀鋒,創造他們自己的敘事和意義系統。例如,在有限的空間之中,選取一個物件來描摹自己的存在,詮釋物象的同時,將自我的某個面向揭示出來。或是,運用自動書寫的模式,以楊牧〈天干地支〉開頭的句子「水影下一個面具」為起點,三分鐘不停筆,擺脫自己既有的思考邏輯和掌握語言的習慣,順隨直覺寫下那些流動無名的意識軌跡。
還有,讀了周夢蝶的〈我選擇〉和辛波絲卡的〈種種可能〉,寫下自己的生命傾向,別忘了我們的選擇能夠說明我們是什麼樣的人,我們沒有選擇的那些、抗拒的那些、放下的那些,同樣也說明了我們是誰。讀了林亨泰寫的「植物還在萌芽的內側/動物還在出生的內側/世界終於面臨一個早晨」,我們書寫對「誕生」的認識與想像。
在名為「貝克特」的課堂上,我們閱讀愛爾蘭作家貝克特的詩和劇本,也閱讀作品之中的空白和沉默:《啞劇》最後那人靜立不動,注視自己空無一物的雙手;《終局》的終局,那人的雙臂垂到椅子的扶手,保持不動,場面持續片刻;《等待果陀》最後,一人問:怎麼,我們走不走?另一人說:好,走吧。然而,緊接這兩句對話的舞台指示,寫著:「他們不動。」;《克拉普最後的錄音帶》結尾,那人雙唇蠕動:「也許我最好的年歲已經過去了。那時還有個幸福快樂的機會。但是我不要它們再回來。現在我心中已無熱情之火。不,我不要它們回來。」舞台指示寫著:「克拉普一動也不動地瞪著前方。錄音帶繼續在沉默無聲中旋轉。」朝向未來,於是不動?或是不動,才能走進未來?
貝克特的人物總以等待永恆的姿態等到幻滅,再也無能行動,疲憊地發覺有限無法抓住無限。我和孩子將《等待果陀》劇中的這兩句對話:「你想上帝在看我嗎?」「你得閉上眼睛才行。」當成一首詩的開頭。18歲的沈薇寫下:
你想上帝在看我嗎?
你得閉上眼睛才行。
你才能去只有你能去的地方
離開和上帝沒有關係的世界
16歲的李向陽寫的則是:
「你想上帝在看我嗎?」
「你得閉上眼睛才行。」
「但這樣,我就看不見他,也看不見你了。」
「別擔心,如果我們真的存在,閉上眼後,我們會更真實。」
「不,我做不到,這樣好孤獨,告訴我,讓我知道你還在。」
而我們讀了貝克特的《啞劇》之後,討論劇中那人在怎樣的情況下會被「甩回舞台上」?反覆出現的「哨聲」和「沉思」有什麼樣的關連?手、樹、立方體、繩子和玻璃瓶的作用和意涵是什麼?那人在什麼狀況下「不動」?「不動」之後,發生什麼事?那些物件紛紛消失和他的不動有什麼關聯?綜觀全劇,他的「動」和「不動」具有什麼意涵?就像羅大里帶領孩子玩的寫作遊戲,我和孩子閱讀和討論了貝克特的《啞劇》之後,寫下它留在我們心上的詞彙──停頓、甩回舞台、沉默、樹、指甲、沉思、跌倒爬起來、哨聲、水、剪刀、回頭──每人隨機抽出兩個詞彙,發展一首詩。
13歲的女孩王日妤抽到「水」和「跌倒爬起來」,她寄了一首詩給我,她問:「這樣可以嗎?」我說:「不要想著交作業,妳要寫出自己真正的感覺和想法。詩是用妳自己的方式來捕捉妳自己的深刻。重寫吧。」隔天,她問:「要怎麼捕捉深刻的感覺?」我說:「誠實就好,不要追求美。誠實專注地面對自己,深刻就會出現。」她追問:「如果是一個畫面呢?要分開還是合起來寫?」我回答:「詩沒有規則,妳自己嘗試。」後來,我收到她重寫的詩,開頭寫著:
「跌倒爬起來」
它像是一句肯定句 我不喜歡
我想坐著
為什麼不坐著?為什麼要爬起來?
接著,她思索跌倒之後「坐著」和「爬起」的差別,她發現自己「還是得起來」,因為「坐著」是湖水,而「爬起」是溪水:
坐著 是封閉的
起來 它 在流動
她最後寫的「它」是什麼呢?那是一個跌倒的人願意再次相信生命,相信生命的變動和未知的可能性。沈薇抽到的其中一個詞彙也是「跌倒爬起來」,另一個則是「哨聲」。她寫下的詩:
卸下衣袍,絲質布料從肩膀滑落。他撫摸耳後直到鎖骨,一道鮮豔如玫瑰的割口。他不知道痛不痛。
在夜晚的松木林散步,她拿了樹下利如刀刃的石頭割開他的脖子。看到血她就覺得狂喜。
可能她有點自卑,於是和他做了不成文協議——聽到哨聲,他就要跌倒。
他細數疤、痂和傷。
她每次都在最高點吹哨。
他每次都摔得不成人形。
那天在松木林,他又一次情不自禁想用鮮血挽留她。她太興奮,拿石頭割一句宣誓主權的話。他沒有爬起來、沒有反抗,連哀鳴尖叫都憋在喉嚨裡。
這是愛嗎,他翻開傷口,看得迷惘,怕懷疑會反抗,反抗會失去。
那是愛嗎,她看了一地的血和自己的手,指甲縫裡還有乾掉的紅。
在她搞清楚之前,她不會放他走。
在名為「紀伯倫」的課堂上,我們隨著黎巴嫩詩人紀伯倫《先知》的每一篇章,寫下同名的詩文。我們寫過愛、死亡、美、祈禱、船來了、時間、深淵。寫完了,我們在課上朗讀,然後再讀紀伯倫寫的。紀伯倫就像我們的同班同學,只是永遠缺席。例如,17歲的男孩徐又喜寫的〈死亡〉:
鞋跟穩重前進的聲音在空間迴盪,直角從牆壁與地面間消失。
在冰冷的空氣中,死亡的動作依然優雅。
因為它,光線變得柔和不刺眼。
因為它,燈管變得沒那麼討厭。
因為它,我能夠更專注的看著每一個人。
順著手臂上的血管、肌肉、骨骼;順著他們的動作,喉嚨吞下口水時的蠕動;因為緊繃而微開的雙唇,
下巴
臉頰
皺紋
淚腺
眼睛。
這是它想讓我看見的嗎?生命彼此之間的張力!
不管是眼前那對緊握的雙手,還是窗外那憤世的街道、城市。
我發現我只能目瞪口呆的觀望著這一切。
一生,我擁有它賜予的一生的時間去明白它的唇語。
希望我多少能明白一點,這麼一來,到了我聽見它說話的那天,就能夠來場精彩的對話了。
每個人的問題只有最深的情感在最微妙的時刻才能自我回答。寫作的形式、想像力的文法,都是為了引領孩子透過特定的方式交出自己。等到掌握形式的能力圓熟,他們開始不受它的控制,任情感引領他們突破既有的規矩,長出一個全新的、貼合內容的形式。到了那樣的時刻,孩子的創作才變得真正自由,流動著無可抗拒的生命感。就像英國導演彼得.布魯克說的,我們需要準備,才能摒棄準備的一切。我們需要架構,也才能摒棄架構的一切。羅大里在帶領孩子進行寫作遊戲的過程,發現「 他們很享受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習慣對所有素材進行批判,包括白紙黑字。他們完全不知道什麼是考試和分數,他們做的事情不受任何官方計畫、千篇一律的教學活動或學校機構要求的控制,他們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明確理由,是發自內心之舉,所以每一刻都是『生命時刻』,而非『上學時刻』。」
羅大里在《想像力的文法》引用德國詩人、教育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在《美育書簡》提出的一段話:「當人具有最完整意義的時候,他才會遊戲,也只有當他遊戲時,才是完整的人。」席勒認為一個人唯有在這樣的審美狀態下,才能「透過自由給予自由」。羅大里開發一系列的寫作引導方法,激發孩子的創造力,因為他希望孩子不是文化的消費者,而是文化的生產者。做為一名實驗教育老師,我僅僅盼望孩子的每一次述說、每一次書寫、每一次為自己的存在命名,都是陷入困境又再憑藉力量爬出又再落入新的困境的動態過程。陷入困境就是走向刀鋒。面對那些難以面對的,就是走向刀鋒。最危險的刀鋒就是自己的真實,要怎麼走向它,如實看待,將它寫下?當我們開始走向刀鋒,這一生都無法停下了。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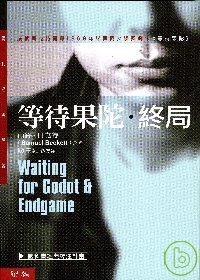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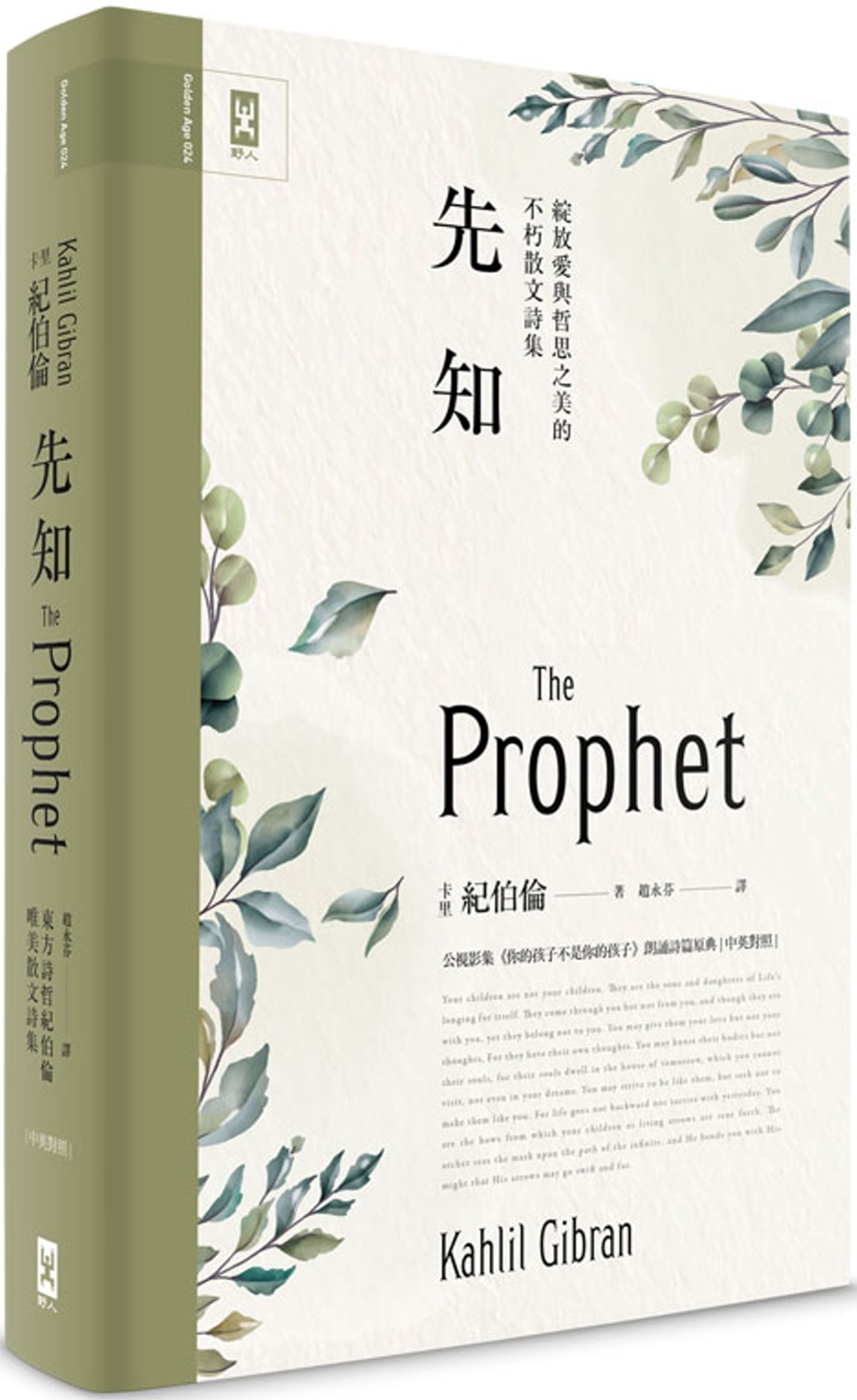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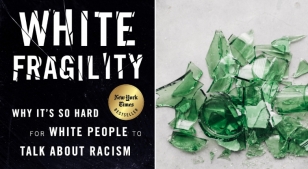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