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別人養鴨是費力如趕鴨子上架,朱一貴養鴨能讓鴨子列隊進退,如操練軍隊,而且每顆鴨蛋都保證雙蛋黃!」錢真說,在那個聽過傳說就能權充見證的時代,眾人咬定朱一貴養鴨有神庇佑,「鴨母王」一說不脛而走。再後來,康熙60年(1721年),朱一貴以明朝傳人為號召,率領傭工豎旗,抗議官府的苛刻重稅與隨意抓人。朱一貴部隊氣勢洶洶,甚至一度建國「大明」,年號永和,在臺南大天后宮登基為「中興王」,雖然50幾天後就被清廷從福建派兵來臺平定,卻是清代臺灣史上第一宗大型反清民變。錢真的小說《羅漢門》,便是根據這段歷史重寫而成。
歷史課本中,朱一貴事件是清朝三大民變之一,另外兩起為林爽文與戴潮春事件。錢真解釋,「這三大民變以朱一貴事件較單純,主要是針對官府苛斂濫權而起身反抗。林爽文與戴潮春事件還牽涉到天地會和八卦會,有幫派、泉漳械鬥與權力爭奪的糾葛。」而選擇書寫朱一貴的關鍵,是她讀了事件中50多人的審訊供詞,被朱一貴所感動,「相較於其他人為了脫罪,把自己涉入的動機說成被迫參與,只有朱一貴能詳述官府惡行與課稅問題。再來是身分的不同,林爽文、戴潮春都是地方首領,但朱一貴只是一個種地的傭工,卻對自己參與抗爭的理由相當清楚且坦誠,很不容易。」

羅漢門位於如今高雄內門,前身為平埔族居地。傳說明朝文人沈光文曾因作詩諷刺鄭經而惹禍上身,於是喬裝成和尚避逃至羅漢門,「羅漢」一稱便因此而來。清初時,官府設置渡臺禁令,除限制渡臺者身分外,更不准攜帶家眷,使得臺灣將近一世紀之間缺乏女性移民。這些渡海來臺的男性移民,無宅無妻,成為鄉間打工仔,又因窮困模樣如羅漢,而有「羅漢腳」之稱。
錢真以羅漢門為主場景,圍繞著朱一貴與其周遭的人和時代展開故事,不同於文獻記載中對羅漢腳的微妙輕蔑,她小說裡的羅漢腳們,生活雖困苦,仍遵循傭工紀律,不僅守護四季循環與地庄運作,人際往來間更有情義相挺。從歷史小說出發,《羅漢門》重新搬演這場屬於羅漢腳的革命,他們一路從羅漢門挺進到岡山、府治(臺南),最後朱一貴在府治穿上花綠戲服登基,有歌謠傳唱「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但對錢真來說,「華麗戲服不是方誌裡的劣俗,也非清廷眼中的幼稚兒戲,而是熱帶地區的熱情展現,是奔放的生命張力。更何況穿戲服對朱一貴這樣的平民來說,其實是相當慎重的盛裝。」
《羅漢門》是錢真的第一本小說,一出手便展現重寫歷史與地方敘事的企圖,並獲得第四屆臺灣歷史小說獎。有感於許多臺灣人對自身歷史的陌生,她認為,臺灣需要先建立歷史背景的基礎,才能從人物中再去延伸故事。「荷鄭時代已經是創作熱點,不過治臺時間相對較長的清代卻較少受人關注。再加上朱一貴事件時期,臺南還沒成為府城。我們比較熟悉成為府城的臺南,難道就不好奇『府城之前』的臺南嗎?更何況朱一貴事件之後,清朝才更加重視臺灣治理,行政調整也變得更細緻,彰化縣、淡水廳都是在那之後才有。」
空間展現也是小說相當重要的一環,一翻開《羅漢門》,就有一張朱一貴事件的行進地圖折頁,幫助讀者更理解歷史現場。錢真站在地圖前,像將軍一般,引領我們的目光行走於朱一貴的天下,「這張地圖是仿《鳳山縣志》的官圖重繪,視角是從中國出發在海上看向臺灣。通常這時期的地圖是為了方便官方統治與管理,所以軍事設施會標記得比較清楚,凡有基層軍事駐地『汛塘』就有旗幟,汛跟塘又有規模之分,規模稍大的汛蓋塔樓、規模較小的塘插旗。鬧街處畫有房屋,虛線則是官道。雖為官道,但不常修繕,因為路太完整,叛軍也容易攻進來。」

《羅漢門》書中的夾頁地圖,由書籍設計師根據《鳳山縣志》的官圖重新繪製。
朱一貴等一介傭工要武裝抗爭,大字不識更不懂統治,就是官府內的地圖讓他們見識到江湖。而對這群傭工來說,從渡海到臺灣的那一刻,江湖就是他們選擇的命運;因此羅漢門成了小說最大的象徵,「門」是地點、是抉擇,也是人生的檻。當朱一貴等人決定抗爭後,他們結拜、豎旗,啟動這場未知的抗爭賭局。每個人無論在局內局外,都有自己的羅漢門要跨、要閃。
小說中如此描述羅漢門一帶的山路景況:「和同樣被叫作『門』的海上門戶鹿耳門不同,羅漢門彷彿有無數個入口,好像都對,又好像都不對,相似的草木竹林迷惑著人的雙眼。」隱隱帶出羅漢門彷彿也是每個人生命中的檻,往前往後都是人生抉擇。為此錢真創造了多組人物性格對照,為讀者提供進出羅漢門的各種可能,比如朱一貴與陳印,一個仗義而孤獨,一個退縮且溫和,卻都不約而同離開原鄉來到臺灣開啟新人生。她筆下的朱一貴個性坦率,又懂得掩飾內心的敏銳;陳印雖性格軟弱,但只要待在朱一貴身旁,便能擁有前所未有的堅強。
如果說朱一貴與陳印的情感屬於性格互補的信賴,那麼鄭定瑞與李勇的「契兄弟」情誼,則為這場抗爭增添了浪漫風景。錢真說,「契兄弟本來就是閩人特有文化,傭工之間,男人和男人互相解決身體慾望的短暫關係相當普遍,我在寫的時候其實很猶豫,真的可以把這個放進來嗎?但如果刻意不寫,就不能呈現出當時社會的面向,這不合理。」

此外,錢真對女性角色的關注,更是《羅漢門》中篇幅不多卻相當重要的設計。故事的主要三位女性:老庄主夫人、卓春與朱一貴的情人,分別代表了新舊時代與想像世界。錢真解釋,「我希望多一點女性的聲音,比較為難的是,女性在傳統觀念中本來就是處處受限,比方說在小說裡最傳統的就是老庄主黃殿的老婆,她雖然有台詞,但等於不存在,她只能順從,也從來不會出現在黃殿的兄弟們面前。這也是有意無意間造成的,她一方面想淡化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是,黃殿也不希望在一群兄弟面前強調自己有家室,好像跟他們不一樣,那個關係就拉遠了。」
卓春是小說中最具行動力的女性角色,也是文獻中真實存在的「卓氏」,她是少年庄主的妻子,個性就像朱一貴愛恨分明,坦率能幹。「我們可以看到清朝發展到最後,女性又回到閨閣裡去,富家千金都開始裹小腳了。但是在早期開墾的移民社會裡,所有的人都是人力,不分男女都要下田,所以她們不用綁小腳,她們也要練武、要保衛村莊。當女性拿起武器,就代表生命多了一些可能。」至於僅在小說中出場一次的朱一貴情人,則是扮演觸媒的角色。她沉迷看戲,在內心編織著許多故事,從不打破現實中所有被綑綁的關係。所以當朱一貴決定來臺時,她對朱一貴說:「我不能跟你走,你也不會帶給我什麼。我所想要的,全都在戲臺上了。」朱一貴聽完,毅然離開原鄉。
面對歷史學者關注朱一貴事件「如何失敗」,錢真更在意「他們為什麼抗爭」,於是她化身事件偵探,將那些消逝於時間裡的人物,一個個用故事喚回現代,《羅漢門》想點亮的,是一群「失敗者」也曾享有一時成功的史實,「比起討論失敗的論點,我認為這當中有更珍貴的東西。」錢真說。
更珍貴的東西是什麼呢?「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啊。我希望角色是能給人力量,更促進對話可能的。這也是歷史小說的意義,透過認識自己歷史的過程,加深自己跟人、土地的連結。在歷史情境裡,人跟人的互動,可以更溫暖也更惆悵,這也是我偏好歷史或武俠小說的地方,我喜歡的美學,都能在裡面揮灑。」

值得一提的是,《羅漢門》也展現了錢真的廣泛興趣,她曾任高中地球科學老師,小說中的潮汐、天文與星象描繪足見其專業;而她對歷史的興趣則是受到青春期開始接觸的大河劇啟蒙,後來開始廣讀歷史小說,「我很喜歡司馬遼太郎,他的《新撰組血風錄》是我會反覆閱讀的作品,他常描寫的幕末時代非常吸引我,我甚至為此去學了劍道……」這時錢真又笑咪咪的說,她在任教學校還參加國術社,學一些偏北派的拳腿功夫,劍跟三叉戟也學了,「小說中卓春與黃麟的練拳場景就是這方面的知識。」
《羅漢門》講述了一段被官方文獻看輕的歷史故事,然而歷史究竟是什麼呢?歷史是回頭張望的過去,也是時光織就的幻影。歷史有如小說中那位抗爭事件殘存的少年庄主,在多年後重新回到曾經住處看見的那個「站在山路上仍然微笑著的朱一貴」畫面。歷史說到底,是大把大把消逝的存在,只要你願意去看,它就還在眼前。這是《羅漢門》身為歷史小說的貢獻。錢真花了兩年時間,不僅幫朱一貴與羅漢腳們的生命增加更多出入口,她更證明,歷史有來有往,情感當然也能有去有還。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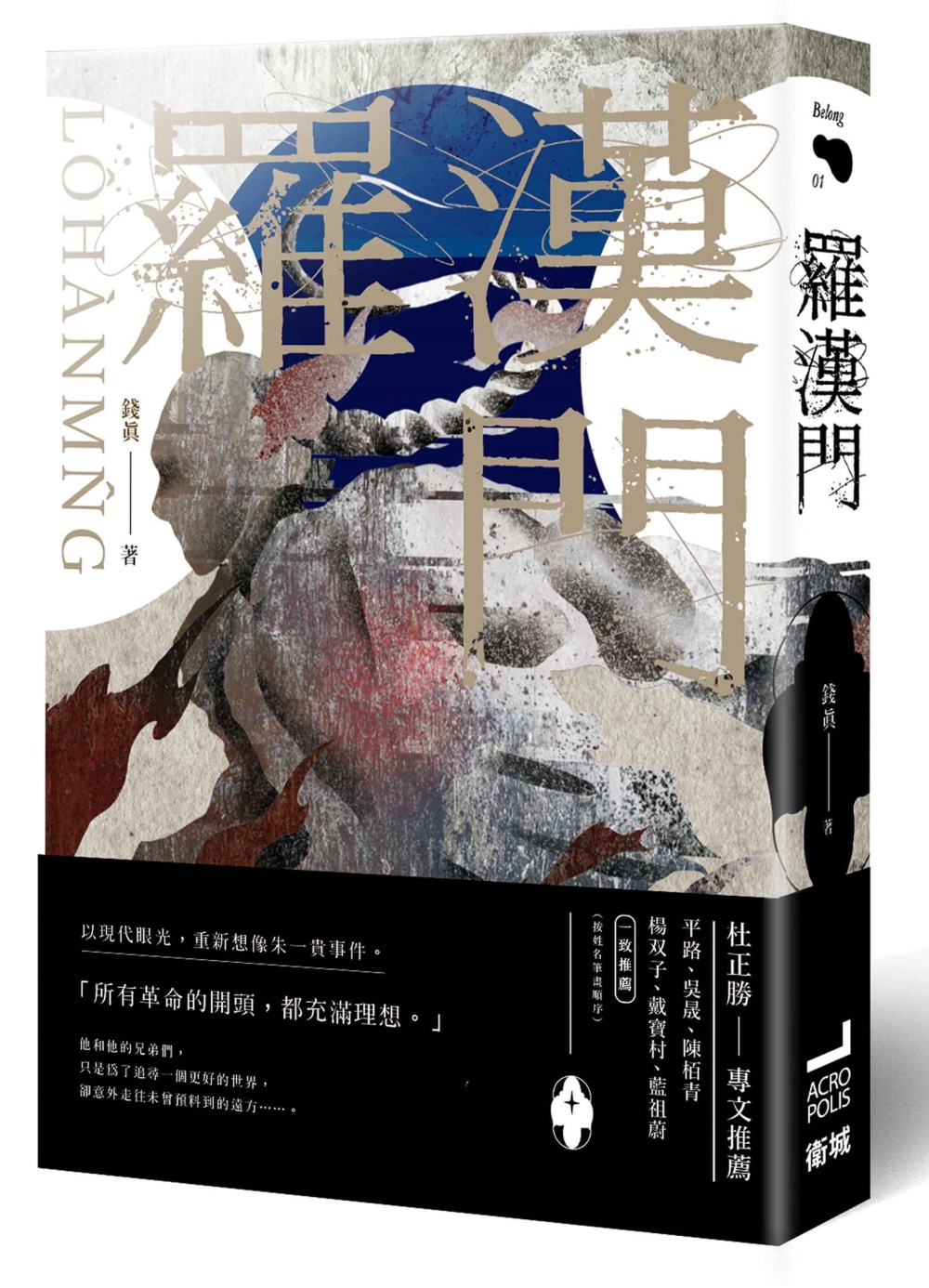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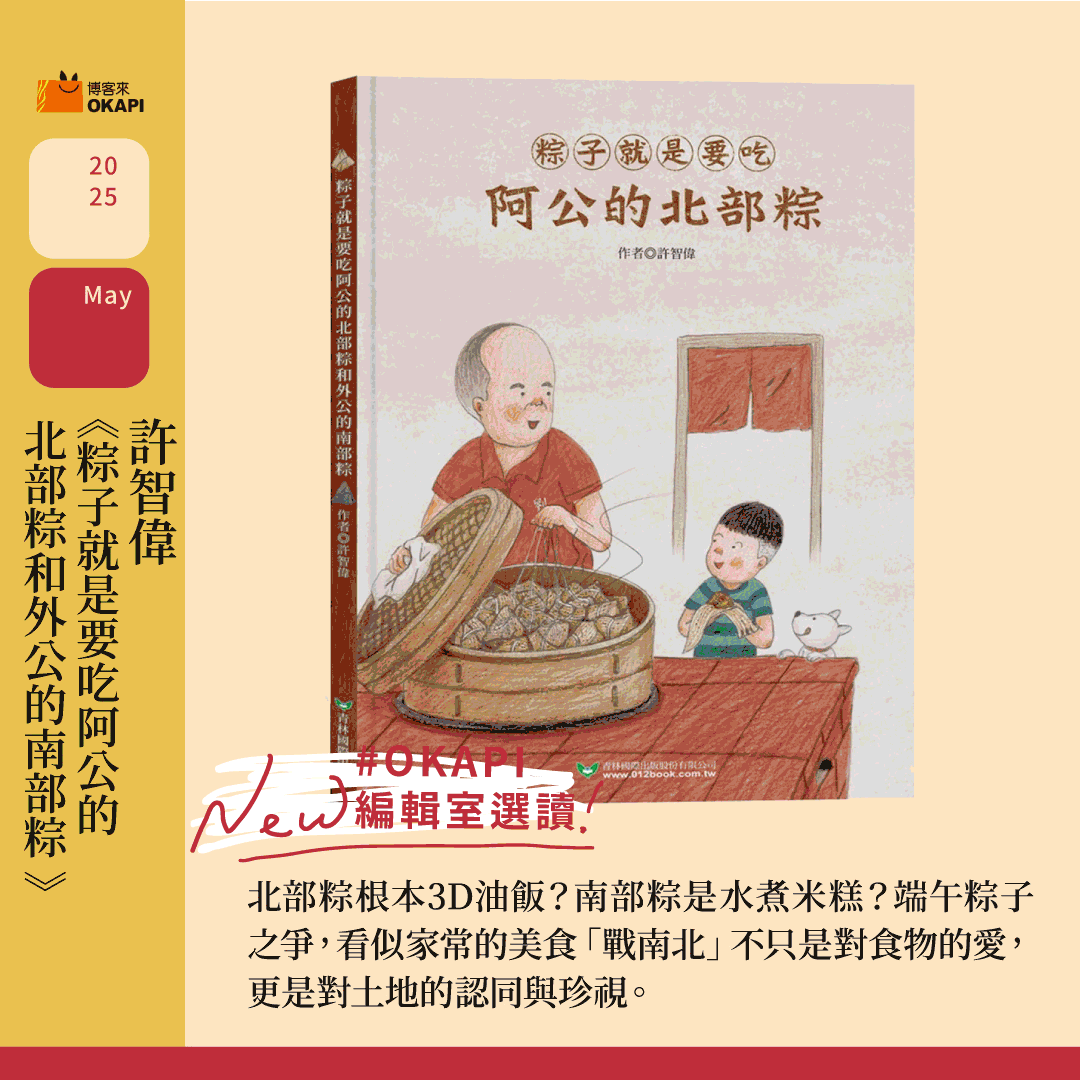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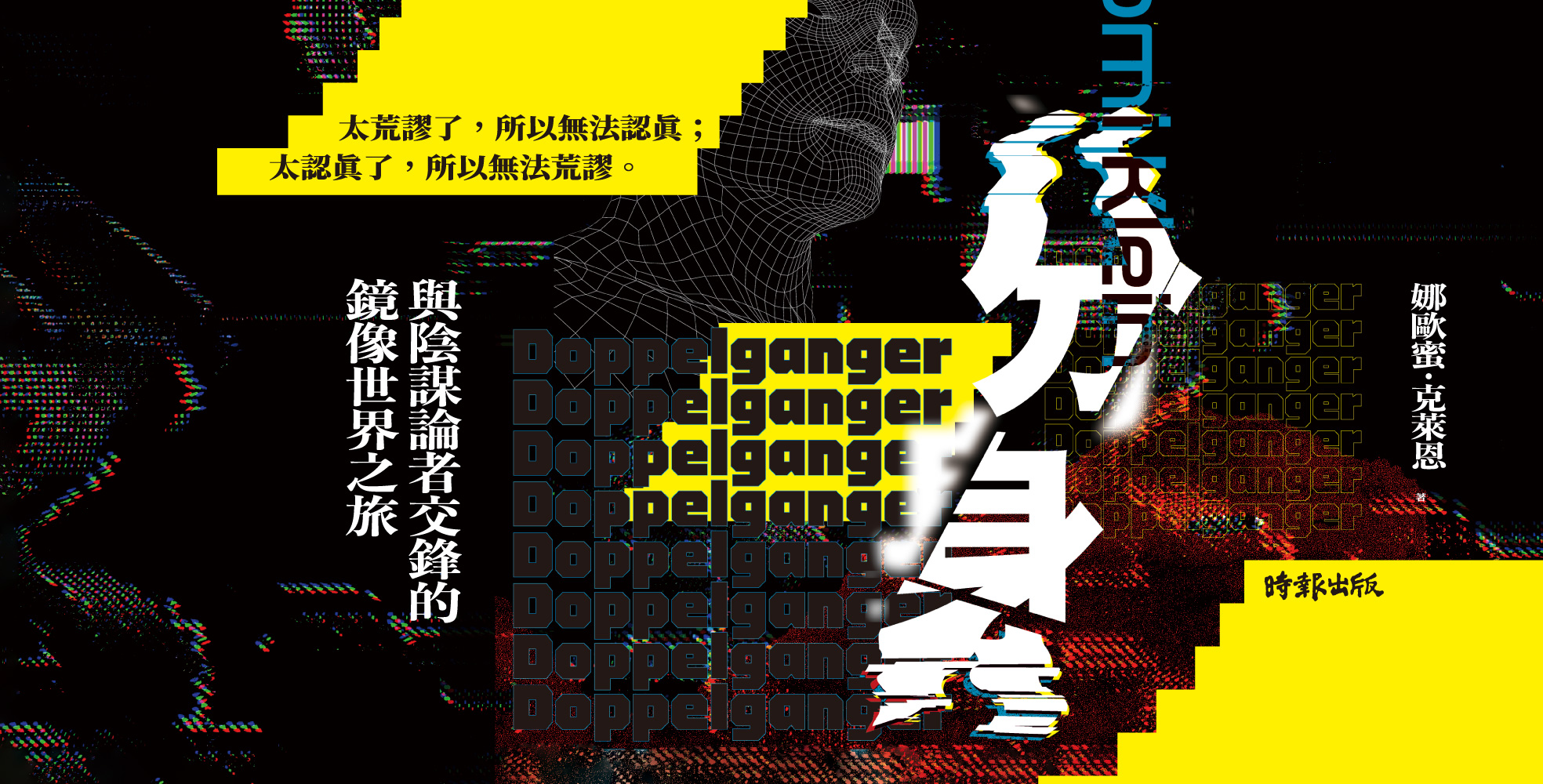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