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白先勇小說《孽子》中,龍子跟主人翁阿青分享他流亡美國紐約的經驗。在聖誕夜,一般人都跟家人團圓吃聖誕晚餐,而龍子「也跟著一群人,在吃聖誕晚餐。」事實上龍子是跟一群男人進行集體而且匿名的性交。
龍子一方面將陌生男體比喻成食物,另一方面將這群陌生人比喻成家人。這群人組合在一起,就是一個家(family);而他們吞食彼此的場所,家(home),就是同性戀三溫暖。
所謂同性戀三溫暖,跟一般男子三溫暖或是溫泉大眾池差不多,但多了許多私密的小空間(死角,暗房,隔間等等),好讓看對眼的男子發生性關係。蔡明亮電影《河流》展示了同性戀三溫暖空間的其中一種樣貌(可能的樣貌非常多種,有心人google國內外部落格即知),還將片中的父親跟兒子磨擦出性的火花。《河流》將傳統定義的家和三溫暖交揉在一起了(而非平行),而《孽子》則將家和三溫暖平行比列為(而非交揉在一起)相反卻又相似的場所:在家裡一起吃飯的家人真的不算陌生人嗎?一起吃下的東西真的不是人類?記得魯迅提醒:人愛吃人。
而同性戀遇到農曆年吃年夜飯的時節(在美國吃聖誕大餐的重要程度,等於在台灣吃除夕年夜飯),比較愛去三溫暖吃人,還是回家吃菜?在《文化研究》第13期,資深同志運動者喀飛在〈老年同志的三重污名:老年、同志、性〉寫到,1996年2月的除夕清晨,台中市夏威夷三溫暖(男同志三溫暖)發生火災,17名客人喪命。我本人則記得,死者之中有台大食品系學生,當時在該系任教的郝龍斌表示會發撫卹金給死者家人。
我一直覺得,傳統家庭跟三溫暖這兩個空間在爭取這批同性戀者。或許也可以說,這兩個相反而相似的空間卻也同樣排斥了他們。
以上舊聞固然不算文學史的一部分,但可算是「公共歷史」的一塊拼圖。在同一篇文章中,喀飛提及近年同志運動者在西門町中老年男同志去的三溫暖進行生命故事訪談(這是公共歷史的一種工作無誤)。大伯們在自己的家中「扮演」好爸爸好老公的角色,而唯有回到這個像家一樣的三溫暖才能「快樂做自己」。在這個例子中,家和三溫暖又是競爭者了。喀飛所說的生命故事訪談已經有部分成果出版:《彩虹熟年巴士:12位老年同志的青春記憶》。
《孽子》描寫的三溫暖情境,以當年的標準而言,可謂驚心動魄。「我們以共有一百多個,有六七十歲全身鬆弛得像隻空皮囊的老人,有十幾歲四肢剛剛圓滑鼓漲的少年,有白人、黑人、黃人、棕色人,在那個聖誕夜裡,我們從各處奔逃到二十二街躲入一幢又一幢又黑又舊的高樓裡,在一間間蒸氣迷漫的密室內,我們赤裸著身子,圍在一塊兒聚餐,大家靜默而又狂熱的吞噬彼此的肉體。我離開那間三層樓像迷宮一般的土耳其蒸氣浴室,出到街上,外面已經瞢瞢亮了。」這一段三溫暖描述,在台灣內外的中文寫作中應該是空前而且絕後的。我說絕後,是因為晚輩大概寫不出這般四海一家(各色人種都有)的歡樂罷。我認為這段呈現的吃人意象,宜讀做性的歡樂,而非人間煉獄:特別快樂的性本來就像吃人一樣血肉模糊。
《孽子》的龍子在紐約很忙,顧肇森小說〈張偉〉的主人翁在紐約也很忙。 張偉發現他的美國男友跟別的男人上床(即:打破一夫一夫的關係),於是他主動跟男友分手,自己卻像是為了報復男友一樣投入「多元性伴侶」的生活(即:雜交,濫交,但讀者你知道我不同意這些用語的貶意)。「他開始去酒吧、跳舞場、或是男人專用的澡堂。」(我有點擔心張偉跟龍子在紐約睡過,艸)雖然張偉身置一夫一夫關係的反面,但「也許在那個酒吧或澡堂的黑暗角落裡,他能再一此的找到一個他可以全心全意去愛的人」。這句話中的「找」,一直到智慧型手機交友軟體(如已經被學院留意的「磨菇」)大行其道的今天,仍是關鍵字。
張偉的性歷險,讓人聯想到林俊穎短篇小說集《夏夜微笑》(2003,原書名《愛人五衰》[2000])。收錄的〈愛奴〉之中,某個角色自白:「二、三年裡,雜交過百人,在海濤洪荒竊笑的木麻黃防風林,在阿摩尼亞吶喊助陣的公廁,在溫柔陷阱的泳池,在盲目分解的三溫暖,以肉慾洗心革面,當然更冀望有愛贖身。」
朱天文短篇小說〈肉身菩薩〉,收在《世紀末的華麗》,一般被視為《荒人手記》的前身。朱偉誠在《台灣同志小說選》的「文本解析」中指出,小說中主人翁男同志小佟,在游泳池畔結識了一個讓他傾心的男子鍾霖。不過,文本中這兩名冤家的應許之地其實是三溫暖,而不是游泳池。
游泳池誠然也是男同性戀意味濃厚的空間,但小佟只在泳池獨游,並未跟人互動(被人釣,或釣人)。「他久已不去三溫暖,愛滋病蔓延之故。」跟年代較早的阿龍和張偉(〈張偉〉首刊於1984年)不同,小佟這年代(應是1980年代末)的三溫暖讓人強烈聯想到愛滋。但小佟還是去了三溫暖,看到煉獄般的景象(跟龍子的經驗差不多),但只看到三五個不要命(不怕愛滋)的浴客(看到的場面比龍子看到的小太多)。他「老死坐在那裡,誰都不裡」;他身置三溫暖,是想被人釣,期待互動,但他卻又不理人。後來他「感覺到有一雙眼睛在看他」,他很彆扭心想「老子沒興趣」,未料一回看,「有一剎那,他們彼此看到。在那空空心巢的浩瀚座標上,他與他遇見。」他們在開在十樓的三溫暖「裸裎相向,高架橋自窗邊飛越而過」。
所以朱天文筆下的三溫暖經驗是倒吃甘蔗,比白先勇和顧肇森所寫的澡堂浪漫甜美。我想眉批一句:在家和三溫暖的拔河中,同志不回家也不錯。
白顧寫紐約,朱寫台灣,都寫出強烈的都會個性:人類成為高樓的附庸,而且互為陌生人。郭強生小說《夜行之子》卻將陌生人逆反為不該見的熟人(像《河流》那樣?)。書中兩個老相好各在國內外發展,久未碰面,卻在台北101跨年倒數的氛圍中(聯想《孽子》的聖誕夜)約在台北吃個新年大餐。這兩個十年沒見的男同志,卻意外提早見面了:在跨年夜凌晨兩點的三溫暖之中。也就是說,老友喝酒之前,先要吃肉。在郭強生的描述中,三溫暖一如慣例,充滿地獄和鬼魂的意象。這兩人是上床了,但飯局取消了,尷尬。
同性戀三溫暖跟台灣同志文學史的緣分還有得聊(我還沒提到傳奇人物「阿Ki」),對台灣公眾歷史的意義也待更持續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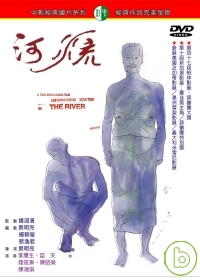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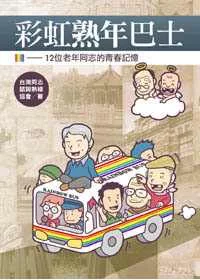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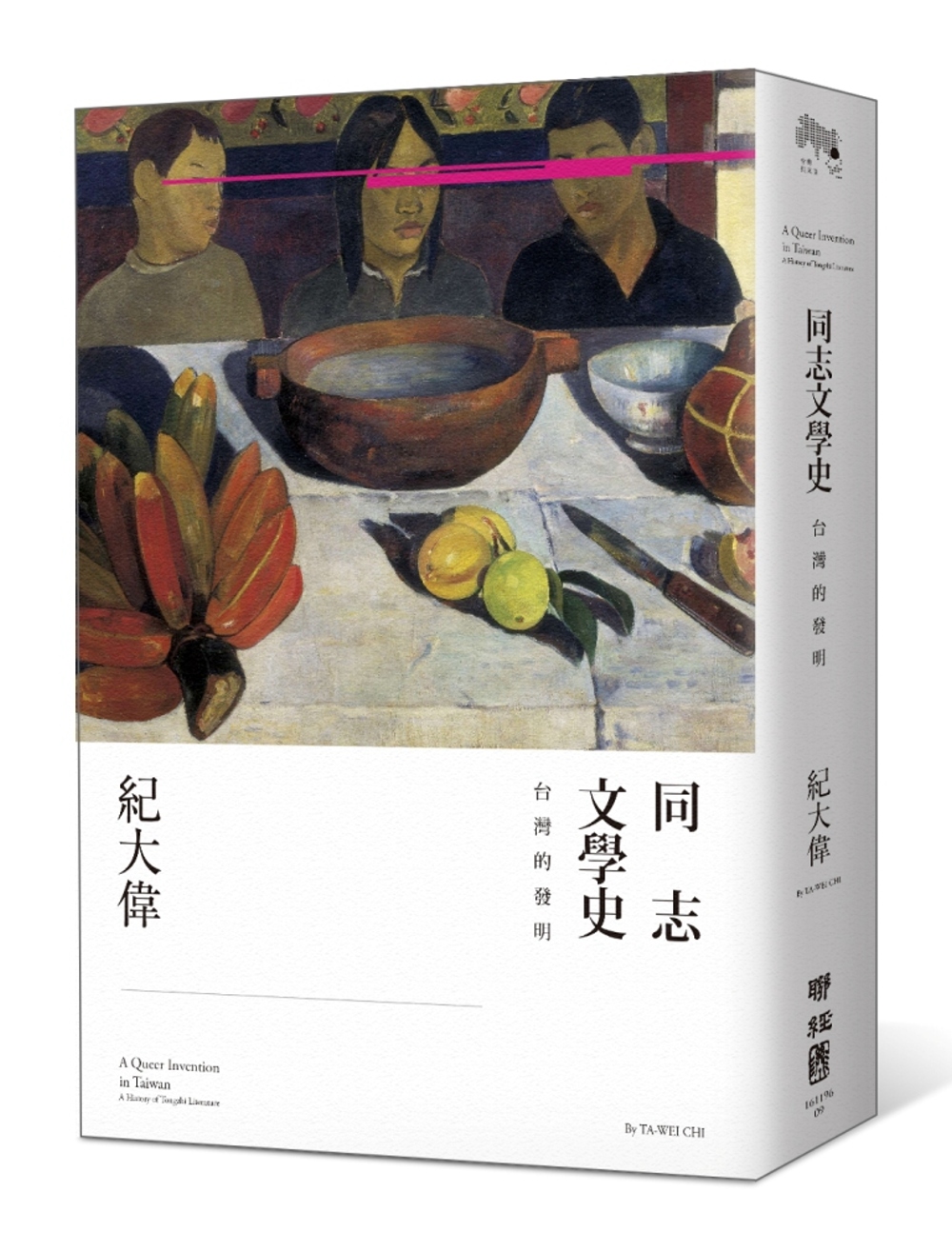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