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放榜的那一週,媽媽趁著排休,開車帶我出遊。我坐在副駕駛座,電台播著輕快的情歌,媽媽說,上大學就可以交男朋友了。講得像是我曾經對交男朋友有興趣一樣。她以為我沒聽清楚,再說了一次。我停頓,回話,說我沒有想交男朋友。又往前開了一小段路,幾分鐘,下一首歌,我們開上一座大橋,就在那個交接的當口,媽媽突然想通,彷彿她不曾懷疑過,用嶄新的口氣,開玩笑卻又遲疑,終於問出那個問題。
我一直很怕,但也許我也一直在等。
那件事情不好說,詞彙太燙,於是媽媽說:妳是不是有「那個」的傾向?
無法說是,或者不是,誠實跟謊言都有難度,幾乎是最困難的口試,而妳已經為此準備了隆重的答案。妳終於能說:「嗯。」或者更接近「m。」難以張口,也難以啟齒的閉口音。車子行駛在關渡大橋中途,但媽媽無暇顧及,逕自開往路邊停靠。她沒接話,我也沒說話,對話就留在橋中央。後來也發生過很多類似經驗,如同親子關係裡的百慕達三角洲,相關的話題總是靜悄悄陷落,開了頭,不收尾,或跳接,或切歌,之後都假裝沒發生過。隱密的攻防戰反覆進行,敵不動,我不動。
接著是上大學之後的事。我的初戀結束得非常慘烈,雙方都年輕,不懂溝通,有許多任性妄為。對方後來劈腿,中間的風雨拉鋸已不復記憶,只記得在椰林大道上淋雨狂奔,或者在醉月湖邊談判,現在想起來覺得真是體力充沛。第一次的分手經驗最苦,吃不下,睡不著,如同行屍走肉。當時流行略寬鬆的褲子,記得有天要去上課點名,套上褲子,手一放開褲子就直接滑落,十天內我大概瘦了七公斤。身邊能夠談論的人極少,幸好有個朋友總是在凌晨陪我講長長的電話,感覺快要溺斃的時刻,每通電話都是空投而來的救命索。跟這個朋友後來失去聯絡,但我會永遠記得她陪我走過的這段夜路。
媽媽察覺異狀,我只能說心情不好,有太多層次需要遮掩,也根本沒有面對其他壓力的耐受度,心裡疼痛而脆弱,輕輕一碰就要斷裂,夾雜著害怕事跡敗露的慌張。沒多久就是農曆新年,大家族的聚會上反覆地被問有沒有男朋友,還有個親戚插嘴說:「妳該不會是同性戀吧?」親戚們有的笑了,有的因為聽到這個字眼而尷尬。完全是地獄中的地獄。
連戀愛都無法公開談了,我又怎麼跳過戀愛階段,直接談論分手呢?
要到十幾年後,我有個異性戀女生朋友發現男友劈腿,她在雨天緊急收拾行李,逃離他們同租的套房,半夜叫了計程車來我家暫住。一進門她就跪倒在門口,呈現 Orz 姿勢,回過神就開始細數她抓包男友的過程,對話內容,心理轉折,哭啊,喊啊,罵啊,崩潰,在臉書貼抱怨文。我突然發現,原來一般人分手是可以這樣的,可以光明正大地攤開來說,甚至哭著打電話回家。
念大學時,看見一些公開出櫃的同志,不一定認識,我遠遠看著那個誰跟誰,尋找一點尾隨的方式。這也是同志遊行的意義所在,仍有人必須躲藏在暗處,藉由一次大型現身,讓很多人知道他們並不孤單,有燈、有人、有路可走。
我在PTT找到Lesbian版,甚至不敢加進「我的最愛」選單,每次都是重新從最外圍的選項繞路而進,怕被誰發現,還有已經倒站的「壞女兒」跟KKCITY的「5466」站台。虛擬的世界,成為妳真實世界的支架。或是精挑細選某個下午,假裝只是經過,深呼吸,推門走進女書店或晶晶書店。《童女之舞》《鱷魚手記》《愛的自由式》構築出一道階梯,飄動的彩虹旗是地下王國的召喚,妳在那裡找到一點近似於認同之物。
我練習在日常生活循序漸進地出櫃,像是在岸邊做一場漫長的暖身運動,接著慢慢踏進淺水池,試圖跟親近的朋友談論,動作必須很小,很怕濺起水花。
初始經驗有好有壞。當我正襟危坐,跟朋友說,我想告訴妳一件事的時候,她就立刻知道了,她覺得很好笑,引用原文就是:「很明顯好嗎!」另一個朋友則石化了,她有點著急地結束對話,幾天後打電話來哭著說:「我沒辦法接受這種事,希望妳能趕快恢復正常。」我跟後者在一個共同的交友圈,我以為她可以接住我的困頓,但我判斷錯誤,剛好我也忙著打工跟家教,忙碌是很好的掩護,我選擇從那個群體撤退。回想起來覺得懷念,那是一個還很在意面對面、或是直接通話的年代。
進一步,退兩步,再進兩步,雖然磕磕碰碰,但我慢慢建立起自己的護城河,發現出櫃其實沒那麼可怕。
跟不太相熟的學姊修了同一堂課,她自然地跟我聊起前女友,不用多說,她辨認出我們是同類,類似這樣的事為我帶來一點安全感。也有意外插曲,系上舉辦三天兩夜的營隊,營區在山上,很冷,工作人員睡大通舖,睡前還要對隔天流程,開會到一半,某個學姊突然指著我,說「蕾絲邊」。我無法招架這突如其來的攻擊,並且覺得這說法古典卻新奇,我無言以對。學姊不放棄,繼續伸手指向我,重述「蕾絲邊」,見我全身僵硬無法回應,她把手伸得更長,將我領口露出的保暖衛生衣的蕾絲滾邊推回去。
我跟媽媽之間也有類似的攻防,很多次我話說到一半,她的眼神或反應,仍舊會把我推回去。我也顧慮到如果真正說出口,她便不能在眾人面前繼續假裝不知道了,但她也將進入自己的櫃子,我家又不是開家具行的,話到嘴邊總是放棄。我是單親家庭獨生女,性向是我們這個小家庭裡的大象,雖已漸漸擠壓到母女的談話跟空間,但我們那時都選擇視若無睹。
大學畢業後,我進廣告公司工作,工時極長,想要通勤時間短些,也想爭取自己的空間,我出外租屋。剛離家時媽媽天天打電話來,問工作狀況,問午餐內容,問一日行程,什麼都問,就是不問我的感情狀況。偶爾媽媽還是會開玩笑地問有沒有男朋友,當然秒回沒有。這樣的往復更像是複診,一次次確認某種疾患的存在,日子久了,我也覺得厭煩,開始長期的不問不說,近乎冷暴力。
工作幾年後,如此的問句又出現了,這次不一樣,我終於有力氣回答:「我喜歡女生。」
那個下午很熱,我站在窗邊講電話,陽光普照,我的聲音在發抖。電話彼端出現很長、很長的沉默,然後媽媽說:「妳這樣不正常。」我回問:「什麼是正常?」已經忘記這場對話是怎麼結束的,最後我一邊哭一邊按掉電話。
我們經歷了關係惡劣的幾年,迸發出巨量的荒謬對話,例如她會突然說可以接受我不結婚,男生跟女生都不要交往,單身就好。再糟糕一點的狀況,我們會突然針鋒相對。我已經不是那個在母親面前失語的青少年,長出認同的同時,我也長出舌頭,學會反擊,學會辯論。不知道從哪一天起,立場竟然轉換,她漸漸說不過我,成為失語的那方。儘管如此,「同性戀」或「同志」仍舊是不被使用的詞彙。我們因為各種雞毛蒜皮小事爭吵,只因為我們不討論最應該討論的事, 我們爭論,卻無法說出核心。我們動不動就吵架,聯絡的頻率拉得很長,見面的時間變得很短。
艱難的冷戰持續數年,很多時候我感覺自己是孤兒,龐大的孤獨感讓我喘不過氣。
三十歲左右,我差不多建立好自己的支持系統,擁有如同家人般——不,可能比有血緣的家人還親密的——朋友們。媽媽見過我的許多朋友,也知道其中幾個女生都是交女朋友的,比例之高,想必對她來說是不小衝擊。而我們漸漸能夠開啟對話,她不會再提「正常」這類字眼,偶爾她還會跟我提起朋友的小孩,說對方看起來就是。接著她幾乎就長出雷達了,我發現她會偷看路上的踢。
從我十八歲的那個「嗯」算起,大抵經過十年,中間有各種大大小小無聲有聲的戰爭,我終於不用再跟媽媽出櫃了。去年公投前,媽媽特地手寫兩好三壞的小抄,進場前還想跟我對答案。至今她還是沒辦法很自然地說出「同性戀」或「同志」這些詞彙,但已不再是禁忌。
每個同志、每個非異性戀者,當他們發現自己跟世界的預設值不相同時,都勢必會走上一段追尋的路,每個人的旅程不同,或長或短,或輕鬆或困頓,有的一路獨行,有的順利跟了團。而如同這段認同的路途,家人朋友也會有他們的路途。出櫃不是看一場電影,無法用兩小時就得到完美的結局;出櫃更像是一千集的鄉土劇,必須吃過很多很多頓飯,過上很多很多平凡的日子,才會有一點點的情節推進。每個家庭的狀態都不同,如果你不幸地降生在高難度的級別,也請不要硬碰硬,就低頭趕快走過這一段,選擇遠一點的大學,經濟獨立,過自己的生活。要好好長大,會有人愛你。
後來,我終於理解媽媽口中的「正常」是什麼。正常是大多數人的選擇,是中間值,如同有人喜歡正常,有人喜歡半糖去冰,有人喜歡無糖少冰。正常不是正確,當你跟大多數人不同,不代表你不正常,你只是比較特別。
 我的Before & After。
我的Before & After。
作者簡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碩士。
2016年2月出版首部小說《向光植物》。
2017年3月出版劇本《無眠》。
2018年以《同志百工圖》入圍台北文學年金。
最新作品為散文集《台北家族,違章女生》。⠀
OKAPI專欄【台北家族,違章女生】。⠀⠀⠀⠀⠀⠀⠀⠀⠀⠀⠀⠀⠀⠀⠀⠀⠀⠀⠀⠀⠀⠀⠀⠀⠀⠀⠀⠀⠀⠀⠀⠀⠀⠀⠀⠀⠀⠀⠀⠀⠀⠀⠀⠀⠀⠀⠀⠀⠀⠀⠀⠀⠀⠀⠀⠀⠀⠀⠀⠀⠀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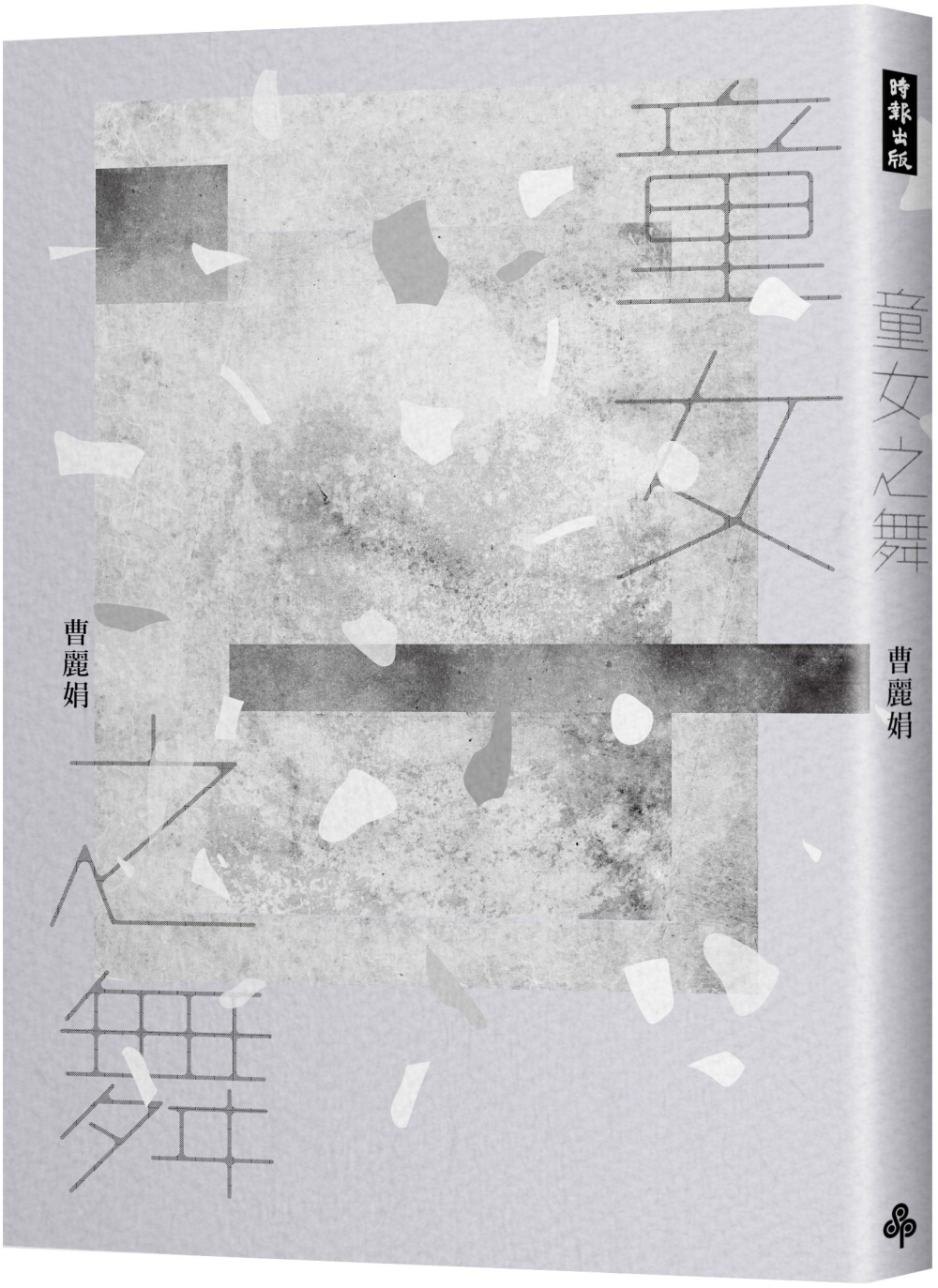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