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內是近年華文文壇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
小說家路內(1973-)的筆名毫無意義,他說,「就只是圖個發音而已。」他本名商俊偉,33歲那年交出長篇小說《少年巴比倫》,簡體版初版扉頁留有成為小說家之前走過的足跡:曾做過工人、營業員、推銷員、倉庫管理員、電台播音員、廣告公司創意總監……小說裡90年代的青春發生在糖精廠,空氣聞起來有股甜味,讀著讀著卻讓人心裡滿滿酸楚與憂愁,路內說起那時當工人的夢想是,「當個科員去坐辦公室啊。茶喝一喝,站起來就下班了。」同樣的夢想,在電影裡讓飾演主人翁「路小路」的董子健說出來,2015年電影入圍第52屆金馬獎。路內寫作至今正好十年,下班後依然下筆不斷,後來專職寫作,已累積六部長篇,並多次被中國媒體評選為年度作家、年度風雲人物。
《少年巴比倫》長18萬字,曾登上指標性文學雜誌《收獲》。刊物都還沒發行呢,他已經把續作《追隨她的旅程》寫完了,堂堂22萬字,又獲《收穫》刊登。一連兩部作品發表在一級文學刊物,是近年來純文學界僅見,質量俱佳,氣勢驚人。日前他為《雲中人》繁體版來到台灣,做為他的第三部小說,小說主角已換了人,這本書是接觸路內作品的一個好機會,也是進入路內創作歷程的一個切入點。「現在回憶起來,因為寫了前兩本小說後,中國文學界有人就說『這傢伙是自發性的寫作』。我問什麼是『自發性的寫作』?人家告訴我:『就是你啊,什麼都不懂。就這樣脫光了上街,扎眼球的。你知道嗎?』」路內說,為了證明自己是有技術的,他決定寫《雲中人》。
《雲中人》是一次技術轉向,著力於結構和形式,小說主角不是前兩部作品裡的工廠工人路小路了,而是就讀三流大學的夏小凡,小城裡有拿著鐵鎚的敲頭殺人狂雲裡來霧裡去,調子更陰暗,小說涵納的議題更多,不是要解開殺人的謎,倒先碰到生存的底,「我想寫一個有技術活兒的小說。通常懸疑小說有其推進力,而我試著不讓事件做為推進力,而是回到人物心理去找。《雲中人》不是直線推進的故事,牌不是一張一張打出來,我一次把一副牌全部攤開在桌上,把它們撥亂了,跳著說。事件之間彼此互有關連,或無關連,要全部看完,才能知道用意。」

《雲中人》以一句「整個路上我都在講這個故事,現在它結束了」收尾,回看《少年巴比倫》開頭第一句是「張小伊和我一起坐在路邊,她說:『路小路啊,你說說從前的故事吧』」,那構成路內早期書寫的標誌──總是敘述者「我」在說一個故事。他解釋,「用第一人稱『我』好寫,講自己故事也容易。第三人稱相對讓距離變遠了。 但第一人稱也存在一個問題,就是長篇的話,第一人稱敘事就是一個說話的,自我敘述的節奏,不會變,很容易讓讀者厭煩。第三人稱敘事操作起來就比較容易變節奏,可以做出更多變化。」
分析得很技術取向,前三本都是「我」,路內話鋒一轉,「哎呀。這樣說來,我早期還真有那麼點自發性寫作。」齁,承認了吧。但這就是路內的魅力,自信與自嘲一體,欲成其事必有波瀾,愈不想怎樣愈要怎樣,一種自我戲劇化。
《雲中人》後,2013年又有長篇《花街往事》,後來也賣出電影版權。資方請他用一句話把小說講完,他想,怎麼可能把這麼複雜的小說精簡成一句話?於是自我解嘲又出現了,「一定是我不好看。長得好看的話,我講十句他也是聽的。」但後來路內還真想出一句話把故事講完,此刻問他《花街往事》寫什麼?「是講一群卑微的人,在任何時代(無論是最好的或最壞的時代),都想維持自己身上一點體面的故事。」小說由60寫到90年代,文革、武鬥、巷戰,往事不只如煙,還如火如荼,從個人擴及到家族,寫青春其實是寫時代,而且這回《花街往事》不只有敘述者「我」了,「小說誕生三個不同視角,有回憶視角、童年視角和少年視角。三個視角之間,敘述的語言和思維差別很大,為了不讓讀者覺得作者連視角和都無法掌握,我想到一個解決方案是,我在講述他人時用次要人物做第一人稱,講述自己時偶爾出現第三人稱。」
不只是有「我」,小說胃納更大,雄心更多。2016年《慈悲》出版,路內依然一句話講完小說:「乍看是講中國人的信念,但其實是講信仰的問題──小說裡人們又信佛教,又拿薩滿教的東西,一會兒堅持自己是無神論者,但又回歸祭祖的傳統──這一盤散沙般的信仰,你也可以說他沒有信仰,那是不成系統的人生觀,但正是這些支撐他們走過這些時代。」小說的素材是偶然得來的,出自他父親和岳父,且小說裡時光有50年之長,「問題在於,很多部分不是我經歷的。也沒有那麼多細節可以把小說撐起來,」這時候,解決方式出現了,他回歸技術層面,那便是使用完全的第三人稱,「讓小說回到簡潔的方式運作。」
從「我」走向「他」,由第一人稱走向第三人稱。這樣說來,路內的小說書寫歷程還真的就是他第二本書的名字「追隨她的旅程」。而追隨路內的描述走,不只把他在台灣已出版的小說複習一次,也理解了路內小說技術的開展史。
我說那方便的話,請把《雲中人》也用一句話講完?他笑了一下,只說,「欸!我愈長愈難看了是吧。」
把講話變成段子,和路內談話豈止是精緻的聊天,根本是看現場即興發揮的相聲、二人轉。他人多妙語,小說中多金句,語言特好,尤擅寫對話,三言兩語既推動了故事,也活絡人物形貌,問他是如何做到?「真要寫工人、寫窮人,他們其實是沒什麼複雜想法的,硬要從他們的心理活動切入去寫,一定沒寫貴族或心理受了傷的職業婦女之心理層面來得複雜。」那工人、窮人怎麼寫呢?「就是從他們的『語言』。我寫這些人物,特別關注他們講話。我就讓他們大發議論,不但講,還要有來有往。互相幫襯,相互烘托,就把人物的面貌和性格建立起來了。在這些對話裡,有些很虛無,有些是自嘲,有些事關諷刺,有些很歡快,表面一個意思,背後一個意思,中國人就活在那個語境裡,很自然明白他們真正要說什麼。」

路內的小說就是對話的雜技團,是語言的遊樂場,看似歡快,底蘊卻是感傷,是一種抒情。他早年的小說,有一種慣見的句法是即刻的時間對比,以「很久以後」、「多年以後」開頭,但隨即告訴讀者這角色後來如何如何,讓人感覺到一種時間的哀愁,有一種立即的抒情效果,「其實馬奎斯《百年孤寂》開頭如此,莒哈絲《情人》開端也是這樣,引入中國後,『多年以後』這樣的句式特別氾濫。我寫《少年巴比倫》的時候不自知。但我必須承認,這種句法可以讓早年的我寫下去,做為『自發性寫作』……」路內眨眨眼又笑了,「這樣的句法提供一種寫作衝動,當我還不是職業作家,初學藝的我下筆不知道該走去哪,前面黑漆漆的,時不時要唱歌壯自己膽的,這個句法讓作者壯起膽子來,把故事繼續講下去。它有讓我講故事的推動力,彷彿聽故事的人在巷子黑暗深處。這是一種自我暗示。」
還有哪些自我暗示呢?「我再提供一個,我長篇寫那麼快的秘訣就是,寫完一個長篇就繼續寫下一個。因為那是你狀態調整到最好的時候,你不要浪費這個狀態,別想著歇一會兒,也別想說回去改你的小說。你就趁這時開筆,寫到你寫不動。用你最好的狀態,把下一個長篇的開篇寫完。」

都是技術活兒,寫下的東西扎扎實實是自己練過的功,走過的路。但他一路往前,筆下90年代依然那麼悠長,似乎未能忘懷。問他為何這麼愛寫90年代?「好玩啊。特別混亂。」他描述90年代,煙沙蔽天,目無王法,「科技不發達,流動性又特別大,那時人們拚命要流動,去大城市,去國外,但交通不夠運,電話不夠打,火車塞滿人,公用電話前人都排成一長隊了。世界比人的運轉慢。那樣的時代比現在有意思多了。現在的世界跑得比人快,世界拉著人往前走,人想慢一點,世界在背後催著你呢!」
時間在催,訪問時間要到了。下一個行程要開始了,下一個訪問,下一本書,下一個年代,風風火火,路內說,「90年代過去,互聯網時代來臨,接觸一個東西實在太容易了。你要得到它、擁有它,不容易。但接觸它很容易。要知道,人有時候只是想要摸摸它而已。『得到』就變得不重要了。」
我忽然想,那個說因為「自發性寫作」而寫《雲中人》的路內,也許不是想證明什麼,他只是不想要「僅僅是摸摸」而已,於是總有一個不太容易得到的什麼在前面,一路往前走,就變成路小路,而不停下筆寫,就成了路內吧。不是90年代特別長,是他不甘心就這樣結束而已。「現在我只想老得慢一點。」路內說。似乎路上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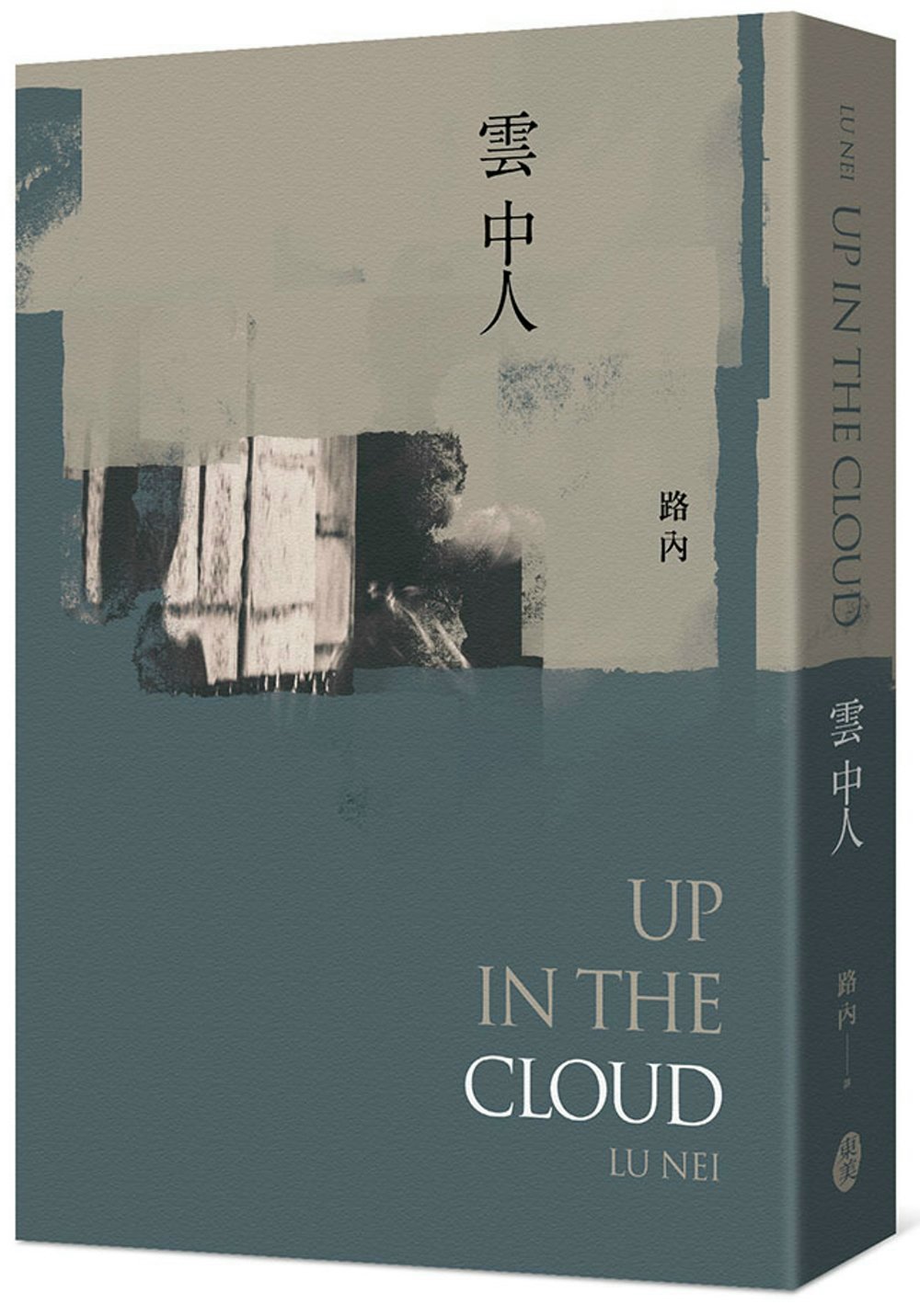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