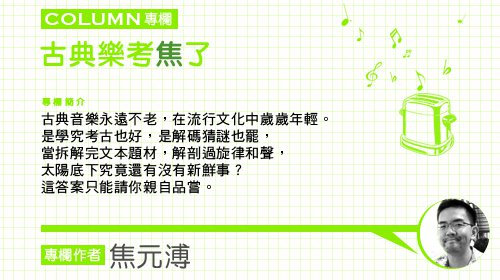
(大家看,我真的很理性,我年假真的有看書,科科。)
不過很少人注意到,《醜的歷史》雖然取材多元,卻有一幅作品出現三次,重複地不亦樂乎。這部作品,就是米勒的「晚禱」——等等?「晚禱」?是那幅曾經來台展出的「晚禱」嗎?這不是世界經典優美名畫,怎麼會出現在《醜的歷史》呢?原來艾可討論的並非米勒原作,而是達利的改作。在達利超現實的眼中,「晚禱」所呈現的意象簡直駭人,根本是死亡象徵。他以變形手法重繪「晚禱」,或將「晚禱」原畫當成配角置入詭譎情境,形成極誇張的衝突與諷刺。
繪畫作品既有醜怪改編,音樂作品自不例外。只是透過旋律與和聲,所變出來的戲法多半詼諧多於可懼。比方說蕭邦:這位音樂家十九歲初到維也納,既見到這大城為圓舞曲瘋狂,卻也鄙視如此輕浮娛樂。從書信中,我們可以清楚讀到蕭邦對此熱門流行的挖苦諷刺,尖酸刻薄的語調讓人難以想像他自己也已寫作數首圓舞曲。在文字之外,蕭邦對這曲類的真實感想,或許正藏在小巧的《降G大調圓舞曲》(Waltz in G flat major,Op.70 No.1)之中。這曲充滿誇張化的維也納風格,第一主題更像是奧地利「尤德林」(Yodeling)曲調。(什麼是「尤德林」呢?大家想想電影《真善美》中的布偶戲,或是台語歌《山頂黑狗兄》中的「U-Lay-E-Lee」,就知道那是什麼了。)
先來聽聽《山頂黑狗兄》裡面的「U-Lay-E-Lee」 (1'23")
再來聽聽蕭邦這首《降G大調圓舞曲》的第一段,是不是就能體會到蕭邦的不懷好意呢?
雖然全曲聽來仍然不失優雅,卻極可能是蕭邦的諷刺之作——也許蕭邦真的討厭維也納式圓舞曲,也許他是見到藍納和老約翰‧史特勞斯等舞曲作曲家大為成功,嚴肅創作卻不被重視的情景而感到氣憤,但無論如何,若和馬厝卡舞曲相較,我們應能肯定蕭邦對圓舞曲並沒有太大的創作熱情,更何況他甚至從來不跳圓舞曲。
至於音樂史上最著名的諷刺作品,大概非聖桑《動物狂歡節》莫屬。究竟為何寫下這部作品,至今仍然莫衷一是。但比較可能的原因,正是作曲家受人排擠攻擊,出外散心途中靈光突現的嘲弄之筆。聖桑壞念一發,那可真是沒完沒了。法國巴洛克宗師拉摩(Jean-Philippe Rameau,1683-1764)首先蒙難:他在《G大調組曲》中寫了一首〈母雞〉,原本只是旋律上的趣味,聖桑卻硬是把該曲開頭旋律拿來惡搞,寫成公雞母雞吵架,母雞下蛋的逗趣音樂。
先來聽鋼琴大師Grigory Sokolov演奏〈母雞〉
再來聽聽聖桑的惡搞版本
更慘的是奧芬巴哈和白遼士,前者著名的「康康舞」被聖桑改給大提琴和鋼琴,用極慢速度演奏,標題則是〈烏龜〉;後者在《浮士德的天譴》中的〈仙女之舞〉則改給低音提琴與鋼琴以笨拙節奏處理,名稱題為〈大象〉……《動物狂歡節》幾乎是所有兒童接觸古典音樂的必備教材,只是當孩子長大後終會發現,那動物世界根本是一張張人的面孔,只是被點名的作曲家同行,大概不會感到高興。聖桑自己也心知肚明,除了〈天鵝〉,《動物狂歡節》在他生前並未發表,或許正是怕這些作曲家,死了也要找他算帳吧!
慢成這樣,你還聽得出來這是「康康舞」嗎?
聖桑和華格納是忘年之交,但他的音樂風格卻和這位德國歌劇巨擘相當不同。可是對當時法國樂界而言,華格納所帶來的影響堪稱無所不在。他的音樂太強大,先進地預見未來,逼得法國音樂家不是受其影響,就是苦思擺脫之道……再不然,那就乾脆哈哈一笑,以輕鬆態度「解構」華格納。比方說作曲家佛瑞(Gabriel Fauré)和麥森傑(André Messager),這兩人不辭辛苦,千里迢迢跑到拜魯特看《指環》。面對如此龐大偉作,這兩人合寫的鋼琴四手聯彈《拜魯特紀念》,卻把所有主題拿來亂改。光是開頭,熟悉的《女武神飛行》像是被放到了哈哈鏡前,成了「歐巴桑跳舞」。此曲惡搞華格納苦心思索而成的「主導動機」,令人啼笑皆非。
惡搞《指環》的《拜魯特紀念》
至於華格納的另一創見,在歌劇《崔斯坦與依索德》中所揭露的「無窮旋律」,其獨到前奏曲與革命性的「崔斯坦和弦」,卻被德布西放到鋼琴作品《兒童天地》中的〈黑娃娃步態舞〉(Golliwogg's Cakewalk)中段,讓人再次見到作曲家不懷好意的引用。
聽蕭提(George Solti)指揮《崔斯坦與依索德》前奏曲,我們先聽(0’05-0’17”)這個句子/和弦就好
再來我們聽羅傑(Pascal Roge)彈〈黑娃娃步態舞〉,在中段(1’17”-1’21”),你是不是也聽到了崔斯坦和弦?
不過,就像達利後來也成為被改作的對象,「整人者人恆整之」自然也出現在音樂創作中。德布西的《棕髮少女》多麼天真純美,偏偏就是有匈牙利作曲家庫爾塔克(György Kurtág,1926-)來搗亂,把主題旋律變形成為《棕髮瘋女》,讓人聽了笑到流淚。庫爾塔克過分的還不止於此;柴可夫斯基第一號鋼琴協奏曲華麗的序奏,在他的《柴可夫斯基頌》中竟成了一堆亂砸的三拍,讓人不禁想起畢卡索對諸多名畫的改作。
德布西的《棕髮少女》
庫爾塔克的《棕髮瘋女》(3'50")
無論如何,就像畢卡索的改作,音樂作品中充滿各式稀奇古怪的引用與變形。或出於諷刺挖苦,或只是開開玩笑,甚至不過是自我消遣,這些作品讓我們見識到作曲家的超凡才華,獨特有趣的音樂美學,以及隱藏其中的歷史典故。艾可說,醜可以比美更美;不管你是否同意,至少,醜應該比美更有趣──不然你聽聽文英的〈哎唷卡門〉或陳昇的〈阿姨打〉,雖然我是真的想問唱片製作人,當初他們究竟在想什麼。
文英阿姨的卡門……
這是史卡拉歌劇院新制作的《阿依達》(Aida),其凱旋場面以華麗鋪張,還有把芭蕾舞明星Roberto Bolle幾乎給剝光聞名……
這是陳昇的……《阿姨打》,誰也來把他剝光? (有人要看嗎?)
焦元溥
不務正業但也不誤正業的國際關係碩士,現為倫敦國王學院音樂學博士候選人。著有《遊藝黑白》《聽見蕭邦》《樂來樂想》等八本專書。你可在《典藏投資》、《南方周末報》、聯晚「樂聞樂思」和中時「唱遊課」讀到他的文章,以及在台中古典音樂台FM97.7和Taipei Bravo FM91.3都會生活台「焦點音樂」、「遊藝黑白」、「NSO Live雲端音樂廳」三個節目聽到他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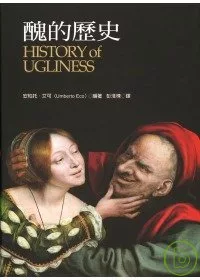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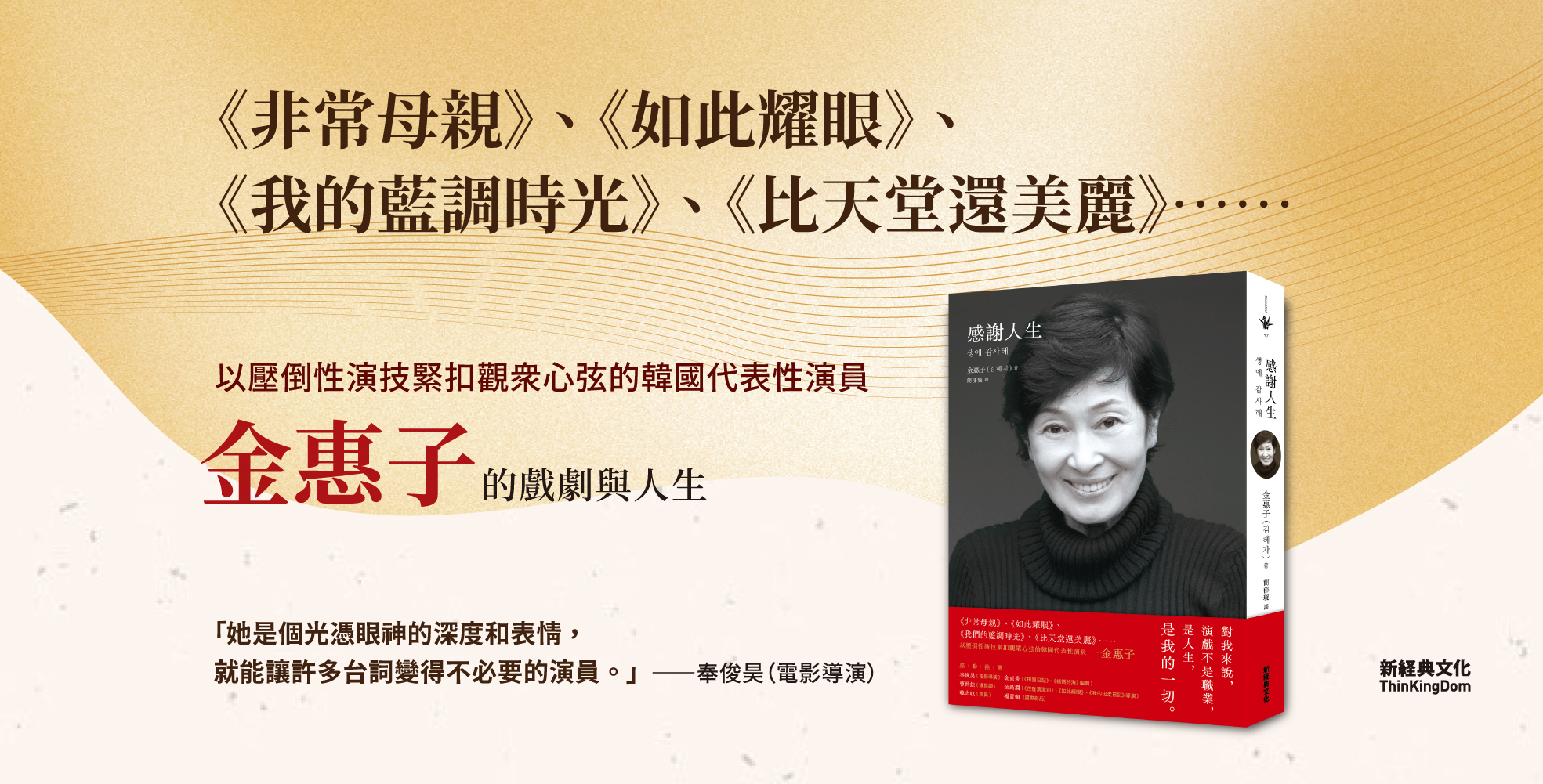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