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80後作家張悅然(圖片來源/ wiki)
中國80後作家張悅然(圖片來源/ wiki)
1999年「新概念作文大賽」在中國正式問世,孵出了一群「80後」新銳作家,幾個有代表性的名字也因此落入大眾眼光。這麼多人之中,首推郭敬明,他的《幻城》是許多台灣年輕讀者對於中國青春派作家最深邃的印象,故事發生在一個架空的幻雪帝國,冰國王子「卡索」與弟弟「櫻空釋」流落人間,為了協助哥哥能夠過上自由無慮的生活,櫻空釋展開了無止盡的冒險和執著。《幻城》的敘事風格打破了許多舊有窠臼,且其意境耽美得不可思議,雖然故事的內裡,長大之後再複習可能會稍感中二且主線稍嫌單薄,但也不得不承認,這種單薄的內裡才方便寄託青少年無止盡的幻想。個人在經歷了《幻城》之後,一位住高雄的網友姊姊見我喜愛,便推薦我看張悅然的〈豎琴,白骨精〉(後收錄於《十愛》裡)。

跟郭敬明有些神似,張悅然的描述總是非常地煽惑的,撩動的,有時候甚至給人濫情之感,例如她是這樣講述白骨精與丈夫的感情:
「她小心翼翼地取下左肩上的那枚鎖骨遞給丈夫。骨頭與骨頭之間有清脆的分離的聲音,她立刻感到有勁猛的風鑽進身體裡⋯⋯丈夫的眼睛灼灼地盯著那枚亮錚錚的骨頭。他動作敏捷地從妻子手裡抓住了那枚骨頭。他當然沒有忘記致謝。他把他迷人的吻印在小白骨精的額頭上。額頭在急遽降溫,但是小白骨精的臉蛋還是芍藥顏色的。丈夫拚命地親吻她的臉,不斷說,啊,親愛的,我該如何感激你呢。我是多麽愛你啊。」
張悅然筆下的故事,常見有飛鳥略過,水晶墜落,除了一種迷離的童話感,更帶有絕望且清澈無染的況味。《葵花走失在1980》裡,主角甘願為所愛獻身,死了也願意長伴左右。《十愛》裡,小白骨精永無止盡地把身上的骨頭交給了樂師丈夫,以所剩無幾的身軀和丈夫做愛,最終再以丈夫打造出的樂器自毀。曾有人分析,中國80後作家為何總專注在這些雕琢又浮碎的感情上,是由於他們多為獨生子女,既孤單,卻又得忍受大人們的眼睛往自己身上望。最後他們只好寄託在個人內在既渺小又浩瀚的世界中。作家莫言則這麼評價張悅然:「張悅然小說的價值在於,記錄了敏感而憂傷的少年們的心理成長軌跡,投射出與這個年齡的心力極為相稱的真實。」
繼上一次的《誓鳥》後,張悅然這次的《繭》,依舊呼應著莫言當初的評價,她仍成功投射出與這個年齡的心力極為相稱的真實。而在我看來,最難能可貴的是,張悅然過去常惹人詬病的是人物底下的「虛無」,這虛無不僅是歷史的虛無,也來自人物與日常生活經驗的斷裂;而這次,她的男女主角們在無比真實的情境下相愛,面對的考驗也極度貼近生活。
在文化大革命時,一枚釘子被打入程恭的爺爺的腦仁裡,後者於是成了久躺不起的植物人,他一倒下,李冀生隨即上位,事業並因此青雲直上,終成一代名醫。李佳棲一出場時,是個帶有純潔氣質的權貴後裔,程恭則因家中的背景惹人訕笑,兩人意外兜在一塊,頻率對上,於是生了曖昧之情,李佳棲甚至去見過程恭的植物人爺爺,那時兩人只覺得有趣,好像在玩扮家家酒,照顧著一個大嬰孩,渾然不覺這個意識全無的植物人,與自己的祖父有什麼關聯。
之後,李佳棲為了追索失落的父愛,追趕上父親的歷史,這才明白50年前,發生在程恭爺爺身上的暴行,極可能與自己的祖父有關。無獨有偶,程恭則意外得知,把程家一脈的福祉給打爛的,正是愛慕對象李佳棲的親祖父。到了此時,兩人終於要正式面對著雙方祖輩恩怨所帶來的謎團與懸案。而隨著他們分頭進行的考掘,這才發現很久以前,故事就已開始編寫了,李佳妻的爸爸李牧原愛上汪寒露,偏偏汪寒露的父親選擇自盡的主因,與李冀生脫離不了關係。世人面對的是李冀生懸壺濟世、勤於救人的正面,而李牧原與李佳棲這對父女則因自己的愛情,反覆與李冀生的陰暗面交手。
從中點出的問題便是:李牧原,李佳棲的父親,為何更接近歷史,卻反而對歷史更無話可說?再者,個人的未來,要跟父執輩們的過去進行怎樣程度上的揪扯?若要切割,那切割的條件在哪裡?作為罪惡現場的旁觀者,要負上責任嗎?若有,那該是怎樣的責任?至於那些選擇以苟活來因應歷史的人,又該如何評價?
在這些角色中,有一個角色特別引人注目,那便是李佳棲的堂姐李沛萱,故事從頭到尾,她的個性都貫徹始終,那就是對於李冀生一心一德的敬重,她同時也反覆提醒李佳棲,要固守這份敬重的正當性。相較於故事中其他人,我認為李沛萱的存在,若置放在台灣轉型正義的討論上,實在是格外貼切。李冀生是否在文化大革命裡害人家破人亡?起初這是個歷史問題,但隨著時間久暫逐漸轉變為信仰問題。而信仰是很難好好討論的。
李沛萱信仰最深,她受到了程恭的報復,於是破了相,臉上從此頂著一條醜疤,她卻從來沒有去舉發程恭加諸於自身的惡待,相反地,她只要求程恭收回對李冀生的評價。為什麼她不去舉發?她是否也怕,若師長問起程恭為何要欺負李沛萱?程恭也許會毫無顧忌地托出:「因為她爺爺害慘了我爺爺」,李沛萱這個角色非常地有血有肉,她願意為了爺爺的清譽吞忍到這種程度,但這樣一個奇女子最後選擇在美國落腳,是否也隱喻了,一個躲避著歷史問題的人,沒有辦法靠得離事發現場太近?而李沛萱的形象,不正好與台灣這些年的一些紛擾,有著隱隱的連結?
種種疑難,都有獨立發展成長篇的質地,且若一開始敘事主調沒站穩,很容易流於一連串的沉悶的控訴,張悅然一口氣經手這麼多,卻沒有左支右絀之感,這也許能歸功於她所做的精彩轉化,透過敘事視角的切換,小倆口呢喃著一邊追憶一邊抒情,面對的家族命題,也是為了給兩人胸臆間埋藏的深情找一個歸處。如此一來,艱硬的命題也有了好入口的質地,更重要的是,讀者思考和對話的空間也因此被打鑿出來了。
雖然仔細觀看,仍可以察覺到介面與介面之間接縫的痕跡。但我們得承認,張悅然此次的轉變是一次非常精彩的嘗試,她以愛情為引,勾出了歷史的縱深。雖然在結尾時,敘事的節奏像是扯散的珍珠項鍊,鬆緊失去了前幾章的秩序,而在釐清了李牧原和汪寒露的情仇之後,回歸到男女主角的情感時又回到她過往小說的輕盈浮華,讓整本小說有頭重尾輕之感,但仍是瑕不掩瑜。讓人在心滿意足的同時,忍不住回頭去複習那個將鎖骨獻給心愛丈夫的白骨精。你將會發現,很難得這麼一位作家,這麼多年過去,仍誠心誠意地想說好一個故事,以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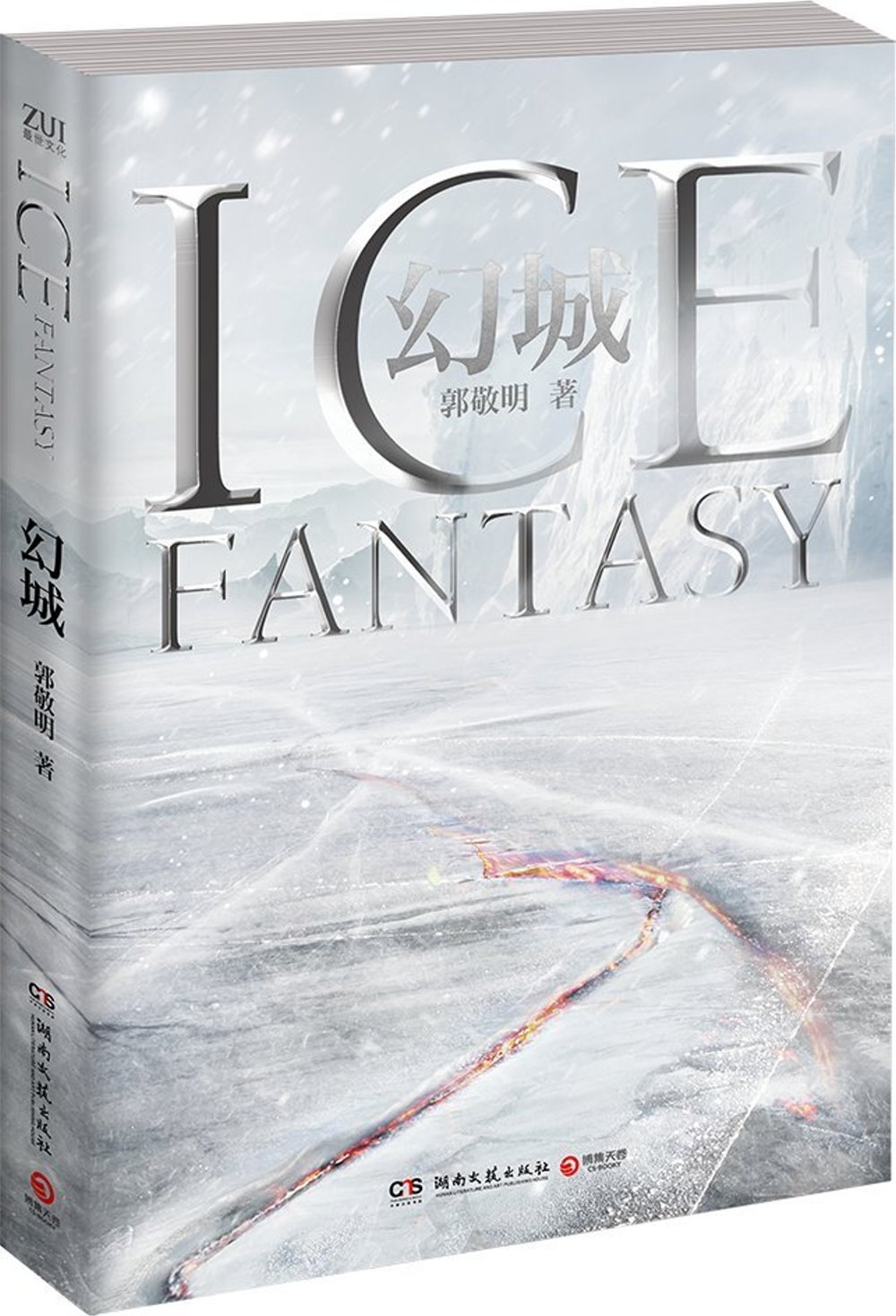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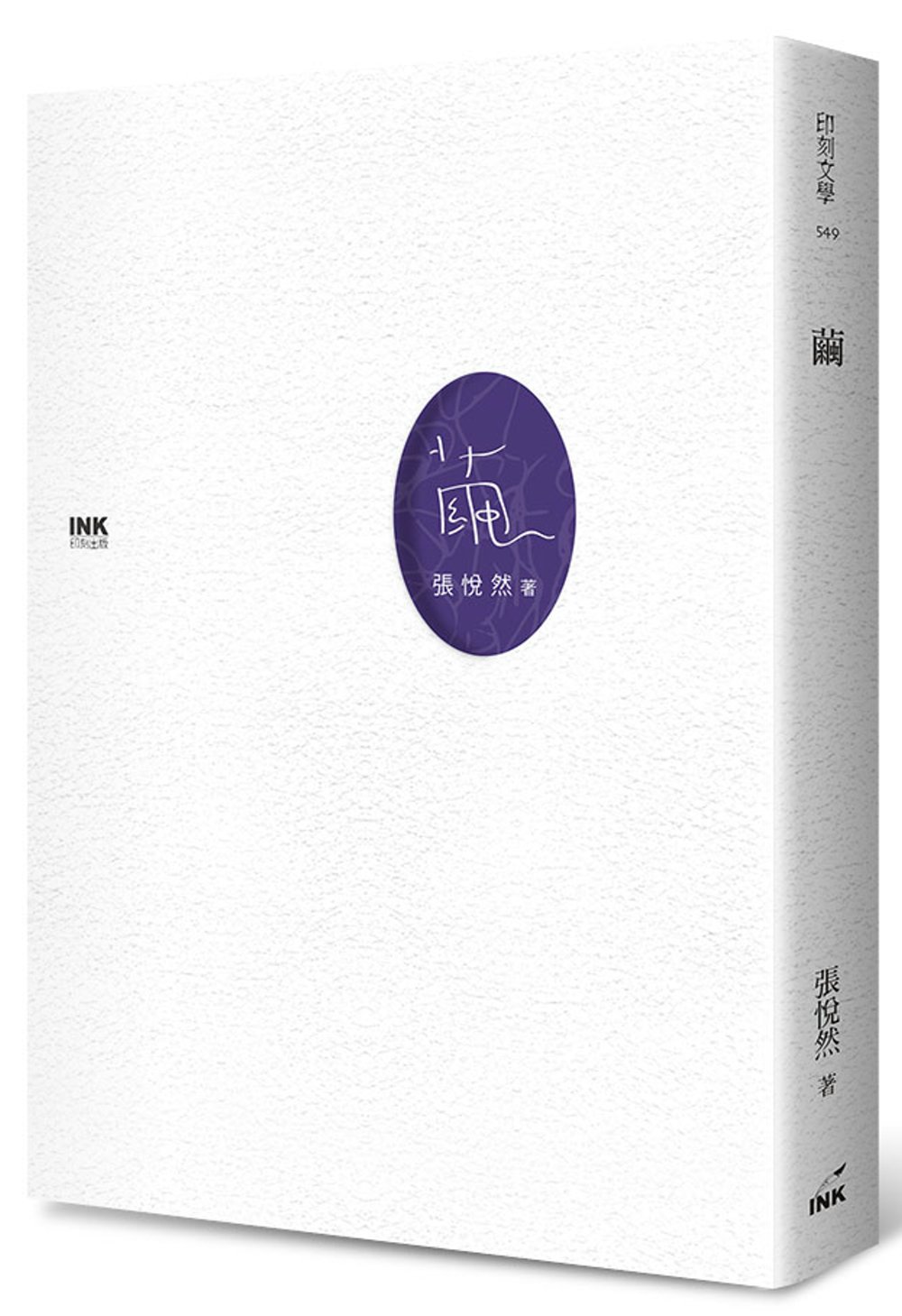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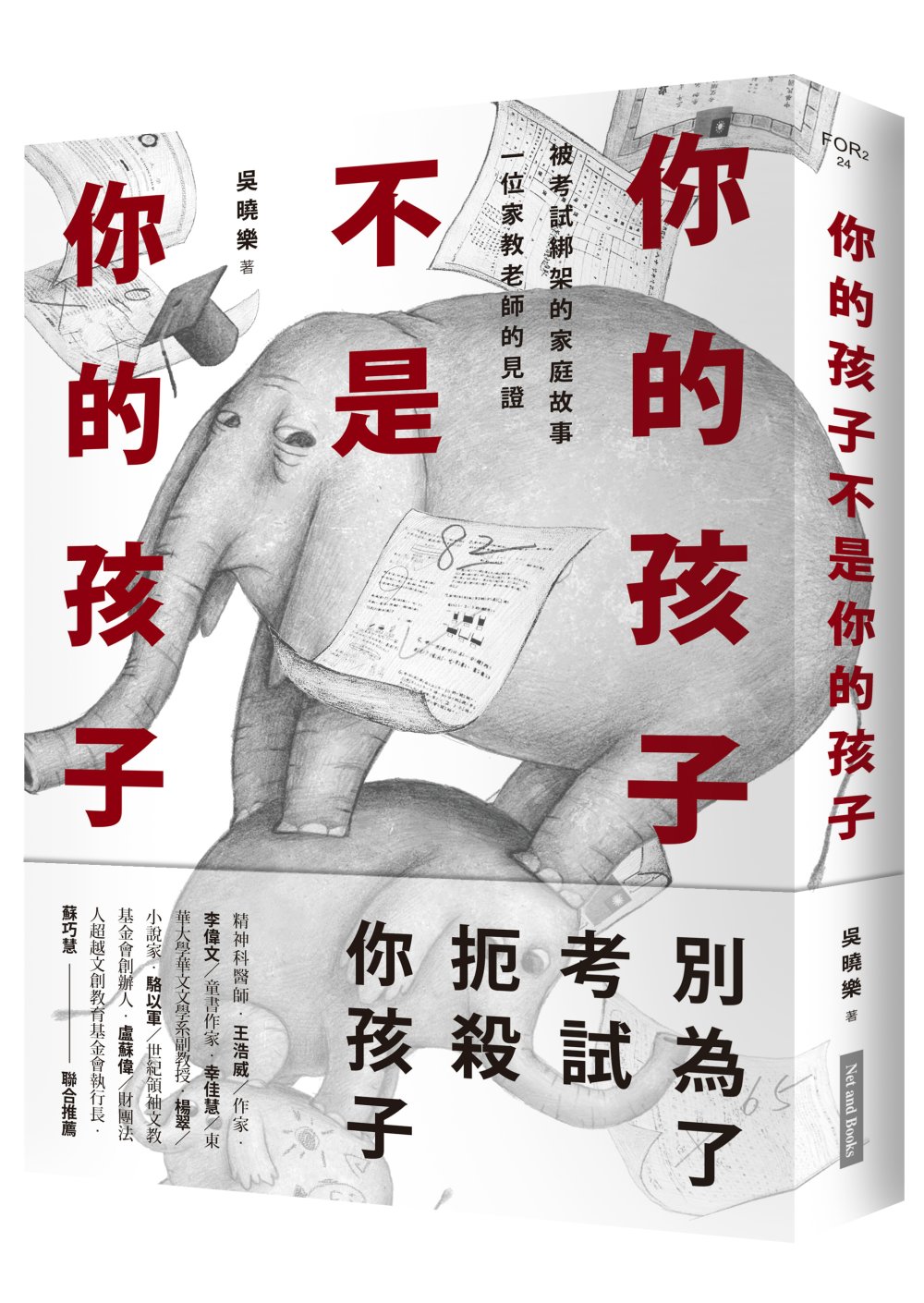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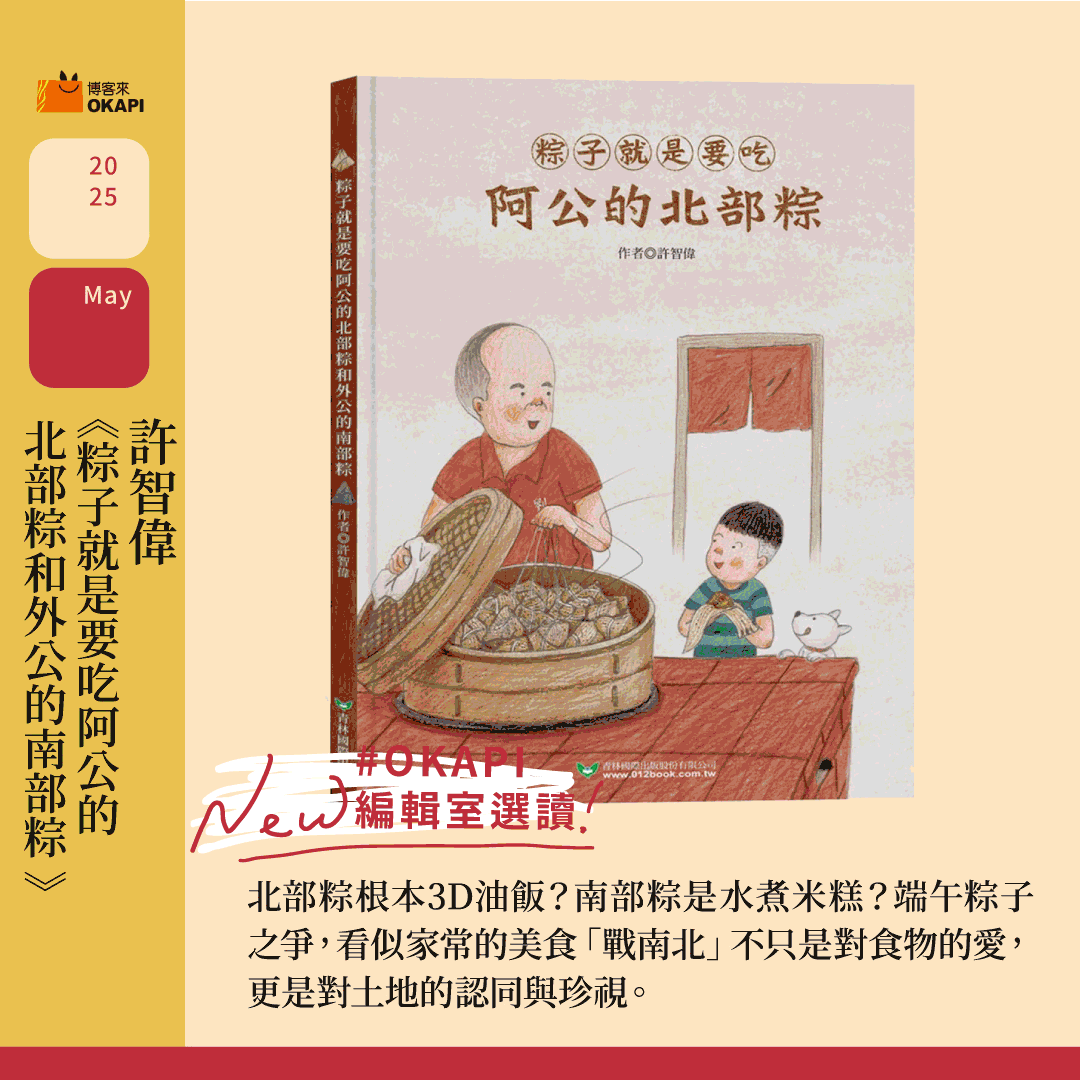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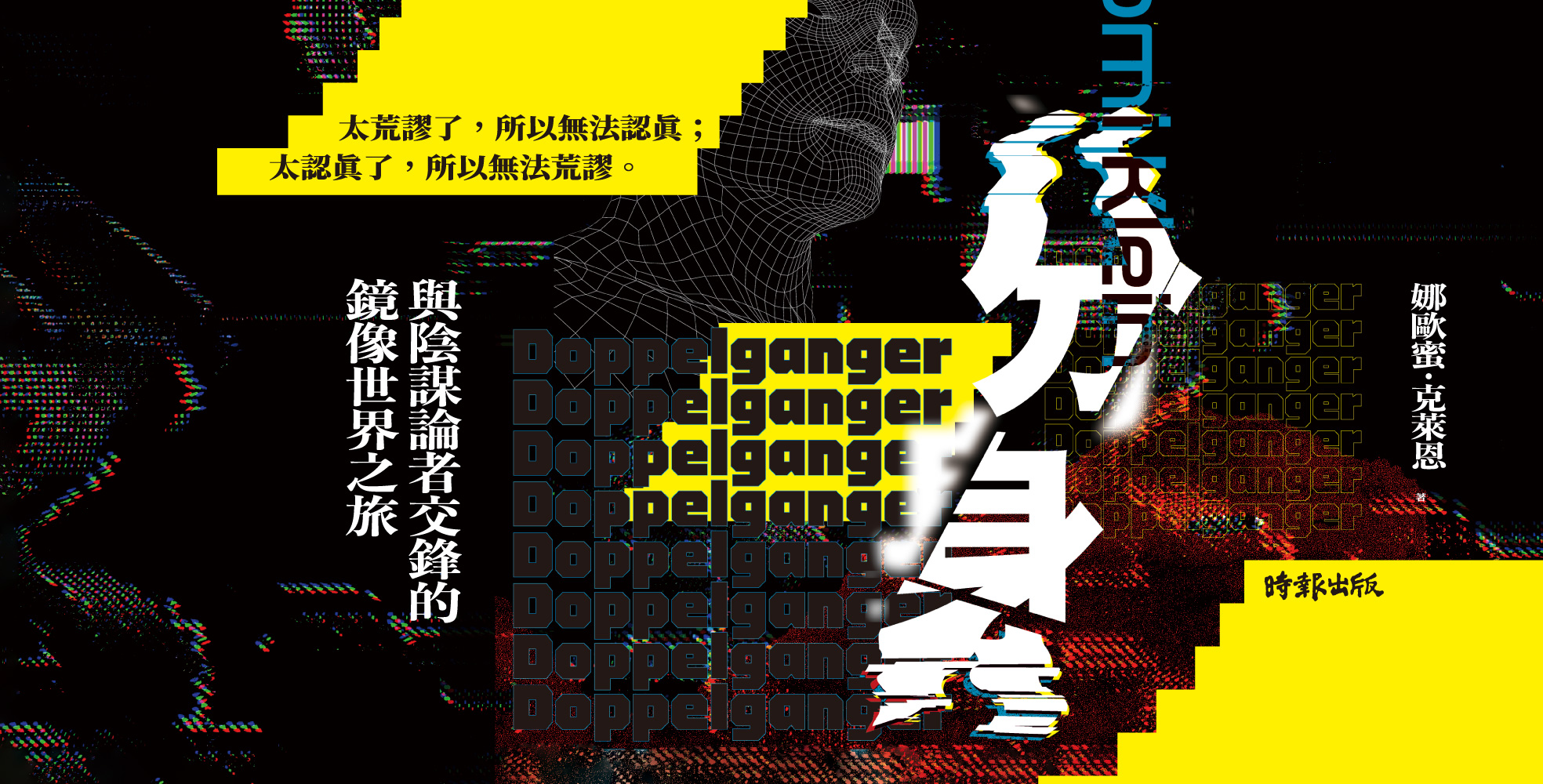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