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厚心得
彷彿是留下了一些痕跡,讓我們得以窺見一個不了解,也無法了解的世界。《平壤水族館》
作者:DL / 2012-09-20 瀏覽次數(4639)
1977年夏天,一群陌生人出現在姜哲煥家,宣稱他祖父犯了「最嚴重的叛國罪」,所有財產必須沒收,同時跟祖父住在同一個屋簷底下的一家人,都得立刻送到耀德集中營集中「管束」。不同於大人的慌亂,姜哲煥一開始沒什麼感覺,他只當是搬去鄉下住,重點是搬家要帶什麼?妹妹美湖拿了她最心愛的洋娃娃,姜哲煥靈機一動,抱了個水族箱,帶上幾條他最心愛的魚。在接下來那一路顛簸、慌亂的「下鄉」路途中,他始終緊緊抱著他的水族箱,小心翼翼護著不讓水灑出來;他本想把祖母拿給自己吃的白煮蛋分點餵魚,卻被祖母一巴掌阻止──這是祖母第一次動手教訓他。幸好他還有心愛的魚。
怎麼會有人如此天真的執著在一缸魚身上?因為那一年他才9歲。姜哲煥一家原本是日本歸國僑民:祖父在京都經營珠寶跟白米,事業有成;祖母是則是北韓共產黨在海外的活躍幹部,父親若無意外應該會當個攝影家,姑姑是藥劑師、叔叔念早稻田……但在1960年代,為了響應北韓政府人才歸國的號召,祖父母帶著全家人回到北韓定居,姜哲煥就是在北韓出生的。
1960年代的北韓生活尚稱富裕,姜哲煥一家無論是經濟、社會地位都高人一等,生活更是優渥,突然被丟到集中營,第一個不適應的是廁所。因為飲食的改變,腹瀉成了家常便飯,整個耀德只有28個茅坑,得供2、3000人使用,非進不可的汙穢公共茅坑與原本家中明亮白潔的廁所馬上成了鮮明對比,惡臭、因為沒有衛生紙而得自備夠大的葉子、雨季滿溢冬天結凍的排泄物……
當然,集中營的生活,廁所不會是重點。《平壤水族館》是姜哲煥在離開北韓之後,所寫的回憶錄。記錄他從9歲到19歲,在耀德集中營10年,以及他如何從北韓到中國、再到南韓的故事。個人經驗跟普遍理論應該是怎樣的關係?黃默教授在他的推薦序中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其實這某個程度也反映了我自己的疑問:我為什麼要再閱讀一本關於北韓集中營的故事?關於北韓、關於集中營、關於21世紀的亞洲、國際情勢,我們可以透過種種媒體、書籍,更「客觀」的了解,為什麼我們還需要那麼貼近的、一個個閱讀他們的生命故事?我們甚至難分真假,不是嗎?
姜哲煥初到南韓時,他的北韓經驗受到質疑,有人質疑其真假、左派分子更質疑其個人經驗如何能代表北韓暴政,這跟共產主義到底有多少程度的關聯性?不只北韓,南非、柬埔寨,甚至我們自以為再熟悉不過的中國,當他們站出來向世界發聲時,都曾遭受這樣的疑問:個人經驗能反應政治或社會的現實嗎?其實,從小生長在所謂「民主世界」的你我,對於極權統治的惡感與批判我想其實無須討論,可是我們依然不懂,我們沒有感覺。
所以我們會有這樣的疑問嗎?我不確定。可是我想我替自己找到了一個出口,在這本書裡,姜哲煥的筆調,帶著怒氣。即使事隔多年,即使他現在已經在南韓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即使他現在為了北韓人權奔走,他可以努力的做些什麼了,可是在他的敘述中,依然看的到怒氣,與不解。一開始我不喜歡這種口氣,我覺得那太過個人發洩,可是當我再回頭閱讀一次黃默教授的序言,我開始真正感覺得到,這本書是一個人的回憶錄,是一個9歲、10歲、11歲……的男孩,在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過程,反映了一部分現實、反映了一群人、一個時代。
姜哲煥帶來的那一缸魚呢?其實剛抵達耀德時,魚就死了一批。不過姜哲煥還是細心呵護僥倖存活下的幾隻,勤於換水,也會趁工作空檔抓昆蟲給牠們吃。不過「魚兒和我一樣,在耀德過得很辛苦。」最後只剩一隻,一隻什麼都吃的黑魚。他盡其所能的呵護牠,姜哲煥把所有他能抓到、能做為魚飼料的昆蟲曬乾、磨成粉,黑鬥士也乖乖的,什麼都吃;只是最後終究敵不過天寒地凍。黑鬥士的死亡彷彿象徵著過去美好生活結束。但書籍設計很巧妙的,留下了一條象徵的黑魚,在各章節間穿梭游走。彷彿是留下了一些痕跡,讓我們得以窺見一個不了解,也無法了解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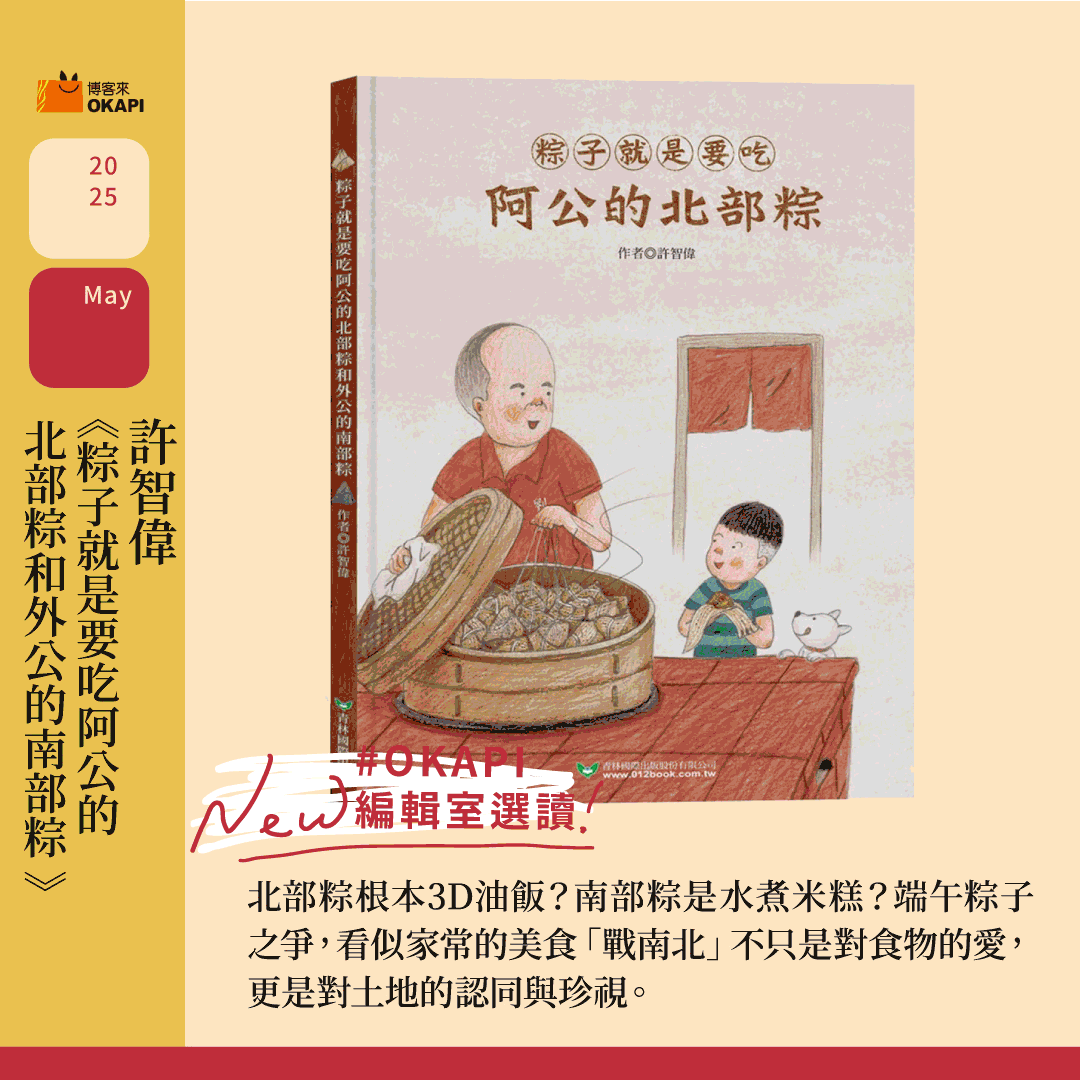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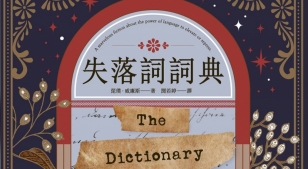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