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但以理)
該要怎麼看待一本小說呢?2006年出版短篇小說集《哀艷是童年》,2008年寫壞了一本小說,作廢不發,胡淑雯說,寫壞的感覺其實很直觀,像是在談一段timing不對的感情,只能丟掉它重新開始,作廢的決定也許任性,她想嚴肅看待自己的作品,所以選擇割捨。直到今年,終於等來了她的首部長篇小說《太陽的血是黑的》。
「小說的本命,該是撼動現實。」胡淑雯說,維持一貫的關懷與深刻,她在新作中為那些沒有發言權的人發聲,可能是無法言說,可能是難以言說,如同她在書中提過的「傷口像一張不曾癒合的嘴巴」,她也為這些傷口說話,將堅實淡漠的人心層層剖開,讓讀者被她的文字刺中,轉而用新的視角看世界,直到觸摸到棉花裡的針。也許偶爾旁觀他人之痛苦,但逐步學習不在別人的噩運裡喧嘩取鬧,然後漸漸,離無動於衷幾步,感覺他人之感覺。
她寫精神病患、政治犯、性侵受害者、變裝皇后,讓這些名詞從新聞的社會版移轉至小說,從此不再只有片面。因為對現實保持敬重,她為刻板印象寫人物故事,「因為對於某些字眼充滿戒心、充滿困惑,我們常使用充滿價值判斷的字眼,但不去表達當事者的處境。」胡淑雯打破標籤,寫出生命本身的質地,也許粗糙、細膩、純真、暴力,也許兼具,寫全然的真實,但她同時避免剝削角色以成就小說,存有對真實的敬重。她的書寫總是節制,在潰堤前夕,不忘留給讀者一座溫柔的水壩。
「傷害之外,更大的課題是療癒,」她說,作為一個寫作者,其實不那麼相信制度與權威,因為一旦訴諸家庭之外更大的權威,例如警察、檢察官、政府,合法的權威是另一種暴力的形式,會繼續造成傷害,所以當她筆下的角色有力量的時候,會讓角色傾向於自己去解決自己的問題、面對疾病、面對漫長的療癒之路。「療癒不是從此不痛,就此忘記,我覺得療癒是知道自己怎麼了,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痛,接受療癒沒有終點,承受疼痛,而不是找到一個更大的權威來出頭。」學習與傷害共處,與現下的自己共生,這是她的小說人物總面臨的課題,她認為人不是機器,不能像進廠維修那樣把人修好,因為經歷過,人就無法再回到原點,「我真的相信人一生只要做到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為什麼變成今天這樣,知道自己哪裡壞掉了,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痛,這樣就很足夠了。」

(攝影/但以理)
出版第一本書的時候,胡淑雯曾自稱「大學不讀書,都在街頭」。對讀者來說,便有種「熱血青年」的形象產生,提到那段時光,她還是十分懷念,但想為這形象做個補充,「精確地說,我是天天泡在社團裡,街頭有事就跟著去,天天晚睡,經常遲到,絕非像樣的學運份子。」對於表裡、詞語、身分定位的精準度,也表現在她對「作家」的看法,直到出版第二本書的現在,她說自己還無法安然接受作家的身分,覺得自己還不夠格,不過她挺安於讀者的身分,真心愛著世上的優秀小說,並且付出許多時間,「對我來說,愛就是時間——願意將自己有限的生命奉獻給對方。」
幸好在寫作《太陽的血是黑的》的末期,她開始想著下一本書,書名可能會叫《恨》,「我想寫『世故』與『遺棄』,一本關於愛的小說。」被過度的詮釋,愛已經是陳腔濫調,「但我們總是需要愛,無時無刻地在經驗並失去著。」朋友勸她別寫《恨》,其實在這個命題底下,她想寫的其實是愛,現在先說出來,當作約定,以免她又反悔延遲。不管她對現下身分的定位為何,交出首部長篇後,我們相信她已得到祝福,絕對可以,開始寫小說了。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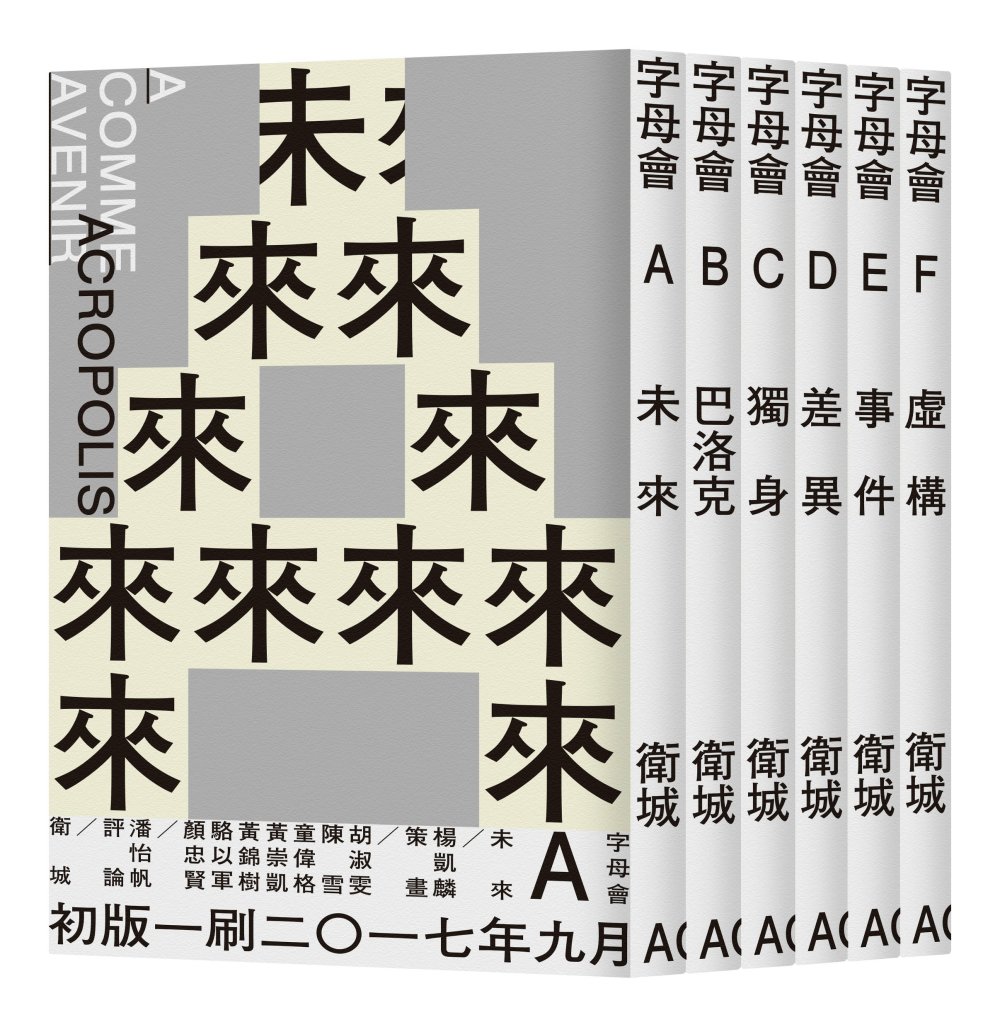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