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上一部長片《那小子咁威》十年後,陳果終於推出新作《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本片熔懸疑、驚悚、科幻等元素於一爐,預告片一釋出,點閱率爆表,今年2月在柏林影展舉行世界首映,4月隨即在港上映,坐收逾2000萬票房,片中納藏的政治隱喻更誘發相當爭議。
《紅VAN》改編自網路作家Mr. Pizza 的同名小說,彼時陳果正醞釀拍長片,監製問他能否翻拍,他一看原著,認定足以將之打造成一部非常商業類型的電影,遂一口答應。唯獨有一前提──不能干涉他如何改編。陳果直言,「做為導演,倘若沒有我的角度,這作品就不是我的了。我們這種導演比較麻煩,不喜歡幫人家做完拍拍屁股就走人,起碼要有一種占有慾,要把人家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東西,所以就成了現在這個版本。」
何謂「我們這種導演」?此話恐怕得拉回到20年前。
1997年以《香港製造》開創香港獨立製片先河的陳果,當年其實是主流電影工業中的一員,導演處女作不賣座,第二部片甚至連在香港上映的機會都沒有,他不由懷憂喪志:「算了,我的導演生涯應該完了。」
「不賣錢有個好處,把我逼出來走這條路,去拍獨立電影。」陳果說,當年啥也不懂,何謂「獨立電影」、「藝術電影」?事實上,早先那兩部電影並非發自他內心所想,純粹是依循電影工業慣例完成,後來他索性不幹導演,回去當策劃、副導。1995年左右,他突生一念,有意拍部關於九七回歸的電影。陳果自認不是那種「磨刀十年,只為一擊」的導演,雖有此念頭,但故事梗概仍未具雛形,思前想後,終於讓他搞出《香港製造》的劇本。「我1995年開始寫這劇本時,有如神助,寫什麼都很好看。那時用一些過期的膠卷去拍,很享受拍攝過程。」今年《香港製造》甫數位修復完成,他又看了一遍,驚訝於彼時的冷靜,用了不浮誇的手法去拍,「現在來看,無論視野、技巧,還是非常OK的。憑這部電影我就開竅了,所謂的『定位』就是這個意思。」
猶記得七一回歸當天,有另外兩部片去拍了滿天璀璨煙花,一是徐克《迎頭痛擊》,另一是張婉婷的《玻璃之城》,但不過以此為背景,觸及的僅是表面,無怪乎陳果喟歎:「這麼大的議題,香港竟沒有一部電影拍!」
然而,《香港製造》完成後,卻未進入香港電影節任一展映單元。「記住啊!最大的諷刺是沒被選上!」香港導演、影評人舒琪為此在報上連續幾天開罵,終於逼得選片人致電給陳果,詢問能否另闢專場,特別放映給外國人士看。很多外國人看完後百思不解:這是唯一一部攸關香港九七的片子,為何不選?後來威尼斯、柏林、盧卡諾影展的邀約紛至沓來,《香港製造》陸續於國際影展曝光,陳果回憶,「在盧卡諾,八千人在一個露天廣場上看你的電影,多大的銀幕!那種感動你是無法形容的!」他頓時明白,「原來拍電影可以這樣!」緊接著,他馬不停蹄完成《去年煙花特別多》《細路祥》,與《香港製造》合稱「九七三部曲」。

憶述這段走上獨立製片的路,陳果戲稱,「就是這樣形成,很奇怪,比打針還快。」他自認算是主流電影工業體制內喜歡看影展的人,一回,香港著名導演元奎問他去看了什麼,他答「侯孝賢」,對方驚呼「哇!這麼藝術啊!很悶的啊!」他只好解釋,「也不是,有時看這種電影也有好處。」寫《香港製造》的過程中,很多東西無形中慢慢走進他的腦袋,從此將他推往另一個境界。
令人詫異的是,《香港製造》尾聲,片中要角持刀上小巴殺人,恰與《紅VAN》情節不謀而合,陳果笑稱,「那就是巧合了,不是我故意的。」
改編電影《紅VAN》相較於小說,在故事情節上未有太大改動,但許多細節則有所變更。電影除注入戲劇張力強的商業元素,更見對人性的淋漓刻劃,陳果說,原作並未聚焦人性,而是強調驚悚,以緊湊的文字鋪排引起網民一陣沸騰,許多人欲罷不能,連夜看完,但陳果仍不滿足,「單純這樣還是欠缺一些東西,因為我們這些麻煩導演,永遠不會甘心純粹拍一個商業片,要拍商業片我早就拍了!」
提及在評論中被一再放大的政治隱喻,陳果反問,「政治的解讀是吧?你看過電影了嗎?有很多政治嗎?」事實上,原著發想乃受福島核災所啟發,由於深圳大鵬半島上建有「大亞灣核電廠」,距香港尖沙咀僅50公里,百萬港人曾連署反對,但仍於1987年正式開工。此核電基地,現為中國運行裝機容量最大者,2010年甚至傳出核洩漏事故,使得港人籠罩在核災陰影之中。網路小說《紅VAN》2012年出版時極受歡迎,「當年香港整個社會變得非常有爭議性,反政府的聲浪非常強大,雖然小說裡沒有太明顯的政治意圖,但主題的背後還是有一點點吧。」反地產霸權或興建核電廠,究竟算不算一種政治運動?陳果認為很難界定,當前似乎只要反政府,就會被標誌為政治運動,是以反核電廠不僅僅涉及環保問題,往往也被解讀成帶有政治色彩。「到我手上改編時,那就好玩了,既然到我手上,就得想辦法把這種社會現象加入電影裡。」
「我說不放任何符號進去是假的,但問題是,做為一部商業片,老闆最忌諱的,就是讓它變成政治電影。」很幸運的,這回陳果碰到的這幫老闆並未在創作上干涉太多,「但改寫的過程中,我也不想把所謂政治的東西抬得那麼高,我只是含蓄地帶到,你看得到就有,看不到就沒有。」反倒是有人過度解讀,一些原來基於政治目的去看的人覺得沒什麼,因而引發另一波爭議。
「我這種導演,必須要有個人立場的時候,我不放,就不像我啊,我不甘心啊,尤其這又是第一次在商業片放這種東西。這部電影在香港算是成功了,但能否延續下去不敢說。我一直在做這種東西,其實是香港觀眾改變了,來看電影這幫人改變了。」據陳果觀察,《香港製造》當年雖轟動,但年輕人對於回歸其實是冷漠的;相隔十幾年再拍《紅VAN》,港人普遍的期待度很高,跟當年有天壤之別,「這幾年的變動,讓觀眾對政治和社會的關心已經變成一種習慣。年輕人已經懂事了。以前我們香港是很討厭政治的,甚至笑台灣的立法院打架,直呼『台灣怎麼這樣,沒禮貌!』,現在香港也差不多打起來了。」
言及香港現狀,陳果屢屢以「慘烈」二字形容,足見《紅VAN》的成功,可說是天時地利的結果。「還好,這種東西雖然沒完沒了,起碼也激發了很多年輕人的覺醒,它一定是社會未來的力量。」時代在變,人心也在變,陳果將現實的大環境織入電影中,反映人性的騷動,雖不露骨,但明眼人一看即知。爭議性隨之而起,在他看來,不失為一件好事,「畢竟主流電影沒做過這種東西,我帶頭做了,而且電影得到成功。」過去,拍片有一潛規則,電影不得觸碰政治,這次陳果索性豁出去,也得到很好的反響,鐵律一破,後面的路就有了更多可能。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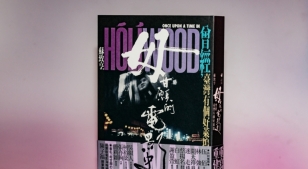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