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但以理)
見面那天,小女孩由她的父親牽著,玲玲瓏瓏地從門外走了進來。她戴著頂小帽,臉上掩不住的興奮好奇,像是要去上幼稚園似的。
她是王文娟在懷孕期間,試圖用想像與文字與其對話的女兒,是《歲夢紀》裡的女主角。原本書應該與女兒一同出生,卻因諸多生活瑣碎拖磨而延遲,如今終於付梓,小女孩已兩歲八個月。王文娟笑說,小女孩是她的第一胎,而《歲夢紀》,則是她的第二胎。
肚裡懷著這個,手上寫著那個;手上寫的那個,正是肚裡的這個──怎麼說都像一種奇特的繞口令循環。「寫書和生孩子在本質上很像,事先做再多準備,孩子什麼時候要正式冒出來,你都不知道。」然而書寫畢竟有個可以捉摸掌握的形式,還有外部現實的壓力(例如截稿時間)橫亙眼前;窩在肚裡的孩子,則只能用自己的感官去觸碰感受,且自有其生理時鐘。「你只能透過胎動、透過超音波,或者她發給你:今天我想吃什麼。一切都是很間接的。」像是星球通訊,王文娟這麼說。
對王文娟而言,《歲夢紀》的書寫,是她上一部散文作品《微憂》的延伸。「以前在當動畫編劇時,故事是為了工作而寫,寫的東西與個人生命經驗沒有太多連結,久而久之便覺愈寫愈空。」在這份空虛的吞食之下,她開啟了「微憂」的寫作計畫,回看平日習以為常的大城小事,藉以重新審視自己。「像是活到了某個階段,就會想回頭去尋自己怎麼來的。」而「微憂」的過程告訴王文娟:創作應該是跟著生命走的,唯有如此,才是一個最健康最自然的狀態。如是,催生了《歲夢紀》。
若是小說,則不免會有一些虛構、一些技藝的門檻與規則。但散文並不必然。「我認為散文應該更自由,應該要處理自己與世界的關係。」是以,走到什麼階段,寫下什麼階段,成了創作者檢閱自己的方式。「畢竟人一輩子能懷孕幾次?也許我不會再有下一個小孩。對我來說,這是一段非常特別、無法分割的經過。」
當然其中也有身為母親的私心。「懷孕之後,會問我父母,以前他們懷我時是怎麼回事?你會發現孕期這段時間,即使孩子已經開始成為家庭的一份子,但其實是不太存在的。」而及至一個小生命確確實實來到面前,每天不斷變化,記憶又會不斷被覆蓋,「你會漸漸想不起來,孩子還在肚子裡那個看不到、摸不到的狀態是什麼。」於是王文娟更希望能替女兒留下孕期的隻字片語,那是她初來乍到、最早的足跡。
在作家身分混入了為人母的元素,王文娟希望藉著《歲夢紀》的完成,讓懷孕的歷程,成為散文另一塊值得關注的主題。「我覺得媽媽們應該都來寫。懷孕這個階段,就是因為看不到也摸不到,所以應該是想像力最豐富的時候。」當孩子呱呱墜地了,隨著時日逐漸成長,父母對孩子的未來想像,會基於愈來愈清楚孩子的個性,慢慢趨向現實。「懷孕是一段比較飄浮的時光,可以開展的光度是更自由的。」王文娟認為,那是一次獨一無二,且一去不返的學習。
「當你知道自己一輩子就是一個人,與當你知道自己要為另一個生命負責,兩者眼中看到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樣的。」懷胎九月與生下女兒,讓王文娟真正跳出了「一個人」的視角,那終究和婚後的兩人生活不同。「假設散文是更貼近的處理自我經驗,有了她之後,我覺得是一個最好的祝福,一個禮物。她讓我不再封閉自己,讓我還有另一個『她』的角度可以去觀看。」


媽媽在受訪,女兒小鷗妹就在旁邊跟OKAPI玩(攝影/但以理)
再從母親的立場回到創作的討論,王文娟點出,懷孕與書寫還有另一個相似的本質,就是空白。與其說自己想藉由文字告訴孩子什麼,不如說她更渴望能夠解碼孩子告訴她的訊息。「寫作是你要自己去生出很多東西,白描也好、比喻或引用也好,必須生出很多橋樑與零件拼湊起來。就像我們以各種徵兆,想像還在肚子裡的孩子一樣。」寫書與生小孩,孰易孰難?「某種程度上來說,小孩會自己長,書不會,所以到一個階段之前,小孩也許比書容易。但之後可能就會愈來愈艱難。小孩是一本永遠沒有辦法寫完的書。」
王文娟總把孕期說成一場夢,「那是一場星球通訊、宇宙平行之夢。」許多讓人似懂非懂的符碼,飄散在空氣四處,引來諸多揣想,或美好或憂心,將這無可取代的九個月填得充實。「我們總是希望能從別人的故事裡,去找出最後屬於我們的這一個──別人的母女關係,別人的相處方式,會不會有可能我們也會發生?後來知道,真的就是想太多了。」或許生命總要有一定比例的無法控制與超乎想像,才會成為世界進步的動力吧。
〔散文.快問快答〕
Q1. 您最喜歡的散文作家是?
王文娟:會定期回頭從書架拿下來翻看的有:唐諾《世間的名字》、約翰.伯格《我們在此相遇》、大陸詩人于堅的《暗盒筆記》、班雅明《單行道》《柏林童年》、布魯諾.舒茲《鱷魚街》等。
Q2. 看過印象最深刻、至今記憶猶新的一篇散文是?
王文娟:陳列的〈呼吸〉,收錄在作品集《人間.印象》。
他寫經過水潭邊聽見蛤仔的嗑叩聲,彷彿一個大自然無明的神祕瞬間,對人間張開眼;文字輕簡綿密,像幻術的網,讓平常多所忽略但時刻真實的存在顯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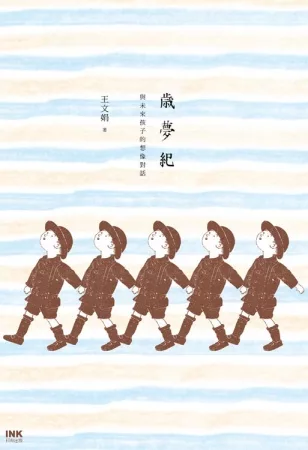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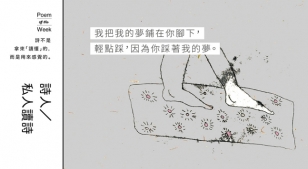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