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我參加她外公的追思禮拜》作者廖梅璇(攝影/陳怡絜)
《當我參加她外公的追思禮拜》作者廖梅璇(攝影/陳怡絜)
參加伴侶親友的追思禮拜並不是件大事,除非你像廖梅璇一樣,她和女友都是女的。
儘管交往11年,廖梅璇早已熟識女友家多名親友,但受限於南部仕紳家庭的倫理與世俗的親屬網絡,她一直被女友拒絕於家庭聚會場合,直到這場阿公的追思禮拜。
很難想像,看來拘謹、沉默又背離人群的廖梅璇,會主動提出要參加這樣的場合。「我和女友在一起的時候,正好是憂鬱症發作時期,我有點被當成病人一樣保護照顧,不太有對外社交的機會。但阿公不同,我去安養院探望阿公的次數比其他親戚更多,理當有追悼的權利。」但在追思禮拜上,她還是強烈感受到異性戀體制以一種含蓄的方式,讓同志自我要求——不要太暴露身分。這樣的含蓄,讓同志在家庭間產生了許多曲折的關係。
希望作為對抗沉默社會的宣示,她將過程寫成散文〈當我參加她外公的追思禮拜〉,近日出版了同名散文集。
「在這種家族聚會,你可以感受到很強的排外性,我意識到『家族』體系對同志的壓迫。」然而,不只是昔日病重的阿公曾對著她們說:「你沒嫁,你嘛沒嫁,你們住作夥?好,好,按呢好。」一名看出她們關係的長輩,從此送女友禮物時,也會同時為廖梅璇準備一份,讓一度覺得自己無法「撼動異性戀體制」的她有了新的體認,「同志的『現身』無論觸發多小的反應,都有意義。阿公的話和這位長輩的行為,讓同志進入一個家族是有可能的,家族的原始意義也因而拓展。」
《當我參加她外公的追思禮拜》收錄的文字,最早可追溯至2005年,當時廖梅璇飽受憂鬱症折磨,為了紓解心中的躁動,提筆寫下家庭關係、伴侶情愛、精神憂鬱與死亡,她不諱言書寫常讓自己陷入鮮明的痛苦情境,連出版前的修改校對,也每每令讓她再經歷一次痛苦。
但痛苦過後,會出現不同的詮釋與細微變化,她說,「就像羽化、蛻皮,新生的皮膚終究會老化,再次於痛苦中剝落,而每次重生的體貌都有所不同,我能感覺到有些痛苦因此解開,有些新的痛苦誕生,這些都讓寫作的苦有了價值。」
 (攝影/陳怡絜)
(攝影/陳怡絜)
廖梅璇以明亮透澈的文字自我揭露,檢視父母是情治人員的家庭背景和憂鬱症,如何影響了她的人際關係與壓抑性格,「可能父母職業的關係,我從小就學會對很多事情保持沉默,但那是很痛苦的,尤其在小小的鄉下地方,同學耳語流傳間隱約知情那個『骯髒的工作』,從那時起,我失去了對世界的信任,家裡也瀰漫一股奇怪的氣氛,父母不談、小孩也不問。」
直到為往生的父親守靈時,她才有機會從母親那兒聽到一些,但已經離開情治工作十多年的母親仍不願深談,畢竟,那是一份窺視別人、影響他人生活的工作。「或許父母的意識形態深受黨國教育洗腦,但純樸的農村成長背景,還是無法讓他們以工作為榮。」
這些是青春期的廖梅璇不了解的,當時她只是不認同父親對黨的熱愛,當父親因為人事鬥爭提早退休,也未選擇回到家庭,而是離開人群,上山務農,「或許爸爸想要的是一個付出就有收穫的踏實人生,畢竟從他十幾歲為了養家投入黨國工作後,黨國就是生活,也讓他改善了家境。」父親在山上仍投入協助宮廟選舉的運作,而那也是黨讓他學會的技能,比他的種田技術厲害多了。
「我想解嚴是世代之間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戒嚴時期的人習慣壓抑自我,仰賴特權階級的恩庇存活,並在台灣跨國經貿活動最熱絡的時期獲取資源,解嚴後人們則迫不及待想改變世界,或者至少實踐自我;但到了我們這一代,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已然建立,又遭逢許多經濟衰退帶來的挫折,資源較優渥的人可以更積極去創造新的機會,缺少資源的人則要面對更嚴苛的生存環境。」廖梅璇說。
在上一代眼中,廖梅璇或許會被劃入「失敗者」的位置,她也坦承,「一開始也覺得失敗很可怕,但失敗久了,就習慣了。」在失敗的陰影下,她對人生乃至世界的苦難反而看得更深邃,「但這一切都建立在『能從失敗中存活』之上,這是我們這世代最悲哀的地方。很多很有才華的人,像大衛林區電影《橡皮擦頭》(Eraserhead)一樣,被削成一支支規格相同的鉛筆,在很荒謬絕望的工作生活中消耗掉自己,或者自殺,那就很慘。」
她自認是悲觀的人,世界正在崩解,人們總要習慣失敗。走到現在,她已經比較能思考憂鬱症對自己的影響和意義,「在大學畢業、為了找工作就醫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憂鬱症,但我高中時已經連購物都有問題,每天只能到同一家小餐館吃飯,」上了大學,開放的人際關係成了她的難題,「當挫折一再發生讓我感到疲倦時,我就開始爽約、不參加活動,別人覺得我沒禮貌、相處起來很悶,惡性循環之下變得越來越嚴重。在學校,有上課、考試的約束,還能勉強維持下去;畢業後開始找工作時,完全要靠自我意志維持規律生活、跟很多陌生人互動,我就完全沒辦法了。當時我一直想,找到工作就能好起來吧……」
廖梅璇沒有好起來,而是開始長期進出精神病院,如今她已無法想像剝離了憂鬱症的人生。在候診區,她看著眾人進出,有年輕人,也有中老年人,有些人調侃憂鬱症是有錢人的病,她苦笑說,「我看到很多底層階級的人也有憂鬱症,只是消失在大眾的視野。」這,如同台灣同志的處境。
或許是台灣在殖民和威權統治下所產生的「靜默」態度,讓眾人習慣以「隱私」、「別人的事」、「不要故意刺激他人」來要求同志或某些邊緣族群,看似含蓄寬容,實則縱容了體制無聲無息的迫害。例如女同志看婦科時,必須回答醫生有沒有發生性關係;被陌生人詢問伴侶關係時,選擇順著社會文化說自己和女友是表姊妹……
 (攝影/陳怡絜)
(攝影/陳怡絜)
幸好廖梅璇還能寫,儘管寫作讓她既快樂又痛苦,她還是努力以節制的文字描述內心巨大的混亂,設法保持一種紀律,卻不要太有秩序,直到文字最終溢出掌控,拿捏到「適度的失控」。
她寫生活的困頓:「關於金錢的回憶,難堪到只能遺忘,卻難以忘記。我曾在麵包店特價拍賣時,擠在瘋狂人群裡拋出十元硬幣,店員扔給我一個麵包。在寒冷骯髒的街頭,我大口吞嚥,兩三口就吃得精光,揩掉嘴角的麵包屑,滿足又有些羞慚,因為心裡沒有湧生足夠分量的恥辱感,當時不知道,往後還有很多機會體會這種感覺。」
她寫憂鬱:「憂鬱症把我變成一個專精嗅聞痛苦的葛奴乙,敏銳追蹤他人的傷痛,駁雜情緒感染著我,在我血肉中蓬勃滋生。」
廖梅璇喜歡的作家大多是女人和病人。「女人、同志和病人看到的風景,與男人、強壯的人完全不同。」在自律神經失調非常嚴重的那幾年,她常在夜裡讀張愛玲《小團圓》描寫痛苦的文字;也喜歡胡淑雯從非中產階級本省女性的角度,檢視批判整個歷史與社會結構,「像一把小小的眉毛鑷子挑痛了全身神經,但同時對生長的庶民社會、弱勢群眾與童年創傷,有非常柔和抒情的描述。」或是蕭紅以沖淡的風格去寫長時期的生活變化,在不堪的人生中撿拾細瑣的快樂。
她知道太多人表面維持正常運作,內心卻有巨大的黑洞。而痛苦之人的內心混亂,是旁人難以窺視的,廖梅璇說,「或許讀者會從我的書得到一點安慰,或許會厭惡這本書。但我希望他們至少開始寫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痛苦,就像當年的我一樣,然後,未來又會有人因為他們的文字覺得被同理,心裡的某塊角落被輕輕的觸及到了。」
延伸閱讀
1. 【書評】吳曉樂:歷劫歸來的人──讀廖梅璇《當我參加她外公的追思禮拜》
2. 【書評】Emily:用少女體寫的血書──讀漫畫《我可以被擁抱嗎?因為太過寂寞而叫了蕾絲邊應召》
3. 【專訪】《橘書》騷夏:生殖的問題,不是「生得出來」的人才配討論
4. 【專訪】八卦之必要──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
5. 【專訪】胡淑雯:小說的本命,該是撼動現實
6. 【專訪】《女子漢》楊隸亞:對我而言,又女又男的狀態可能就是一種「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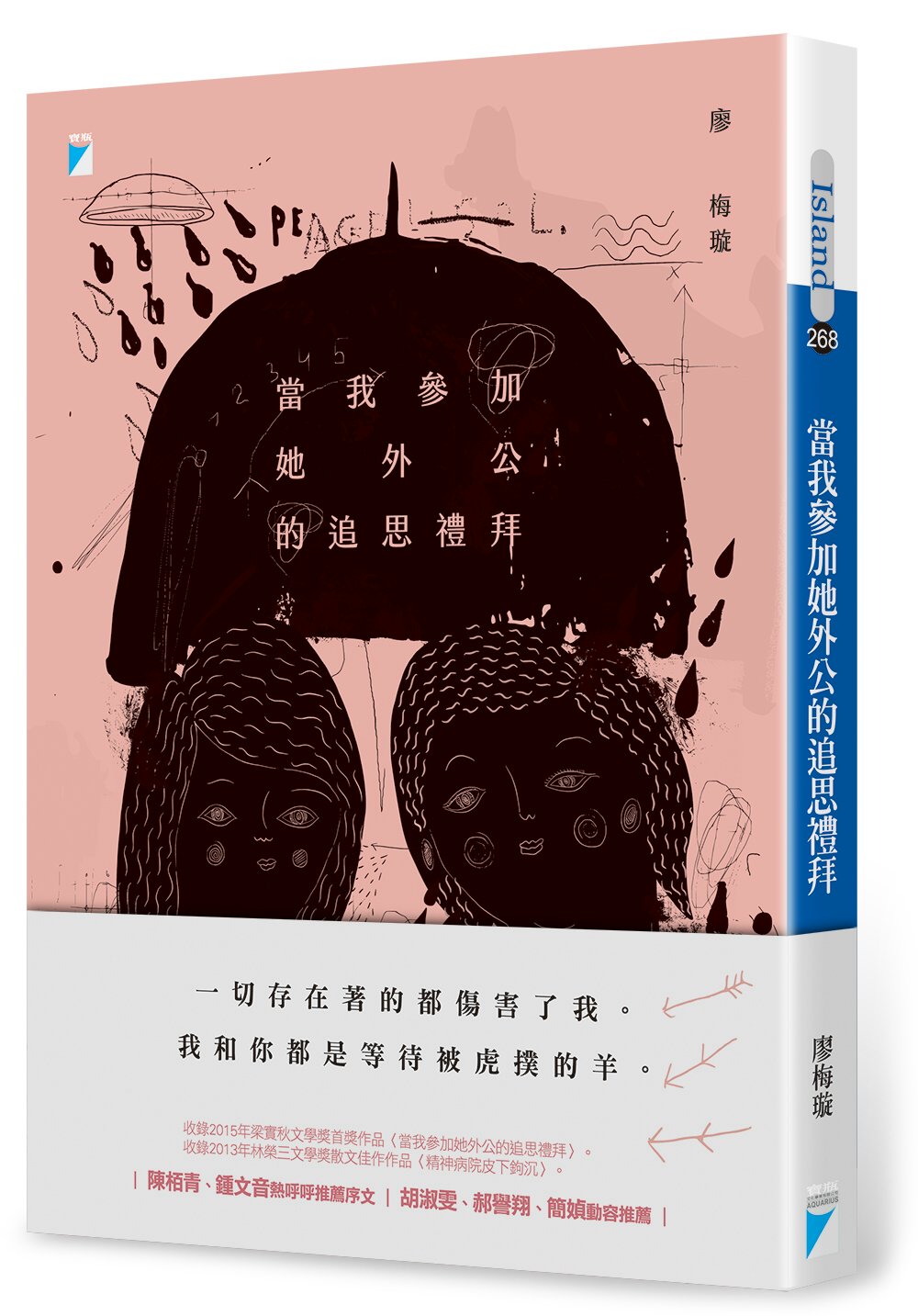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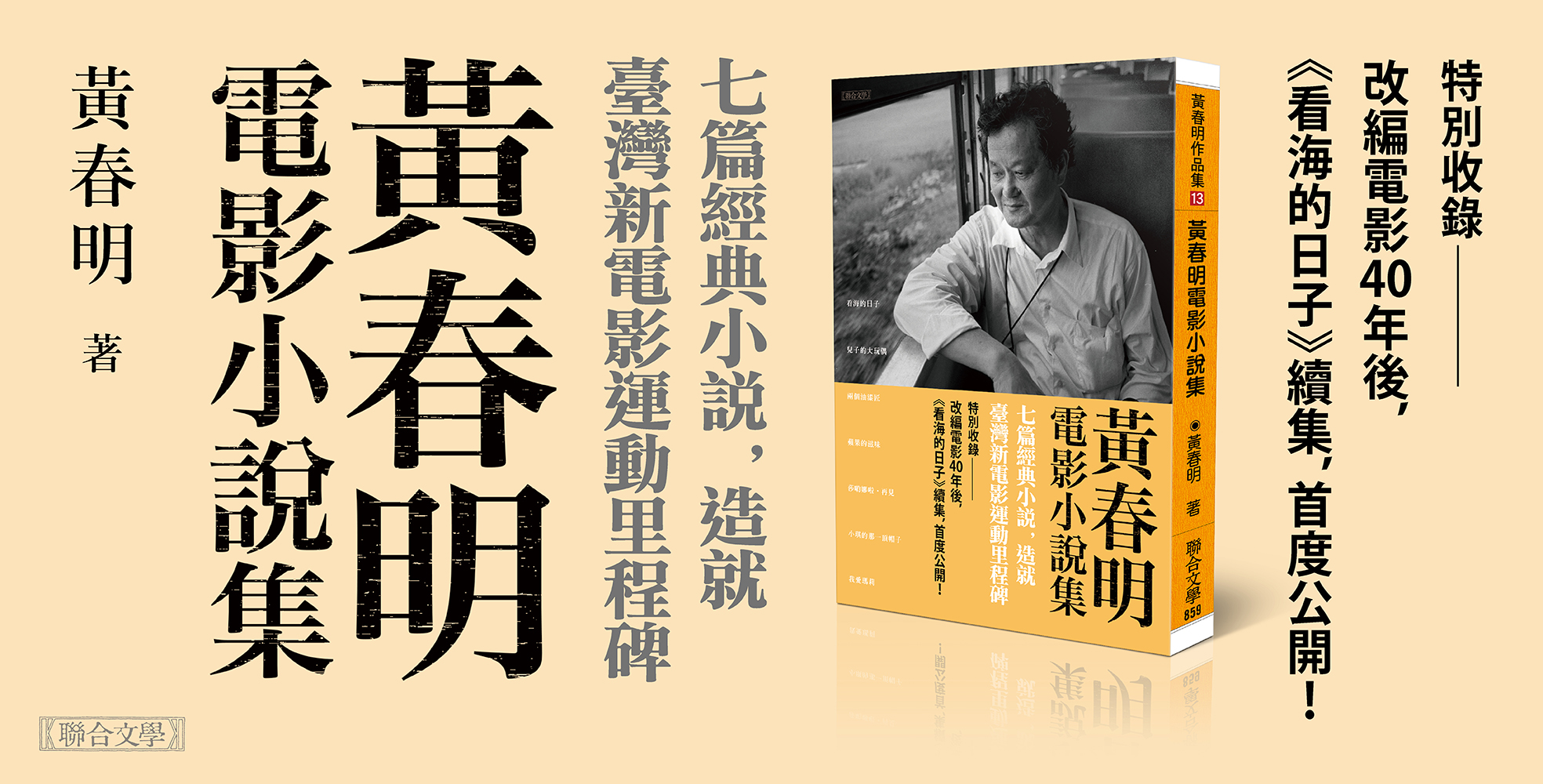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