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是20世紀後半業至今重要的歷史問題,深刻形塑了30多年來許多國家與人們的處境,使人深思現代國家的形式與內涵。轉型正義最簡要的定義是,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處理「正義」的工程。自1980年代開始,大約有80個國家陸續脫離威權獨裁,轉型為民主政體。臺灣也是其中之一。
如果民主化標示了歷史進程的轉向與「斷裂」,那麼轉型正義就是在提醒,歷史並沒有消失,對很多國家來說,也許轉型正義所需要的時間比處在威權的狀態要更久。人類要付出更多耐性與時間,去面對人與人之間在政體的狀態下造成的傷害與壓迫。這些創傷往往也成為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於是裂痕與傷口,透過文學反而成了文化的根脈。
11月13、19日將舉行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本屆模憲法庭正是以轉型正義為題,以李媽兜與杜孝生兩案為辯論對象,並邀請4位來自南非、波蘭、智利與澳洲的學者成為國外鑑定人。11月11、12日兩天,中研院法律所也有國際研討會,將針對韓國、南非、哈薩克、波蘭、匈牙利、德國、哥倫比亞、智利等國家的轉型正義問題進行討論。
為提供讀者另一種理解轉型正義的方式,衛城與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策劃「文學與各國轉型正義」專題,從6個文學家的作品理解該國的歷史。此系列中,蔡慶樺寫葛拉斯與德國,林蔚昀寫辛波絲卡與波蘭,林建興寫波拉紐與智利,黃崇凱寫金英夏與韓國,童偉格寫柯慈與南非,紀大偉寫納道詩與匈牙利。要謝謝6位作家參與這個並不容易的寫作計畫。
# 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活動網頁
# 模擬憲法法庭官方網頁
#「比較憲法視野下的轉型正義」國際研討會
 納道詩.彼得1942年出生於布達佩斯,匈牙利小說家、劇作家、散文家和攝影家
納道詩.彼得1942年出生於布達佩斯,匈牙利小說家、劇作家、散文家和攝影家
桀驁不馴匈牙利──納道詩的《平行故事》
文╱紀大偉
想要藉著閱讀文學進而認識一個國族、一個社會,是一種常見的求知慾。《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作者安德森正是因為曾經被迫放棄在東南亞進行實地田野調查(源於得罪印尼執政者),所以只好轉而研究東南亞文學。但塞翁之馬焉知非福,後來文學研究反而促使他寫完《想像的共同體》。也就是說,文字符號組成的文學可以暫時當作實地調查的替代品。安德森的經驗讓我聯想到白先勇《孽子》被國內外讀者仰賴的情況。正是因為台灣解嚴之前的同性戀文化如陷入五里霧中,讓人難以進行田野調查,所以國內外讀者(包括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才需要暫時藉著閱讀《孽子》來認識台灣的——甚至「中國人」的——同性戀生態。等到人類學家可以在台灣、中國等地進行實地田野調查之後,同志文學才卸除充作田野替代品的責任(以及夾帶的特權)。20世紀末本地同志研究的主要戰場之一是文學,到了21世紀初文學再也不是同志研究首要地盤,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今日台灣到處都是田野,眾人不再需要仰賴同志文學。
國家寓言與強國視線
美國左派學者詹明信(F. Jameson)在20世紀末提出「第三世界文學」可以讀成「國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的主張,並且以魯迅的小說為例。按照詹明信的說法,讀者(預設為第一世界的、美國的讀者)可以藉著閱讀魯迅小說來認識中國這個「第三世界國家」,因為魯迅小說微言大義寫出國家實況。詹明信的主張引起軒然大波;許多國家的批評家(包括左派人士或第三世界國家人士)指控詹明信的閱讀策略太粗暴。但是老實說,時到今日,各國讀者(包括學院批評家在內)卻還是很習慣想要藉著閱讀一國之文學認識該國之真相。國內外研究台灣文學的學者不時一邊批判詹明信,一邊卻有意無意將台灣小說當成台灣社會的維基百科。
我承認我自己也沒辦法脫離安德森和詹明信的陰影。當我終於有機會在匈牙利首都進行觀光的時候,並非第一世界出身的我,也借用第一世界的、美國的視線來粗略認識匈牙利——我身上帶著美國出版的旅遊指南。事實上,位於各種強國之外的各種小國人民都經常不免要藉著美國(或中國等強國)的視線去認識其他小國:台灣人藉著閱讀美國媒體(或中國媒體)的視線來認識菲律賓、緬甸、中東。我手上的英文指南中頻頻用驚嘆號提醒讀者去體驗(同時也要去防備)匈牙利的種種奢華、頹廢。我覺得匈牙利的種種浮誇無度,可以寫成中文的「桀驁不馴」四字。
指南書說,匈牙利的食物是中歐國家裡頭調味最重的,也是最美味的——根據我有限的歐洲經驗,此言不虛。指南書說,散置於布達佩斯各處的公共澡堂恐怕是讀者脾胃不能忍受的,但是值得冒險看看——我實地考察之後,發現美國視線未免大驚小怪。布達佩斯公共澡堂讓人看見同性的裸露、場地的古舊,沒錯。美國人看了可能覺得太放肆,不過台灣人看了應該會馬上聯想到國內各地溫泉。陽明山上各處溫泉大眾池可以輕易超越布達佩斯澡堂的尺度。我同時卻也承認,觀光客的確很容易從有限的布達佩斯經驗(從食物、澡堂等等)輕率推論匈牙利的國族、社會。該地的食物、澡堂等等也可能成為國族寓言,讓人想像匈牙利人的神祕、隱密、肉慾刺激。
桀驁不馴的情慾圖鑑
近日我終於讀了匈牙利傳奇作家納道詩(Nádas Péter)的長篇小說《平行故事》,老實說動機也是要藉著閱讀這部重量級小說來認識匈牙利。我讀了中文翻譯版、英文翻譯版,以及英文媒體的種種書評,卻必須承認納道詩打了我——以及許多英語系讀者——一記耳光。簡而言之,納道詩這部書拒絕被當作「國家寓言」或是「田野調查」來閱讀。
說得直白一點,《平行故事》並沒有讓讀者看到讀者想要看到的匈牙利維基百科,但是卻讓讀者讀到讀者未必想要看到的情慾圖鑑。英文媒體上最常看到的讀者抱怨大致有兩種內容:一,看不懂這部龐雜鉅著在表達什麼(當然也就更不能奢求這部書讓人獲得替代性的匈牙利田野調查);二,不理解書中大量呈現的肉慾細節(尤其是女性、男性、同性之間的性器官特寫)有何意義。前者讓讀者看見太少,後者讓讀者看見太多。我同情這兩種意見,但是我並不會因此否認那些興奮誇讚《平行故事》的書評家。《平行故事》是「不講理」的,但是它同時也的確是偉大的——這兩種評價並不衝突。用我剛才聯想到的說法來說,它也是桀驁不馴的。
我試圖來解釋(或,「非解釋」)「平行故事」這個書名。這個書名讓人想像書中有兩個角色(兩個人、兩種個性、兩個城市或兩個國家)持續來回對話,如同《傲慢與偏見》、《雙城記》這樣的書名所暗示。但是這部書並不輕易提供單單一組貫穿全書的對照組。書中出現大量對照組,一組組的人物、一組組互相呼應的城市、一組組對立的國家,讓讀者應接不暇。在台灣文學中比較相似的例子或許是蘇偉貞的《沉默之島》:書中有兩條小說女主角晨勉的故事線,兩線時而平行、時而交錯、時而互相矛盾、時而互不相干。抓住這兩條故事線互動韻律、互動節奏的讀者會覺得《沉默之島》的敘事結構別出心裁、格外精采,但是抓不住的讀者(也不是這種讀者的錯,而是這種讀者跟書的律動感無緣)就會覺得《沉默之島》不知所云、而且女主角一直在做愛。《平行故事》就像是《沉默之島》這樣,只不過《沉默之島》可以比喻成兩種樂器的室內雙重奏,但是《平行故事》則是規模宏大、氣勢磅礴許多的交響曲(外加合唱隊)。至於書名的「故事」可以解讀為「短篇小說」。看起來「故事」跟「小說」是同義字,但是「故事」(短篇故事)就體質而言是跟「小說」(指長篇小說)相反的:前者是碎片,後者則渾然一體。故事/短篇小說集合成一冊,叫做「小說集」(短篇小說集)而不叫做「小說」(長篇小說),因為小說集子裡的各個篇章大可以各自獨立、大可以各自拆夥,但是小說裡的各章節按照慣例是要前後呼應、首尾相連的。
如果《平行故事》被當作實驗電影作品,可能就比較好懂:幾十個經常互不相干但是偶爾互相呼應的實驗短片,組合成三大單元(對應《平行故事》包含的三部書),再合併成為一部放映時間超長的電影(即《平行故事》)。這種組合在歐洲前共產國家不乏前例,例如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的《十誡》:十個短片,大致互不相干但是偶爾互相呼應,組成一整個《十誡》。觀眾一連看完《十誡》的十個單元,的確可以掌握昔日波蘭的眾生相整體——或曰波蘭的國家寓言。偏偏《平行故事》是小說而不是電影,而且《平行故事》的野心格局又比《十誡》龐雜甚多。
禁忌中求生
那麼,《平行故事》不斷煞有其事呈現情慾追逐細節,究竟是為了什麼?作者在風月上頭著墨這麼多,難道沒有寄託任何寓意?從中文翻譯者余澤民特別詳細撰寫的〈譯者序——去向身體殿堂的更深處〉和〈譯後記——這張桌子行嗎?〉 可以得知,作者納道詩樂於公開演講、跟評論者打交道、被主流文壇肯定,甚至堪稱他是各國譯者共同的大家長(他促成各國譯者在匈牙利共同開翻譯心得分享會),但是他偏偏不提供作者詮釋作品的心得。《平行故事》的性故事有沒有寓意,不能問作者,只能問讀者。
在全書滔滔不絕的性愛(或是有性無愛)場面中,我想要特別舉出「猶太男孩玩弄自己性器官包皮」的意象。書中不時出現的包皮特寫已經引發英語系讀者紛紛討伐,覺得過度、噁心、不忍卒睹。但是不可否認,性器官的包皮有無,在20世紀歐陸歷史上,正是決定一個歐洲人是不是猶太人——是否要被納粹逐出歐洲(或逐出人世)——的關鍵標記之一。納道詩不斷在讀者眼前揮舞包皮的圖像,桀驁不馴,可能就是要讓讀者深刻感受到猶太人(或許泛指各種社會邊緣人)曾經經歷的不堪倖存方式,儘管要以讀者的噁心反應做為代價。
至於書中在黑夜追索男性之間的一夜情(彷彿像是在《孽子》裡頭的新公園一樣)也大可能呼應匈牙利人的惡夢經驗:擔心自己被陌生的性愛對象出賣,擔心自己被警察這種國家機器打手當作祭品,擔心面對自己飛蛾撲火也要求歡的私慾,都讓人可以進行「跨越國界」、跨越「歷史時期」、跨越「性身分疆界」的聯想。就算是置身於台灣、21世紀、不是同志的國內讀者,也有可能「認同」這批午夜的獵人:禁忌的愛就是被詛咒的求生原慾。
到頭來,到底能不能夠透過文學瞭解一個國家?這個常見的、打如意算盤的求知慾被《平行故事》敘事否決掉了。《平行故事》反而用肉慾來複雜化這種求知慾,讓肉慾逃逸閱讀者的輕易收編企圖,讓閱讀經驗置之於死地而後生。
紀大偉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膜》,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酷兒狂歡節》,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
【時代的錫鼓響起,誰在清理戰場?】系列專文
01|蔡慶樺:流著淚剝下我的外皮──葛拉斯的罪責
02|林蔚昀:猴子輕柔的鐵鍊聲──從辛波絲卡的詩,看波蘭百年來的歷史難題
03|林建興:1973年之後的波拉紐
04|黃崇凱:你的祖國正在呼喚你──讀金英夏《光之帝國》
06|童偉格:就像人不能豁免於政治──成為南非他者的柯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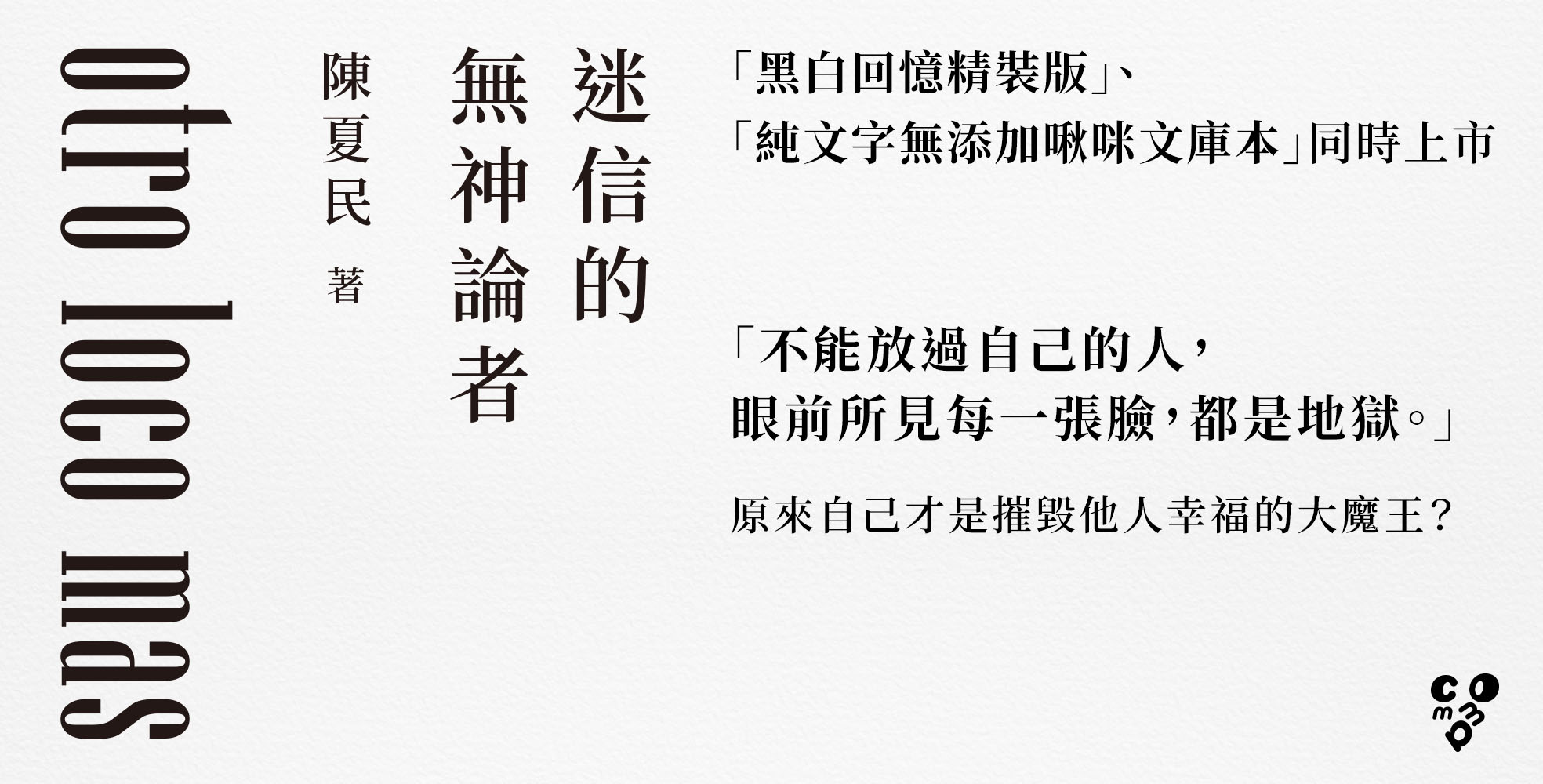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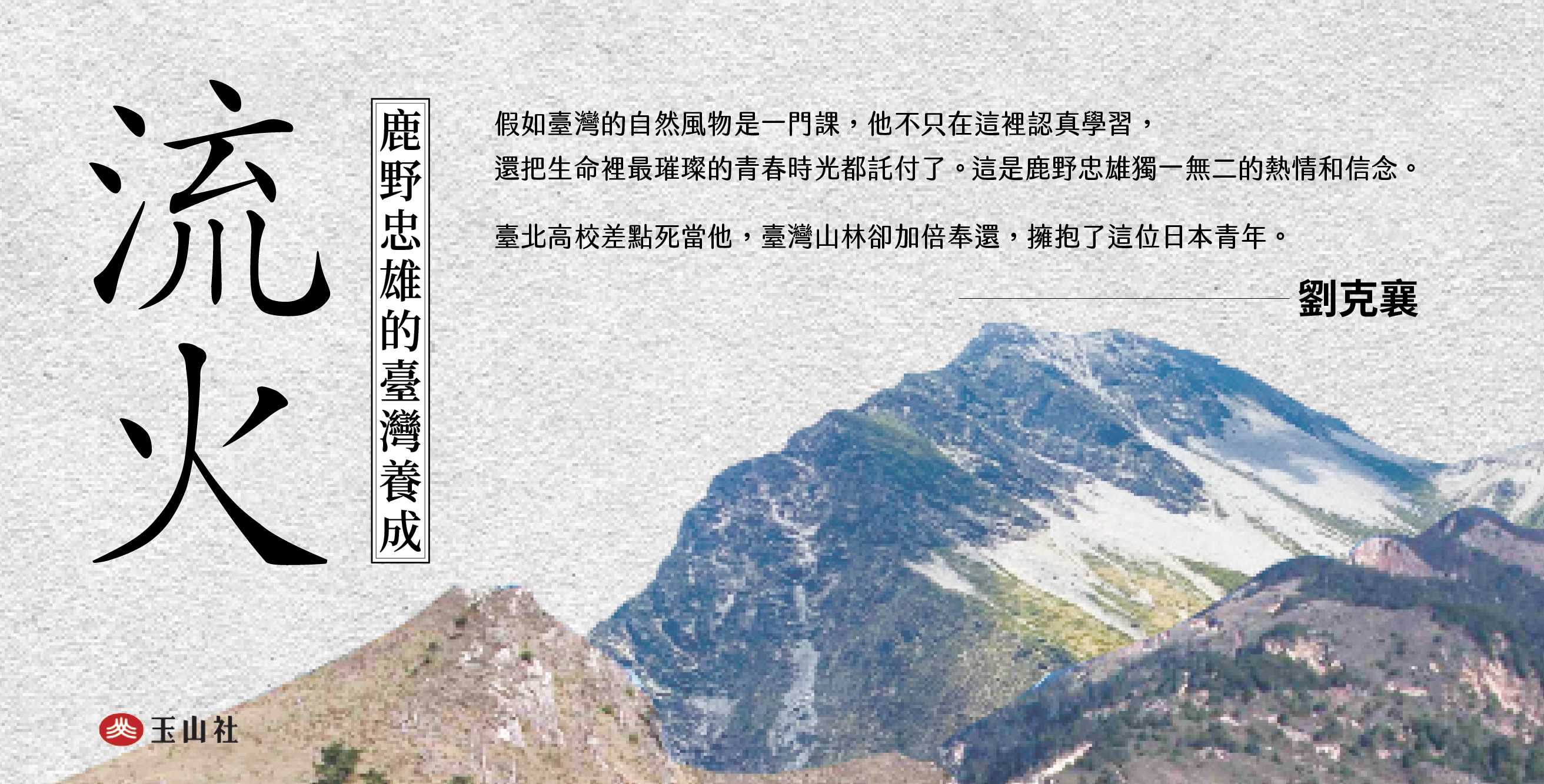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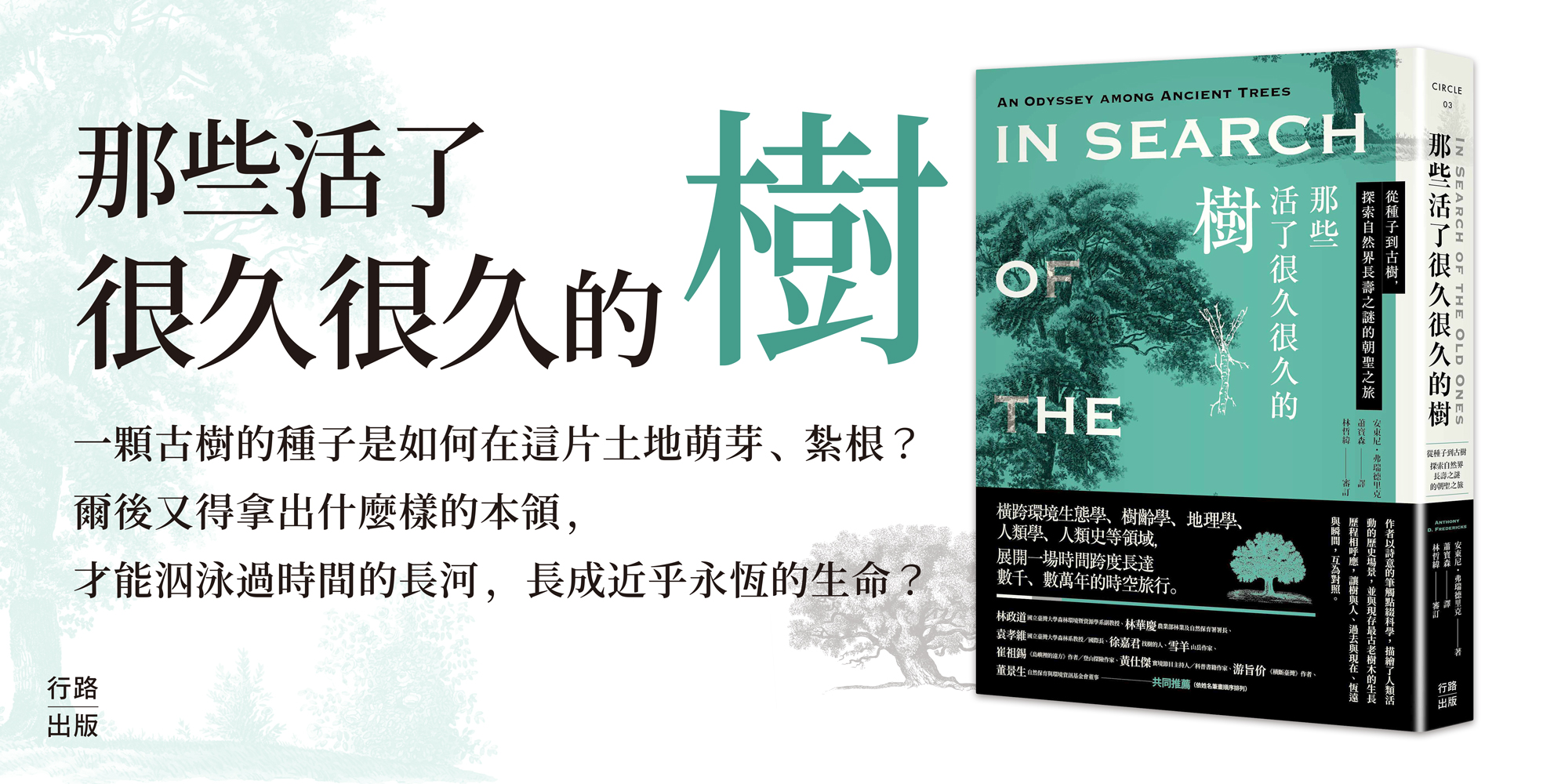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