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顧城的詩至今仍具有極大影響力,他留下許多名句經常為人們引用,包括: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一代人〉
一切都明明白白/但我們仍匆匆錯過/因為你相信命運/因為我懷疑生活……
──〈錯過〉
我覺得/你看我時很遠/你看雲時很近。
──〈遠和近〉
文╱鄧九雲
我想因為我不懂讀詩,所以說話特別大聲。不知道現在的學生,國文課是不是還要小考默寫詩,錯一個字扣一分,錯兩個以上,全句罰寫。高三模擬考的時候,我第一怕改錯字,第二怕的就是新詩選擇填空。錯字有公式,背起來就對了,有時粗心看走眼罷了。但,詩,哪來的公式?老師我覺得你的解釋都好奇怪,你怎麼會知道詩人「創作」的動機呢?我常皺眉頭瞪著老師解新詩選擇題,卻從來沒有信過他們。
其實我曾有機會喜歡讀詩的,因為我要爸爸幫我訂的第一本刊物,是《笠詩刊》。但那裡的詩對國中的我來說實在有點難,像在我眼前一堆丟在水裡的單詞,有的太重沉入水底,有的輕輕浮在水面,偶爾還能順手撈上幾把。於是詩對我而言成了專屬辭典,不過詞彙的或輕或重全是我與時空化學效應的結果。於是我捧著一年份的詩刊,大聲咀嚼被我撈上岸的字。他們說,原來妳喜歡讀詩呢。
長大後,我卻只讀短篇小說,讀很多讀很久,拿著鉛筆在小說裡面的文句旁畫來畫去,他們說,你的小說重點還真多。我說,那些不是重點,是詩,我在找詩。那時我習慣看完一本小說後把喜歡的文句逐字打成一份檔案,自己欣賞同時分享。某一天,已完全不讀詩的我無意間讀到顧城最有名的那兩行詩: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那是一個很憂愁的夜晚,我瞬間被遞與了一把手電筒。於是我開始尋找顧城的詩,卻發現在台灣不易取得。那時我人在內地,在某一篇文章寫了台灣好像買不到顧城的書,結果好多人說買了書要準備給我,我說我拿不了,請大家已買書的就捐到一個叫「微笑圖書室」的公益團體吧。結果幾個熱心的微博同學甚至集思廣益組織了一個「閱讀九九」的活動,希望能不定期的捐贈書籍給偏遠地方學校的小朋友。我選定了一個四川石河村小這間學校。單純因為我奶奶是四川人,滿口四川腔國語。前往出發的那個星期六,四川又地震了。志工們已經在路上,開了七八個小時的車,終於抵達。那些小朋友都是留守的學生,家裡狀況好的孩子都去城市裡了。留守孩子一年只能見到父母親一次,一天只有兩塊錢生活費。志工們說孩子很靦腆有些不知所措,因為好像忽然從圓圈的邊緣被放到圓心上轉得有些昏頭轉向。
我壓根沒有想到不懂讀詩的我,大聲說話時最後能推送一份關懷到那麼遠的地方。或許就如古希臘傳說的一樣,最早的詩人是神的兒子。能夠精煉人類的七情六慾成短短的文字重新組裝,好比卡夫卡說的那種「凝結物」一帖「清醒劑」。所以才能力大無窮。
開始寫小說的這幾年,我重新開始戰戰兢兢撈著我水裡的詩。我追隨特定詩人,好好空出一隔書櫃來安放他們。我在自己的水池裡用手輕輕撥啊撥的,每天浮現的與那些漸漸下沉的其實都不一樣。運氣好的時候,一首完整的詩可以輕輕浮起,我便能任性大聲地讀給自己聽──
我希望
每一個時刻
都像彩色蠟筆那樣美麗
我希望
能在心愛的白紙上畫畫
畫出笨拙的自由
畫下一隻永遠不會流淚的眼睛
我在詩的末端畫上一顆眼睛,謝謝顧城給了我不用流淚的理由。
鄧九雲
演員、作者。戲劇作品遍佈中港台,跨足電影、電視與劇場,近年致力將自己的小說結合戲劇呈現,創造新形式劇場。文字著作Little Notes系列:《Dear you, Dear me》《Dear dog, Dear cat》、《我的演員日記》、《用走的去跳舞》、《暫時無法安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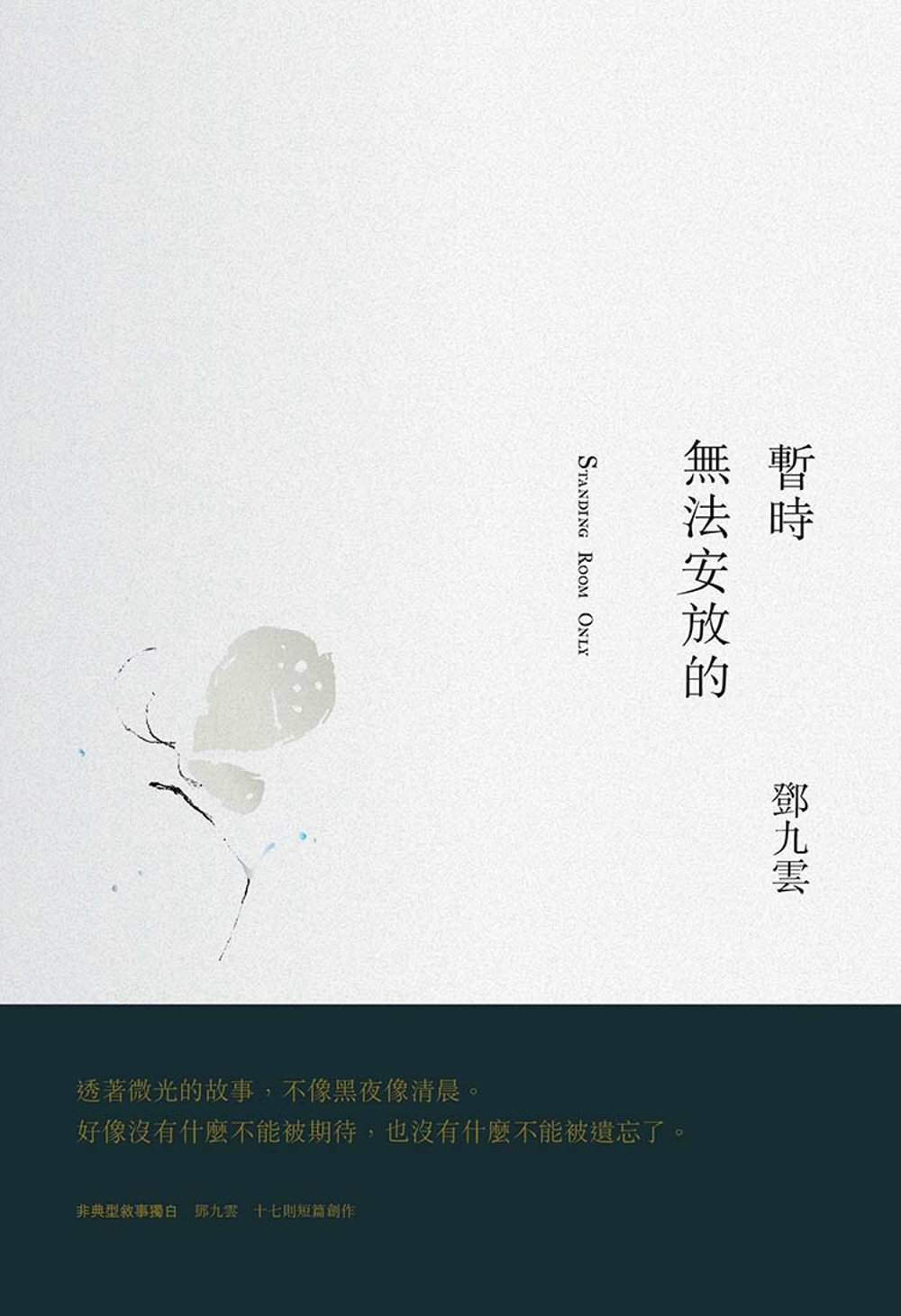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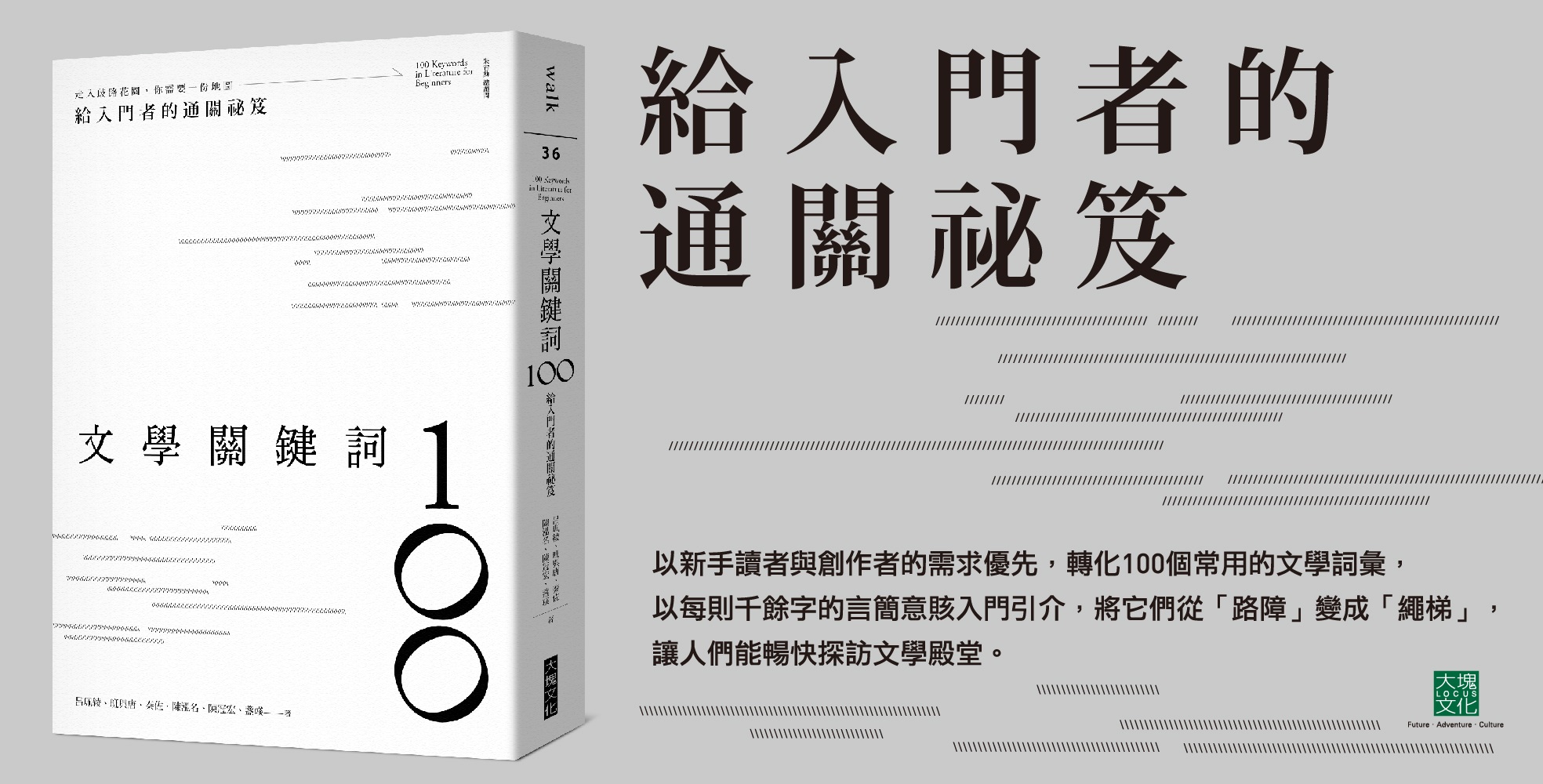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