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人作家唯色。(攝影/白丁,照片提供/時報出版)
藏人作家唯色。(攝影/白丁,照片提供/時報出版)
如同時光倒流 認識的喇嘛們向我點頭 微笑
就像是我每天都在此時進廟朝佛
如同時光倒流 數不清的藏人排著長隊
藏巴 康巴和安多 捧著哈達 握著紙幣
舉著酥油燈或者盛滿酥油的水瓶
如同時光倒流 我又沒排隊 厚顏著
像個遊客 徑直走向覺康
人頭攅動 人影搖晃 人聲訇響 金色的光芒中
我又見到了覺仁波切 伏地膜拜時不禁淚水滑落
──唯色〈回到拉薩〉,節錄自詩集《雪域的白》
藏人作家唯色新作《樂土背後:真實西藏》,罕見關於西藏優美的描述,反而多的是拉薩軍警四處站崗、藏人接二連三自焚、申請護照難如登天等情事;她筆下的西藏,是一般世人看不見的西藏。
唯色曾任《西藏文學》雜誌編輯,2003年出版散文集《西藏筆記》,被中共當局判定有「嚴重的政治錯誤」,因她拒絕承認錯誤,在此書出版、查禁一年後,遭開除職務,只得遷離拉薩,移居北京,與同為作家、鑽研西藏和新疆議題的丈夫王力雄同住。
搬到北京十二、三年了,她迄今仍未習慣,心裡殷切盼望能在拉薩多住些時日。基本上,她每年會在拉薩住兩三個月,然而,2008年3月西藏人民大規模抗暴,她只待了七天,2009年及去年亦未能回成拉薩,皆是因為局勢的緣故。唯色對於自己的「不在場」深感缺憾,甚至羞愧。因為不在場,她成了一個「他者」;因為不在場,她無從見證、無從揭露和訴說。
自2008年全藏爆發抗議以後,做為一個以記錄和見證為本的寫作者,唯色每每回到西藏,都遭遇種種限制和困厄。諷刺的是,儘管北京是中國帝都,強權的中心,數年來她亦常遭受「喝茶」、軟禁、監控等對待,然而相對在拉薩,她似乎還是自由得多。
唯色長期受跟監,行動被高度限制,筆下卻愈見勇健。她的敢言,為她贏來挪威作家聯盟頒發的「自由表達獎」、(印度)西藏記者協會頒發的「無畏言論者獎」、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2010年度「新聞勇氣獎」、荷蘭2011年度「克勞斯親王獎」、美國國務院2013年度的「國際婦女勇氣獎」等多項重要國際獎項,儘管她從來無法出境親自接受表揚。
在《樂土背後》中,唯色屢屢吐露對自由的想望。儘管《西藏筆記》的出版讓她惹上大麻煩,陰影至今在心頭徘徊不去,她卻不感到後悔。「從另一方面來說,我也因禍得福,從此走上獨立寫作的道路,儘管艱辛並時有危險,卻領略到精神的自由多麼寶貴,使我深感慶幸。」
唯色說,「拉薩是我的故鄉,我一往情深。」正是這份情懷,使她堅定、不懼怕,一天天深化的民族自覺,是她最堅實的依靠。
以下是OKAPI 這次的訪談
Q:請問您尋常一天的作息大概是怎麼樣?
唯色:我是那種晚睡之人,或者說故意不睡覺的人,所以寫作與讀書通常是在下午與晚間。上午總是彷徨,似乎是要調整心情,我不是那種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立刻進入寫作狀態的人。我願意宅在家中,臨睡前會磕至少一百零八個等身長頭(其實將近兩百個等身長頭),邊磕頭邊默誦一些佛教心咒,及祈願尊者永久住世的祈禱文等。
Q:您出生於拉薩,小時隨父母離鄉,20多歲才又回到拉薩,能否談談您對拉薩的情感?成年後選擇回到拉薩的理由是?
唯色:對於拉薩的感情,隨著時間推移愈來愈深厚,可是我卻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屬於拉薩。雖然我生在拉薩,雖然我在拉薩度過了20多年,可是人生最可塑的那些年月,我卻是在遠離拉薩但又想像拉薩的異地度過的。那麼,我的拉薩人的身分是否不存在呢?不是,在我的內心深處,我已經認可自己就是拉薩人,即使我也曾把父親的籍貫拿來當做自己的家鄉,但說實話,我在父親的德格老家所感受到的全部激情,遠遠遜於在拉薩的每日激動。
成年後選擇回到拉薩,既為鄉愁,更為詩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總是覺得,只要回到拉薩,我就能寫出好詩。然而,後來我又不得不離開拉薩。而今想到拉薩,內心總是會被牽扯。這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如拉薩這般令我思念。我總是愛說,這世上沒一個地方比得上拉薩。但我也知這只是對我而言,或者對一些人而言。很多人不會這樣,因為拉薩畢竟與他們無關。
也因此,我更願意寫一部拉薩的地方志。所謂地方志,其實並不完全。我之所以選擇記錄或描寫的地方,更多的與我個人的經歷相關,尤其側重這幾年的變化和故事,而不太涉及歷史背景、典故往事之類。可以說,我所寫的地方志,只是一個人的考古史。恰如這句話:歷史成為一種地理,回憶正如考古。所以我寫的是「新編地方志」。
Q:「藏人」身分對您的意義是?什麼樣的成長背景、教育或事件,激發了您的民族/文化自覺?
唯色:「藏人」的身分對我很重要,可能更高於我詩人和作家的身分。我現在保留的詩中,最早的一首是在1984年寫的,當時我已入讀西南民族學院漢語文系,是大一生,我的同學中有十多個「少數民族」和漢人,以漢人居多。這首詩的名字是〈印──致某些人的偏見〉,依稀記得當時我與幾個漢人同學發生了爭論,我當場寫下這首詩,並用力抄寫在教室裡的黑板上,把他們都給震住了。其中有這樣的詩句:「那顆散發著/酥油糌粑味兒的印/深深烙在我心上/我不沮喪/更拒絕你冷漠的/一瞥」。現在重看這首稚嫩的詩,我驚訝的是當時18歲的自己已經有了民族意識。而且,很顯然,當想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時,我的方式是寫詩。
對於我個人來說,在我以今日的方式、風格寫作之時,我逐漸實現的是對自我的「西藏身分」的表達。而這個身分是與圖伯特的地理、歷史和文化,以及無數個博巴(藏人)的故事和身世緊緊相連的。
是的,身分認同與個人的身世、其他人的身世,乃至整個民族的身世是密切聯繫的,否則從何談起有關身分的問題?又有什麼要緊呢?
而對於個人的以及其他人的身世的重新述說,實際上也就是在恢復做為個人和群體的記憶。記憶才是最重要的,因為記憶乃是一個人、一個群體的存在之依據。而在不斷竭力的記憶之時,曾經的焦慮真的已經淡化了。可以說,如此對身世的重新述說反而是一種治療。至少對我是這樣的。
 在藏區東部康地旅行時見到的宣傳看板(攝影/唯色 提供/時報出版)
在藏區東部康地旅行時見到的宣傳看板(攝影/唯色 提供/時報出版)
→點「下一頁」,繼續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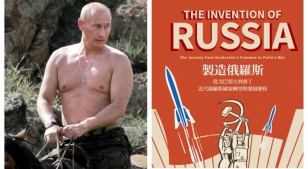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