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代主義鬼才七等生與跨媒材藝術家阮慶岳的忘年之交早就傳為美談。這兩人的作品裡頭剛好也都有男同志出現。阮慶岳的文學作品本來就以同志課題著稱,但是七等生作品中的同性戀則很少被人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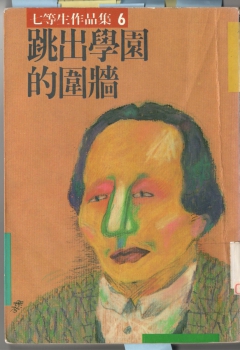 跳出學園的圍牆
跳出學園的圍牆
七等生文學長久以來被貼上「不正常」、「不道德」、「變態」等等標籤。不過,曾經被視為不正常、不道德的同性戀者卻幾乎在七等生作品中缺席。原來,七等生筆下的畸戀、綺情終究還是發生在異性戀體制裡頭。但我偏偏不信邪,還是在七等生的《離城記》找到同性戀的「心鬼」。
根據七等生專家張恆豪,《離城記》這本集子收集了七等生從1972年到1974年之間的作品,相當於作家的33歲到35歲。這本集子收錄了《削瘦的靈魂》這篇中篇小說;這篇小說曾經以《跳出學園的圍牆》之名出版單行本。
這篇小說所指的「學園」,在書中稱為「土苑」,很容易讓人聯想七等生曾經讀過的師範學校。小說中的主人翁「我/劉武雄」跟七等生一樣,主修藝術科(美術),也都因為在校喧鬧搗蛋而要被校方退學。小說中的「我」在學校住宿,因而經常目睹體育系男生在浴室內的健美裸體。這些裸體剪影可能讓讀者想入非非,但只會讓「我」想到男人之間的競爭(美男裸體對「我」來說只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低等動物),並不會讓「我」想到男男情慾。
「我」天天跟肌肉裸男相處而不動心,在我看來並不是因為他完全對同性戀無感,而恐怕是因為他有意無意捍衛自己的異性戀身分。我說「在我看來」,是因為我猜我的解讀大概不會被小說中的「我」或作者七等生接納,但這也沒關係。我並不認為「我」這個角色是同性戀者,但我相信他有「心鬼」:他一看到讓他聯想到同性戀的人(不管對方是不是真的同性戀者),就會心中有鬼,排斥對方。我重視「心鬼」,也就是要強調「同志文學/同志文學史的參與者並非只有身分確切的同性戀者,也有對於同性戀疑神疑鬼的異性戀者」。這種疑神疑鬼的異性戀角色未必讓一篇文學作品變成「所謂符合標準的同志文學作品」,但畢竟涉入了「同志文學」這個研究領域的地盤。
在小說第六小節,「我」拜訪教務主任「閔真先生」:三十八歲、芝加哥大學教育博士、曾結婚但已經離婚。「我」來到閔真先生的宿舍,發現閔真「深沉的注視,好像是專門要對付異性的。」──也就是說,「我」認為他自己在男主任眼中形同異性/女人。在「我」眼中,主任看起來憂鬱、白皙、像外國男明星(馬龍白蘭度)、留著「比一般男人較長而好看的頭髮」──這些形容詞對於同志文學的老讀者來說並不陌生。主任一直說「我」好瘦,還說「我」有點像「蒙哥茂來克里夫特」(Montgomery Clift)──也就是說,主任似乎關心「我」的身材和長相。美國老牌明星蒙哥茂來克里夫特的男同性戀身分如今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不過小說中的主任和「我」未必知道這回事。
這兩人相談甚歡,因為主任完全不同於迂腐的老師,而是博學多聞的雅士。但是「我」卻不知為何越來越心慌。在這篇小說中,「我」經常自言自語,而且將「我」稱作「你」。「我」對自己(也就是「你」)說:「假如閔真先生在跟你碰杯,我就會醉在他的舒服的屋子裡;你實在很願意乘機醉一次;不過,我看閔真先生那對專門對待異性的眼睛,會不會把你當成獵物,像蘇格拉底那群窩囊的希臘知識份子,所以我決定告辭了。」這一小節最後一句話則顯示「我」「看不起」主任這種人。「怕被當成異性/女人」以及「像古希臘哲學家」都很明白表示「我」心裡在惦念同性戀的威脅。「我」雖然跟主任互動愉快,但是他怕了,而且還要強調自己看不起對方。
「我」這個不愛守規矩的叛逆男孩,其實乖乖捍衛異性戀體制。可能正是因為心中有鬼,所以「我」不論看到多少體育系男生的肉體都不會想歪。
我曾經在OKAPI談過阮慶岳的作品〈騙子〉。日本廣島大學三木直大(翻譯過多種台灣文學作品,例如陳克華詩集等等)也特別撰文分析阮慶岳的短篇小說〈廣島之戀〉(收錄在《愛是無名山》)。在阮慶岳發表的眾多男同志主題故事中,〈騙子〉和〈廣島之戀〉剛好都啟動了「鬼」,尤其是「心鬼」。〈騙子〉中主人翁曾經跟一名神秘男子親熱同居,但後來對方突然人間蒸發;〈廣島之戀〉中的男同性戀者去日本旅行一直感覺(妄想?)自己被曖昧對象(也是男同志)跟蹤,後來才發現對方早就逝世,照理說不可能跟蹤主人翁。這兩篇小說的特色顯然不是「這裡也有同性戀者喔」(彷彿臉書打卡),而是「男同志被心鬼折磨」的困境。
這兩者的心鬼和七等生筆下的心鬼並不相同,或許「方向正好相反」:七等生的(自以為是)異性戀角色發現,同性戀像鬼一樣撲上「來了」(這是他的心鬼,跟主任是不是同性戀者無關);阮慶岳這兩篇小說的角色明明跟男同性戀者靈肉糾纏,但是他們扼腕發現曾經「糾纏自己」的同性戀像鬼一樣「走了」,不留痕跡。不管鬼來了還是走了,都讓主人翁難受。
文學中的同性戀者像是鬼一樣來去無蹤,讓「人我分界」以及「人鬼分界」龜裂。阮慶岳的長篇小說《重見白橋》則更野心勃勃地述說了一個龐雜的鬼故事:主人翁「我」被一個自稱是「哥哥」的陌生男子登門拜訪,發現對方糾纏不已、身世成謎,最後發現對方恐怕不是真人而是鬼魂。我並不願斷定哥哥是真鬼還是假鬼(小說故意含糊其辭),而要說這部小說的鬼可以讀成「心鬼」:就算他不是真的鬼,他對作者(阮)、讀者以及主人翁「我」來說,正是「孤魂野鬼」。他形跡可疑,跟俗世格格不入;他可能就是被「我」親生父母裁定的私生子、被墮掉胎兒的化身;他更是被「正常社會」驅逐的男同性戀者。講究正常的主流社會可以接納某些形象良好的同性戀者,但是社會(以及比較主流的同性戀者)恐怕無法忍受這個哥哥。
例如,「我」發現,哥哥和社區的「智障青年」在公寓樓梯間的窗戶露出頭來──原來這兩人一上一下趴在窗台上雞姦。哥哥引誘「智障青年」趴在自己身上幹活(頁106-109)。這個畫面觸及了同性戀,以及幾個議題:一、哥哥的性交是「公共的性」,可以被路人看見;二、哥哥引誘身心障礙者雞姦,究竟是跟對方同樂還是剝削了對方;三、如果這個畫面純屬「我」的想像,並沒有真切發生(畢竟哥哥可能是鬼),那麼曾經跟女人結婚的「我」為什麼會幻想出這個奇異的畫面?「我」也得知,哥哥曾經把異物塞入肛門,求取前列腺快感,結果需要動手術切開肛門才能取出異物(頁137-138)。最後哥哥終於向「我」承認,人盡可夫的哥哥是一個愛滋帶原者(頁176)──在台灣文學中,像哥哥這樣放浪的角色似乎非要身懷病毒才能夠符合作者、讀者的期待。
俗話說,人比鬼更可怕。讀者保持這種洞見查看七等生和阮慶岳的鬼故事,應該會發現鬼和心鬼說出了太多讓人難以承受的實話。
紀大偉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膜》,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酷兒狂歡節》,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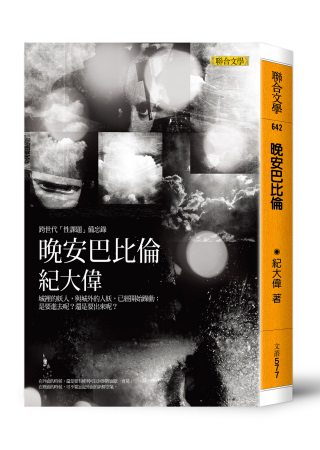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