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厚心得
所以我們不得不,用故事和故事搭建一整座違建般的文明,抵抗並且趨近。
作者:瑋士柏 / 2008-10-02 瀏覽次數(4259)
西夏,最神秘迷人的一段故事的標籤,這群從幾千年前就被以半人半獸稱呼的「羌」人,周代之後離開了曾經比肩的漢屬的文明系譜,到了11世紀華麗的回歸,從遊牧到一個王朝的興起,從漢文明再奪去的農耕與製瓷技術,甚至包含文字,都以更繁美的姿態到達頂尖,然後覆滅。
鐵甲騎兵屍骨化為風沙,當年瓷器遠在歐洲被發現,一整套文字現今乎無人能全解,這群黨項羌人,如一滴精一滴血融進污冷大海,從此不再能辨。
這如同其他許多輝煌過後覆滅的王朝故事,但從哪個角度去投射自己的身世,似乎都還無法抵抗更強大的空虛,和與之相應濃郁的種種或善或惡的情感。
那麼駱以軍在這部新小說《西夏旅館》裡,為何還借著這個可以超現實的華麗故事作為隱喻?
駱以軍的小說從自從首本結集的《紅字團》之後,在每則精彩的故事與故事之中與之後,幾乎都是創作者心靈以身犯險以意逆志的一次次倖存展演。故事或者長到一個篇章,或者短到只在幾句對話裡即被用掉,之中太多故事可以是小說家從容鋪展的材料或者起點,但在駱以軍的小說裡卻這麼輕易地就隨手用掉,彷彿是以與更巨大且重要的什麼性命相搏,而小說家手上有的只有故事。
之中最艱難的部份在於,小說家太過明白那些故事本身的形狀,那種種敘事傳統帶有著一整組意象與力量,以至於一但誠實,就無法假裝那些敘事框架不存在,所有偉大的敘事傳統都成為必須遁逃,或者接招的惡夢,但從另一角度來說太過熟練,以至於還得必須時時抵抗著媚俗。而這敘事傳統如天地不仁,沒有惡意,也就無所謂在乎任何一位站在他面前的作者,誠實的小說家知道沒有魔王可以打倒,也甚至不是個角色,惦惦自己,坦承明白傍身的還是只有,那些最自豪也最羞於示人,編造的故事。
這次駱以軍放棄第一人稱的「我」,型塑了故事裡的主角圖尼克,讓「他」為了亡妻,試著「搭造」一座西夏旅館,彷彿那個古老的經典敘事一般,她的妻子可以藏身這旅館中不同的每一個故事之房間,躲避死亡如那每夜不得不再編造的故事。或者另一輪的經典敘事:在這座迷宮般的旅管理,琥珀般凝固他對亡妻的思念與記憶裡的樣態。又或者是類似另一代的經典敘事:置放那些從此空懸,種種對亡妻的慾望。一個房間一種敘事情境,一個故事裡還有夢境,夢境裡能有回憶,過客各有身世,建築成這座拉距在違建或者卡夫卡城堡,與「凝固音樂般」章節篇目組織成全書的美學習慣裡,與附會於從少年漫畫到個人城市史,從嚕嚕米到都會色情故事,未曾說全文的前情提要隱藏西夏史。
駱以軍在書中還是放進了一個「我」,但終於能讓讀者拉開了與創作者肉身的距離,這個「我」還是有著旁觀主角的力量,也讓圖尼克說出了這所有種種的起源與答案,至少是最為坦白動情的版本:「像我們這種人,長期在漂流之地變貌、變形、變臉,吞食別人的夢境長成自己記憶的部份身體,又因為借居處所的人們或因腺體過於發達,或因歷史的不幸總印痕了被辜負與背棄,他們總要求我們『要去愛』。……我們變成狂愛之人,亂愛之人,我們滿臉愛欲,堅貞誓諾之愛、懺情之愛、純潔之愛……」
從此,無論是脫漢入胡的遷移身世(比如《月球姓氏》)、「我們這一代」,即使是最狂野的想像力,如何被屬於我們的敘事風景所包含限制(比如《降生十二星座》)、夢境與記憶的分野與慾望在之中的痕跡與如迷宮的架橋(比如《妻夢狗》)、透過敘事的力量介入自身記憶與慾望,如科幻改造但終究末世,最後得真誠承擔那些毀棄,攤在「人我的不可能」之前,旁觀的敘事者還是最無可能無辜,把浪漫也頹禿畸形(比如從《第三個舞者》到《遣悲懷》),這種種種種,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但又得明白對那「一沙一世界」不忍離棄噤聲的天真美德。
而說出來的,總是從故事開始,總是只在故事裡結束,但至少,最日常沈重的驚懼與荒誕,譬如意義與情感,不再聞風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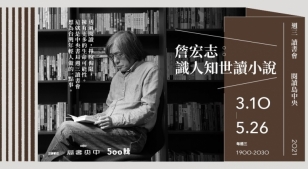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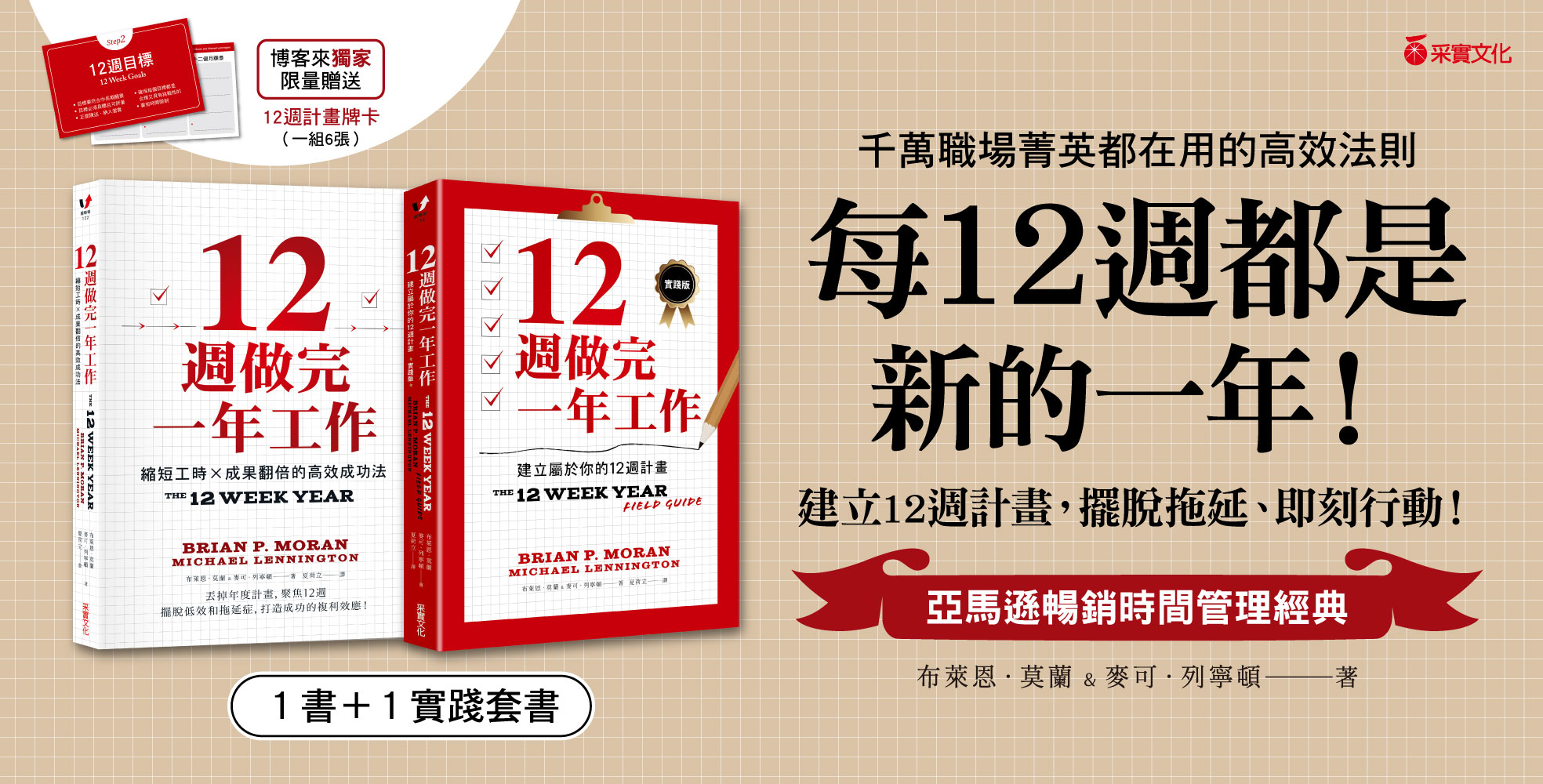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