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達利
剛翻開《人子》第一篇〈汪洋〉的時候,你可能會讀得很不習慣。《人子》的作者是以《未央歌》成名的鹿橋,他帶著一點民初氣息的文字使用方式,或許會讓人覺得有點隔閡,尤其〈汪洋〉一篇在講什麼畢業出航的,拜託?別說是現今的畢業生了,就算是十年前的畢業生,同鹿橋筆下畢業生的思考方式,也已經相差很多了哩。
但待你讀到第二篇〈幽谷〉,這樣的不慣,就會開始淡化、轉換,變成一種極適切的說書方式。
〈幽谷〉講述一個倦遊旅人,返家途中在無人幽谷歇息,在天色將明之前,聽見分派顏色的使者將各式顏色分配給即將開花的蓓蕾們,其中有一朵小蓓蕾,得到了可以綻開任何一種顏色花朵的殊榮。花朵們一面七嘴八舌地提供意見、分享經驗,一面認為要讓它靜靜地思考,因為天光一現,就得開花了。
這朵擁有完全自主權的花蕾,最後選擇了什麼顏色?或者,它將做出什麼出乎意料的選擇?又或者,我們雖然覺得擁有選擇權是種幸福,但事實上是種太沉重的責任?
在〈幽谷〉之後的故事,篇篇都是如此精采、耐讀、發人深省但不教條的寓言故事:〈宮堡〉中矗立在夕陽中光輝得如同天堂的宮堡、〈皮相〉中發現自己的精魂可以自由進出外在皮囊的老法師、〈獸言〉當中睿智的老猩猩、〈人子〉裡頭跟隨老師走遍全國學習如何分辨善惡的小王子、〈忘情〉裡太重感情以致於忘情的精靈、〈明還〉當中與萬物共生共存的小小孩... 每個故事用鹿橋的文字敘述起來,都有種從容、恬適的味道,所有喜怒哀愁都被一種更大的和諧包容,讀進去了,所有的滋味又會重新在腦子裡翻轉出來。
鹿橋在〈前言〉裡說,這些故事「只要喜歡聽就好,不一定要都懂,不但是聽的人不必都懂,講的人也不必都懂...這懂不懂的話是指故事裡的意思,不是指所用的文字。」或許你會覺得奇怪:怎麼會連說的人,都不一定懂故事在講什麼呢?但達利以為,這正是寓言故事吸引人的地方──故事經過敘述者傳達出來,但真正的意義,需要的不是一個「這個故事在告訴我們什麼什麼」的提醒,而是聆聽者的思索、消化,以及轉譯,才會獲得專屬於自己的感動。
終於在你讀完倒數第二篇〈渾沌〉時,會訝異地發現,前頭所有的故事,以一種完全不同的面貌重新組合,它們變成了另一篇寓言、傳達了另一個意涵、表現了另一種生命的姿態;再回想第一篇〈汪洋〉,你才會驚覺,原來那則像是畢業感言的文章,其實是孕育這所有故事的原初海洋。最後,再讀那篇有趣、同鄉野奇譚一樣的〈不成人子〉,正好讓你心滿意足地把書閤上。
其實在臺灣商務印書館重新整理、出版鹿橋全集之前,達利已經讀過許多次舊版的《人子》了。這些沒有單一解答的寓言故事,在生命的每個階段裡閱讀,都會透出不同的感觸;故事當然是一樣的,但因為讀的人心境不同,就會在字裡行間讀出不同的意義。
或許你曾經以為,「寓言」只是一些給小朋友看的、似乎一目瞭然的故事。
但閱讀《人子》,你將會發現,真正的寓言故事,其實應當就是如此──
它們不僅好讀、耐讀,也將是讀者生命的歷鍊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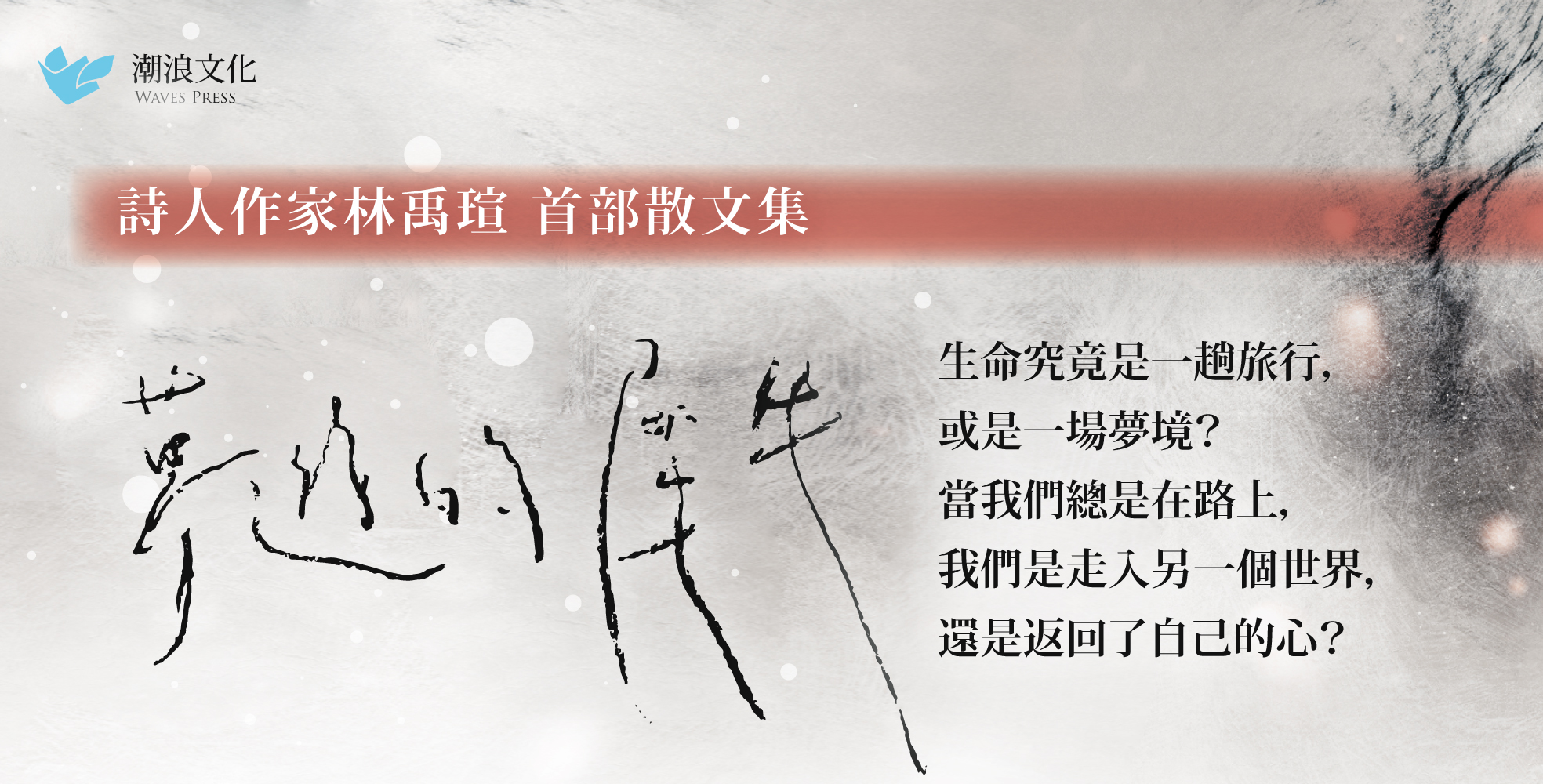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