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發現1950年代的《聯合報》(在1951年創立,在1953年正式改組為今日的《聯合報》)很有意思。它採用斥責同性戀的口吻,向讀者兜售同性戀奇觀。這些舊報紙證明,在白先勇投入寫作之前,有些本地讀者(白先勇可能包括在內)早就從報紙獲得對於同性戀的負面印象。恐怕正是因為1950年代報刊再現的同性戀「不值得同情」,白先勇在1960年代開始發表的作品才會再三呼籲讀者「同情」同性戀。
各界早就公認白先勇延續中國文學傳統、繼承歐美現代主義;但耐人尋味的是, 很少人指認白先勇是否也受惠於台灣歷年來的印刷品。難道1960年代的作家們沒有看過1950年代的《聯合報》嗎?
1959年的《聯合報》出現「讀者投書」,感嘆「新公園」成為「同性戀」(這是投書用詞)的「男娼館」(這也是投書用詞):「新公園已經成了半公開的男娼館,同性愛的泛濫地」、「這裡有成群結黨的可憐少年經常有計劃的勾引外籍有那種變態嗜好的男士」、「請市府趕快為新公園添置路燈,派警員巡邏,根除同性戀,男娼的禍害」。
這裡的「成群結黨的可憐少年」讓人聯想《孽子》的同性戀男孩們。這裡的「外籍變態」有可能是指美國人;1959年正值越戰(1955-1975)。
1957年,報紙花上半年以上的時光持續報導「黃效先殺人焚屍案」,更為「同性戀」這三字進行密集的負面宣傳。在無數報導中,我只列舉冰山一角的兩個樣本。1975年上半年,〈黃效先殺人動機!弱點盡被控制 終至行兇除根〉一文指出,「黃效先殺人的真正動機究竟在那裡?既非謀財,亦非情殺,而是迫於死者楊士榮同性戀的威脅,楊藉此弱點,控制了他的名譽,他的行動,甚至他終生的幸福,因為他已準備與一位名門閨秀結婚了。」同性之間因為情慾糾紛殺人,不算情殺。「黃效先生性文弱,有女兒態,畏羞,動輒臉紅,認識他的人都不敢相信他會做出這種事來,可見他因陷於楊士榮同性戀的陷阱,在心理上、精神上所受的刺激之深。」
弔詭的是,報導將被害者楊姓男子寫成狡猾的加害者、將加害者黃姓男子寫成無奈的被害者:楊姓男子用同性戀毀滅黃姓男子的人生。報導看似同情黃姓男子,卻忍不住調侃黃姓男子的女氣。
在這篇報導見報一個多月後,《聯合報》另一篇報導〈失足僅一次 身體無變態〉指出,被法醫檢查之後,黃姓男子自稱「我完全正常,我並沒有什麼半陰陽變態」、「我們(按,黃跟死者)只發生一次關係,就只有一次。」從報導可知,當時社會一遇到同性戀就想要檢查當事人的性器官是否「正常」。
再過四個月後,身為「國大代表」的趙班斧投書到《聯合報》,指出「革命先烈黃百韜將軍的兒子黃效先殺人焚屍一案,報載已由最高法院判處死刑」,呼籲總統特赦黃姓男子,「為先烈遺孤留一線生機」。趙班斧並且引述最高法院的判決書,強調「黃效先並沒有卑鄙下流的同性戀行為」。越強調某人跟同性戀無關,當然就越描越黑。在高唱反共愛國的1950年代,為同性戀命案「廢死」竟然也形同一種愛國方式──為革命先烈挽留遺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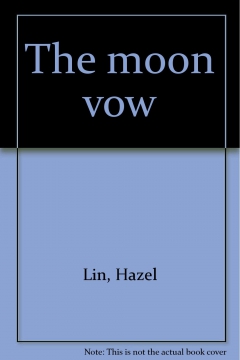 The Moon Vow書影
The Moon Vow書影
除了非文學文本之外,《聯合報》也刊登「揭開同性戀神秘面紗」的文學。從1958年開始,《聯合報》「副刊萬象」連載美國小說《月誓》(The Moon Vow),作者是「中國女作家林涵芝Hezel Lin」,這小說用赤色中共匪幫竊據前的北平做背景,翻譯者署名「南方朔」。知名評論家「南方朔」生於1944年(或云1946年),在1958年的時候年紀頂多14歲。這兩位南方朔恐怕不是同一人。
報紙編輯在連載小說前面登出小啟表示,「女醫生把一個看來沒有病的姑娘,從極嚴重的無形的病態拯救了出來,這女性感情上的病態,雖然書中女主人是一個極年青的中國新嫁娘,事實上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如此病態的新娘子。」此處報紙編輯欲言又止的「無形病態」正是女同性戀──報紙編輯知道女同志秘辛頗有賣相,卻故意賣關子。
在小說內文,女醫生蓮華對女病患說,「…妳對性的問題,有著一種很不正確的看法……妳不需要男人,但妳需要女人!妳不是沒有性慾,而是妳性慾的發洩失了常。…為什麼不讓我介紹一位心理病態專家,很快地把妳醫好?」
小說敘事聲音(但不是蓮華)表示,「關小姐已經顯示出她是一個很不正常的女性。從這一下午她的言行上看來,她很可能是一個迷於同性戀愛的女人。」
關小姐後來跟蓮華承認,她加入了一個號稱「針線會」的同性戀俱樂部。原來「女紅」這麼玄奧。俱樂部主持人是一個富有的單身女子,聘用的女僕全部參加女同性戀活動。「…針線會的內情……是同性戀愛的俱樂部」、「我們大家包括那些女佣人相互關切,志同道合相親相愛。社會上一般人自以為他們的生活是正當的,我們幹的勾常是不法的,所以我們就更團結得緊」、「大家公推我做『槍手』,挑逗(按,招徠新會員)的工作全由我負責。……呶,我把要說的都說了。人生為的是謀求快樂,我們覺得那樣快樂無比,為什麼做不得?犯什麼法?」
蓮華忍不住斥責關小姐,「妳犯的罪過是引誘李梅,背棄親夫,變成一個搞同性戀愛的女人。就憑這一點,妳就吃很大的官司!」
我查過,《月誓》這本美國小說確實存在,作者「中國女作家林涵芝Hezel Lin」也不是虛構──我特別查證,是因為這部小說看起來很呼攏。此書此人早就被美國文壇和學界打入冷宮,幾乎無人再談。《聯合報》連載的這部小說,文學價值可議,娛樂價值卻高。這部小說值得被譯介給台灣讀者嗎?用21世紀的標準來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用1950年代的標準來看,答案卻可能是肯定的,這部小說「寓教於樂」,讓台灣讀者一方面「理解/誤解」同性戀,另一方面又可以「意淫/淫樂」同性戀。
1960年代白先勇等等作家撰寫同志文學,預設的挑戰對象很可能就是大報(如《聯合報》)公然渲染的同性戀「知識/偽裝知識」。
紀大偉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膜》,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酷兒狂歡節》,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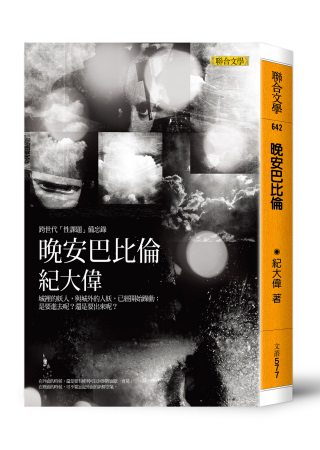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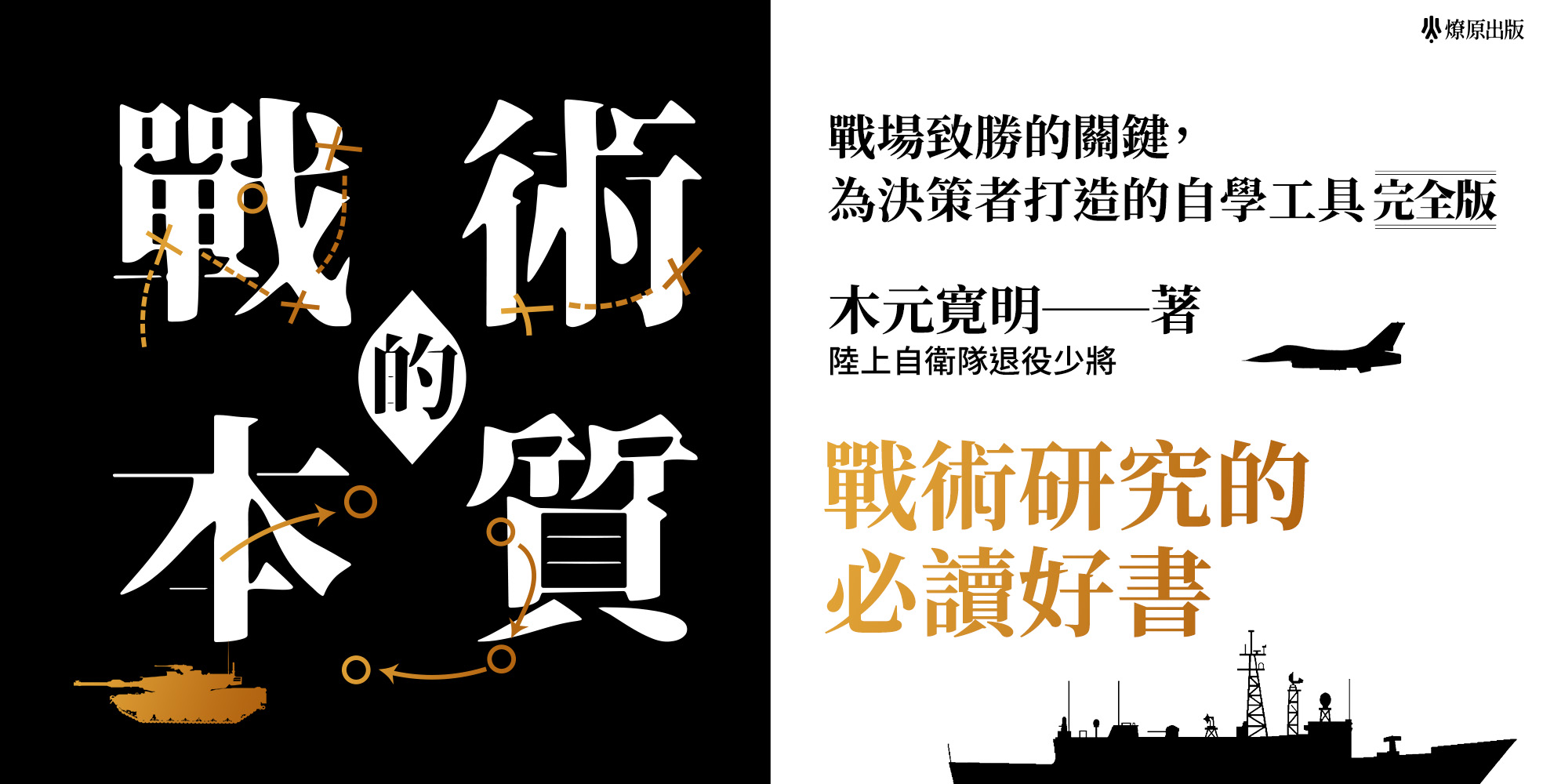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