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時候,某些城鎮已經睡死在過去,人還是醒著,有些公路已經通不到遠方了,然他們卻還在逃著。那些被遺忘在世界盡頭的少年們,如清水佑一,隔代教養、城鄉差距影響已深。在那裡,暮色與霓虹誰也幫不了誰,甚至遺忘了彼此曾有過的青春,如果祐一是惡人,那我們是視而不見的共犯嗎?
有時候,某些城鎮已經睡死在過去,人還是醒著,有些公路已經通不到遠方了,然他們卻還在逃著。那些被遺忘在世界盡頭的少年們,如清水佑一,隔代教養、城鄉差距影響已深。在那裡,暮色與霓虹誰也幫不了誰,甚至遺忘了彼此曾有過的青春,如果祐一是惡人,那我們是視而不見的共犯嗎? 
有時經濟造成的寂寞,是更殘酷的永夜。有些孩子還沒有見到日頭上山,夜幕就已經西沉了。「我的生之光呢?」觀影中,彷彿一直聽到清水祐一心頭這樣的回音。
名著《小王子》提醒人們要用心看,因為有些事是眼睛看不到的。那如果真用「心」來觀看電影《惡人》,主要幾個角色的寂寞又是什麼樣子的呢?那彷彿恍然進入了陰陽師安倍晴明的庭園啊。被祐一殺害的女生佳乃,她的寂寞像狂風驟雨中一灘爛泥,混著風貪戀著遠處一點不關己的花香,於是更嘟噥著水泡流竄著眾多欲望,「我要脫離貧窮,脫離我爸爸的那間美容院……」,那爭先恐後的泡泡聲兀自在寒涼中沸騰著,哪裡都去不了的一灘死水啊,生時就怨著、嘶咬著、低吼著,厭著祐一工人的身分似一路尾隨地癡纏她,正好被棲息在暗處的怨念一把擄去,一身廉價時尚,緊抱著她的LV包包如灰姑娘的入場卷,女孩,或女孩們,妳們要靠男人的車疾馳去哪裡呢?
而那被群眾罵喊成「不是人」的殺人犯清水祐一呢?他似有知覺開始,世界就關了燈,處在一個黑漆漆的密室,他跟女友光代說:「我的家放眼看去就是無垠的海,彷彿哪裡都去不了。」從小被母親遺棄,交給外婆隔代教養的他,像個棲居於黑闇中的野生小獸,面對的是他那都是老人的鎮上鄉親,以及垂死的外公,他是那裡唯一的年青壯丁,他總載著鄰居進出醫院,他的工頭說:「祐一的人生就是工作、吃飯跟去醫院。」
沒有任何暮色比人生的暮色能壓得更深更沉了,更何況是人們集體的暮色。那個村鎮整個沉默著,屏息以待進入深夜,祐一年輕的光進不去也穿不透,他活在一個失語的世界(語言在老化的世界裡會逐漸散失),於是打開手機找尋那點光源,游標的光像螢火蟲的光一樣,忽遠忽近,似乎觸手可及時,又會飛走,他看著螢幕中援交時半裸的佳乃,像想吃了她一樣,吃那頭的光,一口吃掉與他相同的絕望。他在網路上寫滿對話,對真實人生則無言以對,因為那是夢。
那些寂寞的急救法,像純粹解饞的垃圾食物,吃到都打嗝了,溢滿的氣味仍是膨脹的空虛,四處流竄發脹的餘味不散。
而將企圖追他的佳乃,一腳踹出車內的增尾,是一帥氣的富家子,在電影中始終在空轉著日子,像追逐各種異味的蒼蠅,特愛寄生於人之腐敗中,卻又嘲笑著別人的腐蝕,他一生當一天過,不斷換女友、不斷開名車飆馳,尋找更腐爛的可能,包括他的酒友,從那些捧場性的笑聲中,他享受著「高人一等」,但沒有那台子,他去哪裡都人走茶涼,他活如戲台上的鬼,附身似地享受不屬於他的掌聲,不斷地巡迴演出,嘲笑著所有可能無用的努力,那風都吹不動的恐懼,宛如地縛靈的存在。

這電影如生靈版的百鬼夜行,似有安倍晴明在簷廊看著這一切生態,寂寞之惡是條蛇,四處竄進靈魂的蔭涼處坐大,成為吸納眾生的另一方界。女主角光代也一腳踏入他們催眠似的來回隊伍中,她說自己的人生沒有離開那條國道,無論是求學,還是上班的地方都在同一條國道上。
光代著迷於大海與燈塔,日子卻如同被蛛網黏住的螢蟲一樣,總在服務的西裝店看著交流道,那窗外的陰雨、客人試裝時露出的灰指甲,內心的蜘蛛時時逼近中,那骨柴般的身軀抖顫著,蛛網上總有濕霉之氣在犯擾,因此她第一次因網交見到祐一時,他身後的夜幕低沉,吸引了她衝進那黑夜裡,趁機想振翅出她所有的生命之光。

如果以心的視覺觀看寂寞,幾分像生態寫生,它穴居在每個人心裡,有時在無形中早蠶食了宿主,但他們仍呼吸著,為了逃避,進入遊魂似的狀態,我們像在看他們的夢,但又如此真實,因為《惡人》並不是在講哪一個惡人,而是在講一片惡土,如果寂寞加上貧窮,會起什麼樣的效應?
我們或許不是活在最貧窮的年代,但我們的精神上無時無刻不感到貧窮的威脅,故事中的人仍有下一餐飯可以吃,但未來的貧窮追著電影中所有的老少們,在這沒有工業可發展的廢棄小城,無法再維持旺盛生產力的老人、無法適任就業的年輕人、早已習以為常的隔代教養現象、年輕人以愛情來當脫離該地的手段,未果者便棄養孩子。21世紀有半數勞力密集的工業被淘汰,不少城鎮被宣告死刑般地流放在國家邊陲地帶,這是當今世界普遍的情況,城鎮暮靄,日如夜寐,美國電影《內布拉斯加》,兒子載著以為自己中獎的老父去大都市兌獎,繞著圓周般的公路,行過父親的家鄉,發現整個鎮與鄉親都老了,比他老爸更老地昏睡了。
早在80年代,大衛林區的《雙峰》,鎮民就如同做一場夢一樣,不會醒來的一群人周而復始,大都市的警探去了,發現人沉沉地睡在現實生活裡,活進那土地的瞌睡裡。清水佑一就是生來便睡進了這沉夢中,巴望著一天醒來時,發現真是個夢。母親在他幼年時,將他遺棄在燈塔前,叫他看著那催眠般的光暈,祐一的外婆最大的快樂是參加所謂鬧哄哄的養生座談,其實是騙人的賣藥集團。佳乃厭棄佑一,因為她仿若看到那一無所有的自己,於是怕自己怕到要誣賴祐一綁架強暴她,使得祐一失手殺死了她。在那裡人人渴望自己的夢不要醒來,唯獨祐一想從這永夜裡掙脫,於是他在逃亡的最後,看到遠方的日出時,彷彿第一次見到太陽一般掉淚。

在電影末尾,佳乃的父親經營的理容院,是街弄盡頭唯一閃著亮燈之處,那景色在很多電影裡可以看到,如美國恐怖電影總愛在公路上安排一個孤伶伶的商店,等著年輕人過了這一站後,就要被莫名地獵殺,日本電影《那夜的武士》、韓國的《聖殤》那裡都有即將被廢棄的工廠小鎮,那裡面的年輕人都沒老,只是在工業化時代之後,鼓勵集體努力的氣氛消失了,個人時代來臨,在沒有被栽培的環境下,他們跟自己的鎮一樣被遺忘,如祐一被擱置在遙遠的盡頭。
祐一其實是一場長達一生的惡夢,但並不是惡人。金錢遊戲被大幅改寫,大批人還被錯置在過去,我們都趕忙開往人們說的新公路上,拿著標示不清楚的地圖,通往新經濟的烏托邦,迎著螢之光,每一趟都是近在眼前的長征,而另一些道路,人跡罕至,無人聞問,那是通往每一個「清水祐一」的家鄉。
《惡人》改編自日本作家吉田修一所作的長篇小說。此片以殺人案為切入點、聚焦底層人群面臨的困窘處境,吉田將其視為自己的代表作。該小說單行本甫一出版就迅速賣出十萬多冊,如今累計銷量已過九十萬本,曾摘得每日出版文化獎和大佛次郎獎桂冠,2010年被東寶公司拍成電影版,由李相日執導,深津繪里與妻夫木聰等主演,本片曾獲第34屆日本電影金像獎男女主角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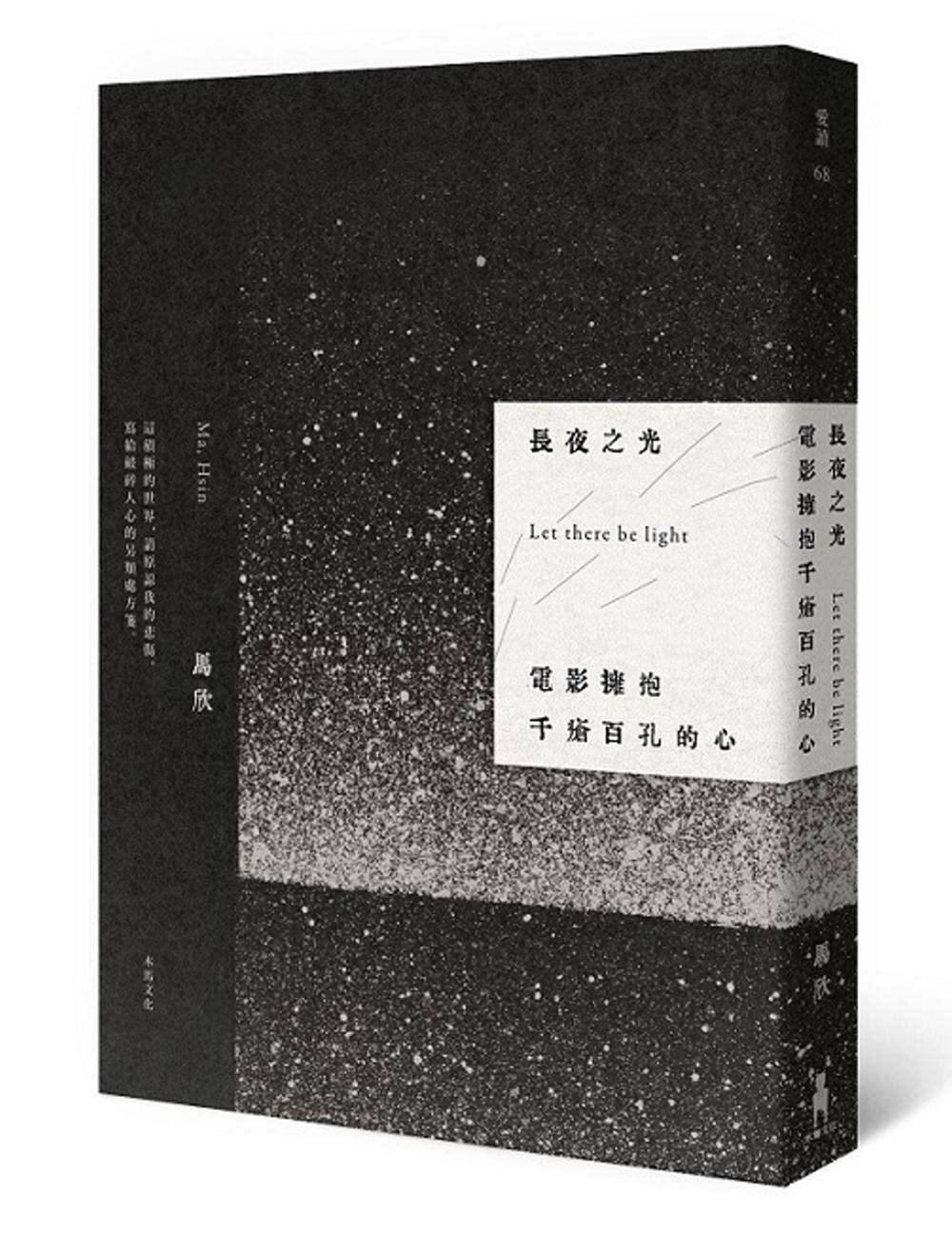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