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台灣文學中,1970年代男同性戀角色遙想美國但通常沒有本錢赴美,就算真的入境美國也只能屈居社會底層;1970年代女同性戀角色追求可以在台灣境內具體實踐的生活,並不像男同性戀那樣妄想外國;1980年代的同性戀角色,不論男女,卻都可能出國(西方國家),而且積極追求西方定義的個人成就──這些同性戀角色終於可以出國決勝負。
他們在台灣的時候可能是魯蛇,但是出國之後就搶著當溫拿。
我在這裡討論的作品中,顧肇森的〈張偉〉(收錄在短篇小說集《貓臉的歲月》)篇幅特別短,卻也特別膾炙人口。在〈另類經典:台灣同志文學(小說)史論〉(2005,收錄在《台灣同志小說選》)中,朱偉誠指出,〈張偉〉這篇小說「在台灣同志圈口耳相傳」,讓同性戀讀者覺得感同身受,堪稱「經典」(20-21)。我從善如流,先談顧肇森。
為什麼〈張偉〉享有口碑?在〈張偉〉中,「像張偉這樣表現傑出的年輕人」(朱偉誠語)從小到大都是台灣教育體制中的佼佼者,各方面都讓父母師長滿意,唯一的缺憾是沒有女朋友。他在高中時代,就在圖書館看過《變態心理學》,猜測自己就是書中某種人。他不負眾望赴美發展,終於交了這輩子第一個男朋友(美國白人),組成「一夫一夫」版本的核心家庭。後來張偉卻發現男友外遇,憤而跟男友分手。
《孽子》諸子離家出走並不光彩;張偉的離家出走卻很體面。他第一次離家出走,是離開父母的家(一個爸爸、一個媽媽的現代核心家庭)前往美國;在「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意識形態護佑之下,離家的他不但不會跟父母發生衝突,反而讓父母有面子。他第二次離家出走,是離開他跟男友的家(男配男的現代核心家庭),這一回他的離家原因仍舊正氣凜然,因為他要處罰膽敢外遇的男友。從張偉享有的道德優越感高度觀之,他離開父母的家絕對不是不孝,他離開伴侶也絕對不是他自己的錯。他離家出走兩次,但是這兩次他都做好人,不必做壞人。
我認為,〈張偉〉能夠廣泛打動讀者,可能因為它明顯襲用本地讀者愛好的張愛玲式文字腔調,可能因為它鋪陳唯美的同性戀者性啟蒙和愛啟蒙畫面,更可能因為它釋出一種特別討好主流社會的訊息:同性戀者除了性偏好跟一般人不同,其他各方面都跟一般人一模一樣,甚至比一般人還要傑出。張偉釋放出來的訊息,很容易轉化成為一種政治訴求:社會應該接納同性戀者,因為同性戀者跟一般人一模一樣,甚至比一般人更優秀、享有更強的消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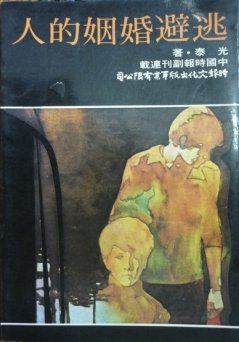
〈張偉〉不是最早提出同志政治訴求的作品。《孽子》,以及比《孽子》還早出版的光泰小說《逃避婚姻的人》,都比〈張偉〉還早問世,而且都提出明確主張(主張內容:社會應該如何看待同性戀者)。〈張偉〉看起來只有個人層次的感嘆(只關心自己過得好不好),沒有社群層次的主張(不關心同性戀者共同命運),但是卻比《孽子》和《逃避婚姻的人》更容易打動主流讀者:畢竟資本主義盛行的社會往往慫恿讀者崇拜張偉這種個人主義的贏家。
身為優秀同性戀者的張偉正好投合在不同國家(包含台灣)、不同時代都曾經出現的右派同志運動。右派運動者認為,為了爭取主流社會接受,同性戀應該主打「形象牌」,展現跟一般人一樣正常,甚至比一般人更優秀的光鮮形象(像張偉一樣),同時絕不能讓主流社會看到某些同性戀者的「負面形象」(例如《孽子》諸多角色的不男不女、性交易等等)。但是同志運動內部是有多元立場的,許多運動者並不贊同右派立場,並不願意獨尊社經優越的同性戀模範生,反而更加重視持續處於社經弱勢的眾多同志。
顧肇森後來發表的短篇小說〈太陽的陰影〉、〈去年的月亮〉跟〈張偉〉相似,都將同性戀者描寫成美國社會的成功人士。但是〈太陽的陰影〉、〈去年的月亮〉更上一層樓,提出明確的政治主張:只要同性戀達致成功,就應該被社會尊敬。〈太陽的陰影〉的敘事者「我」,復國,旁觀久未謀面的親哥哥,建國。因為建國在美國參加保釣運動而被列入台灣當局的黑名單,長期不得回台灣,跟家人(包含生父以及弟弟「我」)分隔多年。「我」突然被建國邀去鳳凰城作客,才知道建國變成「成功地產商」(70)、是同性戀者、跟黑人男友麥可同居,而且生命垂危。麥可跟「我」透露,建國得了「後天免疫失調症群」(AIDS)。「我」終於了解,哥哥一直不跟台灣家人聯絡,主要因為父親不接受哥哥的同性戀身分,而不盡然因為哥哥參加過保釣。
麥可跟「我」展開辯論。台灣文學難得出現這樣一個黑人角色,可惜他的言行像是腹語術操作的傀儡。這段兩人對話是「恐同」(homophobia,恐懼同性戀者的心態)和「反恐同」的對決,讀起來像是政令宣導的課文。麥可看破「我」的三種歧視:種族歧視(歧視黑人)、同性戀歧視、愛滋歧視,並逐一反駁。這三種歧視的確值得合併解析。但是這篇小說可議,因為它祭出一個主打優越感的勸說者:黑人有資格講道理,因為他本人是「成功的地產商」(一起炒房地產的合夥人就是哥哥建國)、大學的教授(70)。彷彿社會弱勢者(例如黑人、同性戀者)只要成為成功人士,就有資格殲滅主流社會的歧視;按照這個邏輯,如果社會弱勢者沒有出人頭地,是否就是失去了對抗歧視的正當性?
建國病逝之後,一方面「我」突然濫情懷念兄弟兩人的童年時光,另一方面麥可淡定致電給「我」──原來建國留了遺產(炒房地產賺來的錢?)給復國。「我」的濫情落於俗套,麥可的淡定才耐人尋味:這個同志版本核心家庭留遺產給弟弟,也就是將弟弟視為這個核心家庭的一份子、視為繼承人之一。
〈去年的月亮〉的主人翁「我」是女同性戀者,不過這篇小說並沒有採用「女同性戀」一詞。小說主人翁「我」是比美國男性同事更加成功的亞裔女性建築師,非比尋常。她在L城(我推測是洛杉磯)出差住旅館的時候突然被李太太找上門來──在七年前,李太太本來是「我」的同性伴侶。七年前,李太太離開「我」,選擇嫁給社會地位不高的美國白人,後來夫妻陷入貧窮。
〈太陽的陰影〉中,同性戀者藉著強調自己的成功來擊退「我」的歧視;〈去年的月亮〉打造相反的局勢,身為人妻者藉著展示她平庸的婚姻生活來爭取「我」的赦免(畢竟她在七年前離開「我」而選擇男人)。不管同性戀角色占上風還是占下風,兩篇小說都祭出同樣的對比:勇敢的同性戀強者(追求不同於社會主流的同性戀生活,以及高人一等的成功,都是美國社會尊崇的勇敢行為)vs.需要被異性戀主流體制保護的弱者。兩篇故事的同性戀者甚至都有意無意用金錢降服異性戀者──〈太陽的陰影〉的哥哥給弟弟遺產(似乎是要用錢脈證明血脈),〈去年的月亮〉的「我」想要掏錢救濟李太太(似乎要證明同性戀女強人比異性戀丈夫厲害)。〈去年的月亮〉也是離家出走的故事:只有弱者(李太太)才會選擇(異性戀)家庭;強者(女同性戀建築師)卻不需要家,樂於單身。
在〈張偉〉、〈去年的月亮〉等篇小說問世之前,蕭颯就發表短篇小說〈迷愛〉(收錄於短篇小說集《死了一個國中女生之後》)。顧肇森小說中的女、男同性戀者到美國爭取成功,但是〈迷愛〉中的女同性戀者到美國追求毀滅。
跟〈去年的月亮〉一樣,〈迷愛〉並沒有使用「女同性戀」之類的詞彙,但是明確說出故事中「三個女人鬧戀愛」。小說角色分成兩邊,其中一邊包括敘事者「我」, 一個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婦,另一邊就是「我」側面得知的三個女人逸事:譚瑩, 從小男性化打扮,曾因為女友芝明追隨新加坡男子而自殺,後來被家人送美國讀書;芝明,周旋在譚瑩和新加坡的男友之間,後來轉赴羅馬修道院修行;莊太太, 有夫之婦,跟芝明爭奪譚瑩。這三人在美國發生情殺,至少有兩人殞命。發表在1980年代初的〈迷愛〉跟1970年代描述女同性戀的作品大不相同,因為〈迷愛〉的諸多女性角色竟然有本錢談跨國戀愛(跨越亞歐美三洲),但是1970年代作品的女人很少有出國機會。〈迷愛〉反而貼近1970年代描寫男同性戀的作品:同樣將美國視為台灣同性戀者嚮往的庇護地。
連旁觀三女糾葛的敘事者和敘事者之母都很好事地在旁進行推理:「我」認為,「起碼在國外,她(譚瑩)容易遇著真正懂得她的人」(從上下文可以推知,「真正懂得她的人」應該是指「能夠接受同性戀的人」或「同性戀者」)(142);「我」的母親則說,「只有美國那種地方,才會出這種怪事」(怪事,是指三個女人的情殺)(143)。
〈迷愛〉也是出國決勝負的故事。三個戀愛的女人至少有兩個離開了家,然後在美國窄路相逢。這三名女子看似輸家,因為她們看起來並沒有在西方取得事業成功(小說沒有提及她們有無工作、收入),也因為她們身陷情殺。但在小說結尾, 敘事者「我」卻感嘆自己跟三名女子的對比:身為人妻人母的「我」已經對愛情冷感,但三名女子展現「迴腸盪氣,生死相許的愛情」,讓「我」「慚愧、疑惑」(143)。顧肇森筆下的同性戀者值得肯定,是因為事業成功;〈迷愛〉中的三名女子讓已婚婦女慚愧,是因為愛情壯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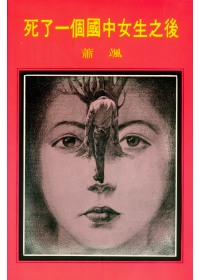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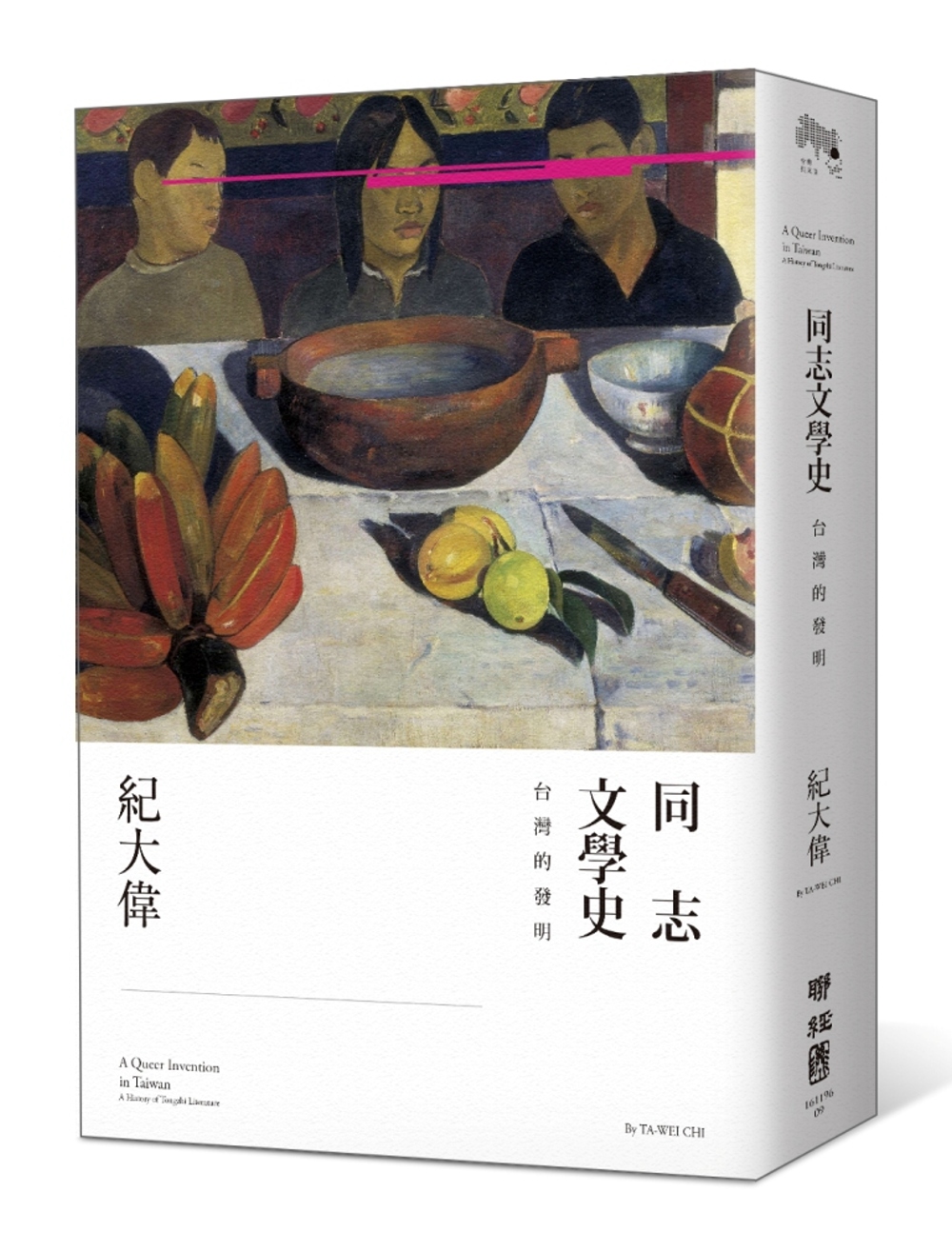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