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aron Hayes〈In The Near Future〉,2009(圖片來自此)
Sharon Hayes〈In The Near Future〉,2009(圖片來自此)
我在一本免費發送的藝術雜誌上第一次看見了Sharon Hayes,她捲髮大鼻(附帶一提,是我喜歡的類型)、手持一副白底黑字近乎簡陋的標語:「I AM A MAN」,兩名警察正上前攀談。因著語言的歧義以及我幾不失準的gay-dar,我對這標語的直覺翻譯是「我是男人」;另一張照片裡她憂鬱沉默地站在百老匯街口,胸口掛上「NOTHING WILL BE AS BEFORE(一切不再復返)」的海報,我完全忽視內文對她的訪談與介紹,只覺得這兩張照片使我感覺有力量,便毫不猶豫地把它們從雜誌上剪下,然後貼在書桌前的牆上。和她一道的還有兩張虎斑貓拍立得、和一捲佔屋派對之夜的底片放樣。
 從免費藝術雜誌上剪下的Sharon Hayes(圖/羅浥薇薇)
從免費藝術雜誌上剪下的Sharon Hayes(圖/羅浥薇薇)
那組作品名為〈 In The Near Future(在不久的將來)〉,從2003年到2008年,Sharon Hayes在六個不同城市的特選地點進行這場行為藝術表演,她選定的地點都是曾經歷大型公眾示威事件之處,但她所標舉的口號卻截取自完全逸離脈絡的、過去的別項群眾運動,甚或憑空捏造。比如「I AM A MAN」其實是1968年發生在美國田納西州的民權運動「曼菲斯清潔工大罷工(Memphis Sanitation Strike)」為抵拒種族與階級歧視而生的標語;曖昧抒情的「NOTHING WILL BE AS BEFORE(一切不再復返)」則純屬虛構。奇妙的是,這些錯置的呼喊與需求天外飛來並不使人感到錯愕,它們幽怨又鏗鏘仿佛未曾離去,從過去到現在,仍在文明的荒謬殘酷與自我重複之中深戀徘徊。
1991年Sharon Hayes來到紐約,那是個仍遭愛滋的死亡陰影籠罩、美人如慧星劃過的時代,即使死去的並不是她的朋友,而是她剛剛發掘的藝術家、革命家、或是她才剛想著想要成為的那個人,但在那五年之中紐約瘋狂攫取住她,迫她見證那絕對政治性、絕對女性主義、絕對queer的創傷場景。因為切實目睹,必須選擇要投身而入亦或袖手旁觀,必須選擇要離得多遠或多近,因為切實選擇過、活下來,她將永遠攜帶著這些創傷場景漫溯在歷史之流。
Sharon Hayes談論九零年代初期的紐約與AIDS如何永遠影響了她的人生與創作
她對於紀年與城市的敏感,使我記憶起1998年帶著無比熱情所奔赴的那個台北。直至今日我才漸漸能夠理解,那時候我所遇到的大多數人,都為我們正要面臨的世界的開口而焦慮且興奮:BBS還正盛,地下讀詩地下聯誼秘密集會都貼了諱莫如深的條子在窄窄的書店走道上徵人,晶晶書庫初登場,新的遠渡重洋而來的論述與名詞、新的遠渡重洋回來的運動份子,永遠不缺的讀書會,永遠不缺的戀愛與背叛。時代就要裂開,已經看見光,身體跟不上,憂鬱如蛇如瘟疫見縫苦纏。
一個季節會有幾次,我到不同的醫院探望朋友,醫院會依情節輕重斟酌搜身的嚴厲程度。台大醫院算是寬鬆的,我們穿越或癡坐或轉圈的精神科病人、抵達為情自殘的社團友人,我因為緊張而佯裝自若地說她實在太傻。「那妳告訴我,我該怎麼辦?」她忽然十分認真地看著我的眼睛:「妳告訴我好不好?」走出舊院區,同行的黑玫瑰學姊(我們叫她黑玫瑰,因為她永遠獨來獨往,而且衣櫥裡只有黑色衣服。)忿忿地說她實在不明白,「愛情」如何在現代社會被打造成如此重要且教人生死相許的概念。
凡此種種,我們作為九零年代末台北的活口,自願或者非自願留下的證詞,都仿佛因為太過珍視而顯得畏首畏尾、躊躇不前。再看Sharon Hayes,恍然或許這正是我們需要形式的原因,有時愛的核心只有足夠遠離它才得以顯現。
那年來到紐約的我擁有一敗塗地的人生與一敗塗地的愛情,來到紐約之後我開始繼續對著一個或幾個愛人寫下無數情信,證實我無能堅守陣地、我對知識體系、語言系統與自己的失望、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如何不可能、暴力如何以愛之名行使無礙。那樣的日子裡有一天,我和其中一個人到MoMA約會,MoMA大廳中央架設了一隻孤單的麥克風,不時有路過的人走上前去、喊出相似頻率尖叫的聲音。我知道人本來有吶喊的欲望,但感覺人的想像力總被欲望侷限,便問身邊的人:為什麼沒有人走過去開始讀一封情書呢?
那時我還沒有去聽Sharon Hayes,卻擁有與她相似的衝動,我想走向大廳中央,把愛人剛剛在書架間塞給我的紙條唸一次給所有人聽,我想讓這裡的人都和我們對彼此的渴望不期而遇,我正是如此帶著暴露性與表演欲。Sharon Hayes說:「Everything Else Has Failed ! Don't You Think It's Time for Love ? (萬事失敗豈不正好相愛)」 她機敏的台詞閃爍星火、既苦且甜,當我們終於得知私密的愛不可能存在,愛與放棄其實深深相連,如此渺小的、處處游擊的時代,為了迎接偉大的失敗,我們無計可施只能放膽相愛吧、相愛。



 Sharon Hayes〈Everything Else Has Failed ! Don't You Think It's Time for Love?〉, 2007(圖片來自
Sharon Hayes〈Everything Else Has Failed ! Don't You Think It's Time for Love?〉, 2007(圖片來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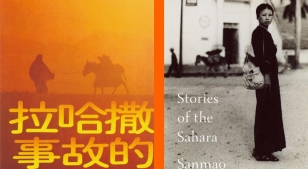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