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許悔之(1966-)的詩〈白蛇說〉(最早發表於1995年《聯合報》副刊,收錄在詩集《當一隻鯨魚渴望海洋》)是熱門的國文課教材,在考卷出現過。這首詩屬於一個「歪讀」白蛇傳的傳統:《霸王別姬》原著小說作者李碧華在小說《青蛇》(1986年香港版,1989年台灣版)把配角青蛇提拔為主角;徐克把李碧華小說改編為電影《青蛇》(1993),呈現兩大巨星張曼玉(青蛇)和王祖賢(白蛇)的情欲纏綿,時至二十一世紀還是觀眾津津樂道的同志電影之一;小劇場導演田啟元(1964-1996)以歪讀孔子神話的戲碼《毛詩》(1988,劇本散見各大圖書館館藏)出名,在1993年推出立基於白蛇傳的戲碼《白水》。〈白蛇說〉是在同志文化生產(電影、小劇場等等)興盛的風氣中寫成。詩的標題「白蛇說」一方面意味「評論白蛇」(一如周敦頤名作〈愛蓮說〉),另一方面更指「白蛇在說話」。這首詩很明確表示「白蛇在說話」:她期待青蛇(青蛇被明確寫成女字旁的「妳」)一起「修行愛和欲」(詩中用字)──她要她進行肉體交纏(像是雙蛇盤繞)、體液交換(像是雙蛇吐涎),而且要她遺棄許仙(按照傳統,許仙本來是蛇妖的欲望對象)。這首詩讓讀者重新評估白蛇,所以詩標題解讀為「評論白蛇」也行。
這首詩的優點就是缺點:它選擇了直白,也就放棄了曖昧。詩中「同性戀身分認同」與「詩語言」合作無間,讓讀者輕易辨識這是同志詩,而且是凸顯愛欲的同志情詩;但也因此,這首詩並不呈現「同性戀身分認同」與「詩語言」之間的潛在矛盾,沒有提供讀者玩味矛盾的機會。

我發現履彊(1953-)寫了同志詩,是因為我早就在OKAPI談過履彊小說大膽寫出軍隊中的男男性關係。但我一直到最近才發現,原來履彊的詩是小說的雙胞胎。履彊詩集《少年軍人的戀情》(2005)內容大約有百分之五十是小說集《少年軍人紀事》的副產品──詩人主動承認,他在1990年代撰寫《少年軍人紀事》各篇小說時,同時將每一篇小說的「小說本事」改寫成詩,並且將詩跟小說在同一個版面發表。詩集中的〈軍營某夜事情〉、〈互相煨暖的靈魂〉不但都可以直接對應《少年軍人紀事》的同名小說,而且都附帶詩人解說(這本詩集的詩大半緊接著詩人題解)。這兩首詩當然是同志詩:詩句把男男性關係寫得很白,詩對應的小說和解說,更再三提醒讀者絕對不能忽視詩中同性戀。
不過這些詩也就沒有留給讀者自主詮釋的空間。作者坦然表示《少年軍人的戀情》和《少年軍人紀事》都是他個人記住青春的備忘錄,也就是說,兩者(都是1990年代產物)跟1990年代盛行的同志身分認同摸索課題並不相干。我承認,有些同志詩就像許多其他詩一樣(例如慶祝國家慶典或是家庭活動的詩),被當作存放記憶的器皿,但是器皿本身未必被當作藝術品琢磨。
裸男特寫是陳克華(1961- )詩中常見風景。他在2004年選擇主動出櫃後(主動出櫃,是為了抗拒被動地「被出軌」),作品更加坦然展示讓人強烈聯想男同性戀。我早就在OKAPI談過陳克華在2006年出版的詩集《善男子》,詩集封面展示詩人自己傲人的胸肌。既然詩人的同性戀身分認同經過當事人再三認證,那麼讀者就可以放心將陳克華的詩作讀做同志詩──這種放心(放心其人其作一定不是冒牌的同性戀)或多或少也讓國內外學者、學生將陳克華詩當作同志詩研究的首選對象。這種放心,固然讓文學研究者和教學者享受方便,但是我認為「沒有信心掌握文本」的讀者可能比「放心掌握讀本而不虞出錯」的讀者更能享受讀詩樂趣。
2012年,台灣目前首屈一指的同志專門出版社「基本書坊」推出《BODY身體詩》,內容是一張張明信片一樣的卡片,卡片正面印了詩人的詩(各自歌頌男人身體的某個部位)或親筆素描,背面是百無禁忌的裸男照片。照片來自「ㄚ莫蝸牛」 和「RIVER TU」,兩人都是2010年代拍攝台灣本土裸男出名、在網路上走紅的「六年級」攝影家,在他們這個時代之前,拍攝本土裸男的本土攝影師並不多(例如杜達雄),而且走紅的場域是印刷品而不是電腦網路。詩集中,詩跟裸男照片的比例是27首:32幀。既然整本詩集是男人細密描摹男人的結晶,那麼讀者可以很放心確定集子裡都是同志詩了,割捨了霧裡看花的麻煩/情趣(但麻煩就是情趣)。比起集子中直接歌頌特定器官的詩,我比較欣賞〈大腿〉,原因之一是這首詩偏偏「表裡不一」(詩的標題是表, 內容是裡,像是泡麵包裝不符合內容物一樣),不讓讀者一眼看穿真相。

《BODY身體詩》內頁。
「男人們紛紛來到了天堂洗澡/那時,我還是兒童」。我猜測這裡的「天堂」應該是澡堂,而「我」不論是男童還是女童都造成驚駭效果(如果這個經常、長期探訪成年男性澡堂的兒童是女生,那麼她也可真不簡單)。兒童將諸多男人的大腿比擬為一群樹木組成的樹林,結果終究(可能在兒童時期,也可能在成年後)「在大腿的森林裡迷失」──原來是因為兒童喜歡「不斷摘採樹梢╱纍纍垂墜的碩大果實……」。「我」在童年(以及成年階段)不同男人大腿之間穿梭,品賞不同男人的生殖器,彷彿沉溺於(沒有酒精的)酒池肉林。這裡情欲是溢出社會規範的(不管兒童是男是女),是跨世代的,而且是童心未泯的。
鄭聿(1980-)第一本詩集《玩具刀》(2012) 看起來跟同志沒有明顯關聯。鯨向海在序文指出:1. 他和鄭聿都是在電腦網路上發表的詩人。鄭聿幾乎只在個人的部落格上低調發表,似乎無心參加網路世界或真實世界的文人社交。這種不顧印刷品的詩人如今看來很平常,但是畢竟是1990年代網路崛起後的新現象。2. 「玩具刀」這三個字是個簡單、低調的矛盾語(oxymoron),玩具和刀是互相矛盾的。例如,我覺得「玩具一般的男人」和「刀一樣的男人」就是性別氣質形成對比的兩種人。刀(或者被玩具化的刀)在詩集裡至少有兩處讓人聯想到性行為:「他在我裡面雕刻/我會痛……在很深的地方/雕刻自己的樣子……問他是不是快完成了」,他在我的「心」裡面,還是在我的「體腔」裡面?兩者都可能。這兩人是一男一女還是一男一男?其實兩者也都可能。而這一句「我的短刃/從他的身體/抽出便是長長/的一生」──他是被凶器插過,還是被凶器一般的性器插過?(性器官在常民語言中經常比擬為凶器。)如果是被真刀所插,結果應該非死即傷;如果是愛戀(尤其是失敗的愛戀),才會長達一生。
鄭聿第二本詩集《玻璃》(2014)書名驚世駭俗──在黑話的世界,男同性戀(或,男同性戀的後庭)的最重要代稱就是「玻璃」(衍生「玻璃圈」、「賣玻璃」等等)。但是這位詩人愛搞曖昧,詩集內外並沒有明說玻璃意象跟同性戀的關係為何。孫梓評在序文指出《玻璃》勝過《玩具刀》之處,在於「降低了敘事,使狀態呈現」,這個說法正得我心。「好的文學就是要說好聽故事」這種嚴重簡化文學口號盛行,許多小說跟情節緊湊的電影看齊,許多詩和散文也被賦予說故事的責任──這種將文學等同於說故事的看法,形同將文學縮小變成小學國語課教材。對啊沒錯,小學生都喜歡聽故事;這個社會把文學讀者都當成小學生。詩本來就可以擺脫說故事的包袱。
〈匕首〉這首詩容易讓人聯想到《玩具刀》內容:「琢磨了一生/把最利的部分/斷在他體內//讓自己鈍」。被琢磨一生的東西,可能是詩中提及的詩藝,也可能是抽象的愛情(愛情跟一生,是形影不離的一組詞),也可能是被具體化成為凶器/性器的愛情。自己由利變鈍(由硬變軟?),是指交換詩藝之後的結果,還是性器抽出的結果?兩者都有可能;或許詩藝形同性器。這兩具人體,是一個人的兩個分身,一男一女,還是一男一男?我猜讀者會選擇最艷情的詮釋。在〈從/失戀到/世界/末日〉這首詩,敘事者說別人都以為他侃侃而談不必斷句,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大部分的句子,都斷在我裡面。」這裡斷掉的東西看起來是「句子」,可是〈匕首〉也早就暗示「詩句」(詩藝)、「愛情」、「凶器/性器」這幾種東西的相似性。〈匕首〉的敘事者斷在別人體內,〈從/失戀到/世界/末日〉的敘事者斷在自己體內──詩人似乎很愛操弄1. 「容易插斷的東西」(包括性器)、2.「容易夾斷東西的體腔」(體腔在這裡包括心房)、3.「有點黏又不太黏的體內與體外」等等意象。
早逝詩人葉青(1979-2011)關切「身心對立」:並不是老生常談的「靈vs.肉」,而是「發乎情的心 vs.止於禮的身」。在葉青的詩世界,心可以動、身體不能摸。她去世之後,兩本詩集《下輩子更加決定》(2011) 、《雨水直接打進眼睛》(2011)才面世。她在BBS網路平台發表詩作,列印出來裝訂成冊,就是簡陋版本的詩集。根據詩集說明,葉青參加過同志運動、探索「身分認同」。然而,雖然她的詩顯然都是哀怨情詩,但是她的詩並沒有標舉身分認同或同志運動。《下輩子更加決定》開卷第一首〈當我們討論憂鬱〉就是「身心對立」的展演:「當我們討論憂鬱/總說那是一種心情/但為什麼沒有身體的憂鬱/渴望一個人卻只能擁有她的背影。」這幾行除了點明被愛的人是女人(那麼愛人的人也是女人嗎?),更揭示憂鬱有兩種,各別對應心、對應身。這首詩比較關切的憂鬱,並不是心的憂鬱,而是身的憂鬱──我推測是(性的)壓抑。
身心對立也在〈值得一再丟棄〉這首詩出現:「我們」之間,有詩一般的愛情,以及愛情一般的詩──這種說法看起來很平常,但這個說法暗示了我們之間只能有語言卻不能有身體。「我們」的身體止於禮:「只有肉體 留在法國電影裡」,只有別人(法國人?還是異性戀者?)能夠享受肉體交融,「讓陽光揉皺白色的床單」。也就是說,陽光跟我們處於對立面。〈你的身體〉這首詩則想要突破身體受到壓制的困境:「很想成為你的身體……用你的雙手環抱你的身體╱讓別人以為那是沉思 或等待的姿勢但/那是我們長長的擁抱」。「我」想像「我你二人」同時融合在「你」的身體之中。在禁止身體觸碰的葉青詩世界,這種身體融合的妄想實在太放縱了。葉青詩中,身體碰觸是禁忌,但禁忌的原因沒有說破。
更多的好男好女,不男不女,等下一回。
作者簡介
上下則文章
-
PREVIOUS ARTICLE
【黃麗如專欄|囧途】台灣的便利是因為太多人過勞? -
NEXT ARTICLE
【哀傷浮游2】新世紀福爾摩斯,我為你傷心(並致小鮮肉)──陳柏青讀〈可愛〉
主題推薦RELATED STORIES
-

跟爸爸訣別、跟媽媽出櫃,李屏瑤如何長成「台北家族裡的違章女生」?
「身分證數字開頭為2,非典型女生樣,過30歲不婚不嫁,其他人都以譴責的目光望向你,這樣的我,感覺像是大家族裡的違章建築,容我以鐵皮加蓋的角度,寫冷暖分明的成長觀察。」作家李屏瑤回望從小到大的成長經歷,書寫家庭、性別、性向帶給她的不同捶打與滋養,彷彿對我們說著:不如世俗期待,又怎樣呢?
6883 1






 上一則
下一則
上一則
下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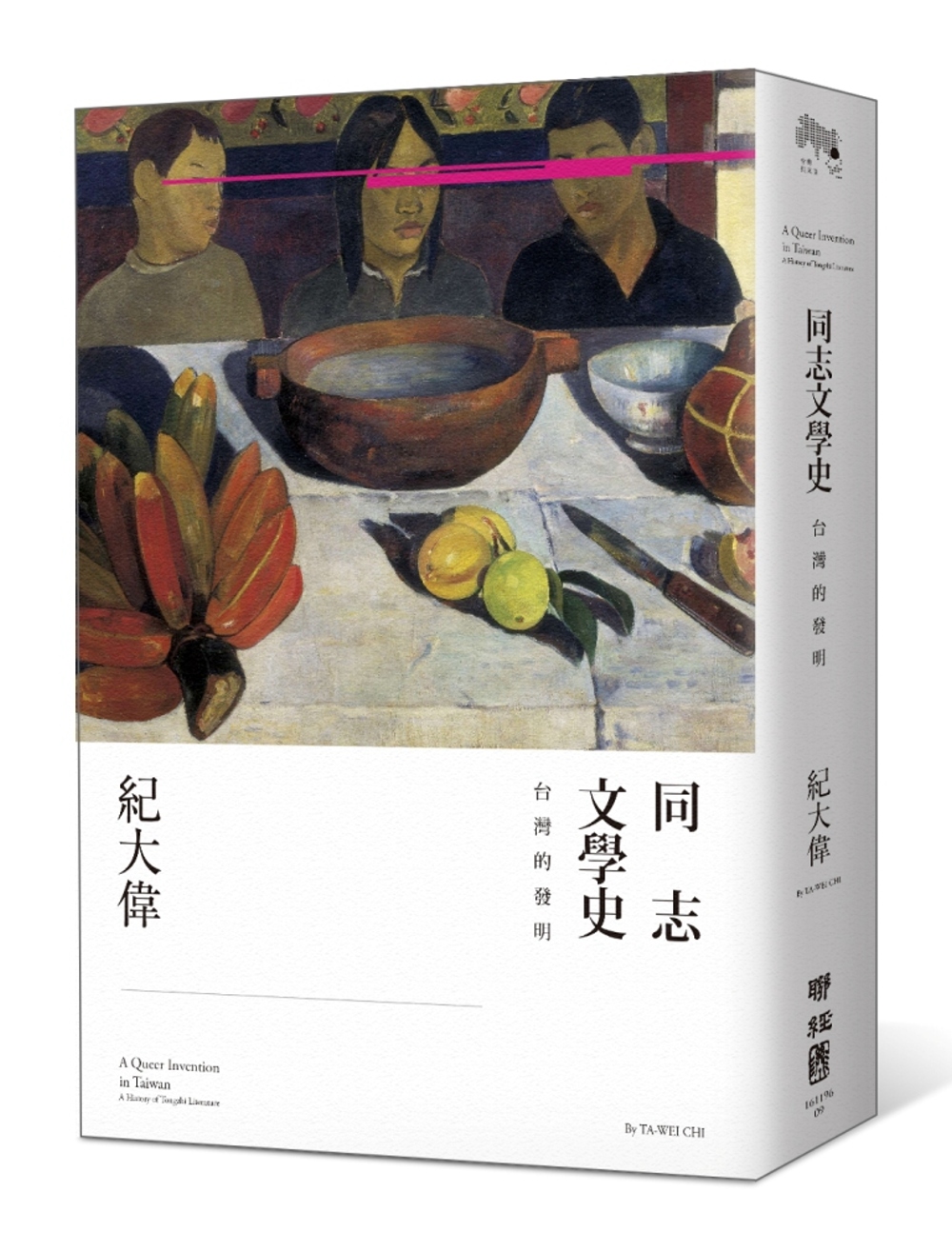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