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秀如(左岸文化總編輯)
民國64年4月16日,早上去了學校,但是那一天沒有上課。老師發給我們每個人黑色臂章,要別在左臂上。然後全校師生列隊,走出開封街校門,在面對中華商場的中華路上等待。等什麼呢?等「民族救星」蔣公的靈柩從我們前面經過。中華路上萬頭鑽動,那時候我還不認識「動員」這兩個字。蔣公還沒到,我們就全體跪下來了,等到靈柩車走了好長一段時間,我們才能站起來。當時我哭得好傷心,從此熟記〈總統蔣公紀念歌〉兩部合唱,到現在一個字都不會唱錯。
我對世界的理解只有我爸訂的《聯合報》、國防部寄給我爸的《青溪通訊》和三家電視台。由於家住台北縣工業區,(越區就讀)放了學就得趕快搭公車回家,從來都不知道原來重慶南路離學校那麼近,那裡有好多書店和報攤,而且是傳播黨外思想的溫床。上了國中升學壓力超大,但我還是天天天藍,該讀的「南海血書」沒少讀,該唱的淨化歌曲沒少唱,該罵的「美麗島暴動」沒少罵,而且認定林宅血案是「家博那個大鬍子幹的」。當時的每一篇論說文都是用「我們一定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解救大陸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作為固定結尾。
高中三年,每年的國慶日都要戴著綠色傘帽排出梅花的綠葉,國慶日前一天也要前往台北體育場擔任四海同心晚會的排字,還有123自由日世界反共聯盟大會也要排字,直到非常非常後來,我才知道世界上還有另外一個酷愛排字的國家叫北韓。忘了說,每天早上升旗典禮完之後都要唱軍歌,每屆高二班都要參加軍歌比賽,如果沒記錯,我們那一屆的指定曲是〈我愛中華〉,我們班的自選曲是〈勇士進行曲〉(男兒立志在沙場,馬革裹屍氣豪壯……),結果是唱〈夜襲〉的班級奪冠(早就說唱〈夜襲〉比較討好不是嗎?「鑽向共匪的心臟,鑽向共匪的心臟……」)。
所以,當我上大學之後第一次聽到二二八事件,我那個藍藍藍天就忽地塌下來了。我第一次在南昌公園聽黨外人士開講,還要高雄來的同學幫忙翻譯。他很驚訝:「妳不是台灣人嗎?怎麼聽不懂台語?」我第一次感到在自己的族群裡是個陌生人,並且對自己非常引以為傲的「字正腔圓」的國語感到厭棄。二二八只是開始,在「馬克斯.韋伯」都會被禁的時代裡,學校社團偷偷舉行的讀書會讓我慢慢地知道了獨裁者不讓我知道的歷史。我們經常笑說,再這樣讀下去就要被抓去唱〈綠島小夜曲〉了,但80年代的我們哪裡知道綠島到底關了什麼政治犯?
如今我們已經用普選的方式產生過三位總統,經歷過兩次政黨輪替了。我在去年太陽花運動期間,晃到青島東路、濟南路,去看那一張張年輕的臉,他們若不是不記得戒嚴時代或根本就是解嚴之後才出生的世代,對他們來說,呼吸自由的空氣是如此地理所當然。他們不像我們這一代以及更早之前的世代,被迫或自願活在獨裁者所編織的謊言中,他們用自己的身體在大埔、文林苑、華光社區抵擋徵收的怪手,他們集結上凱道要求洪仲丘事件真相大白,他們佔領立法院逼迫重審服貿條例,現在他們醞釀要上街頭拒絕課綱微調。課綱有什麼重要性?有,因為我們的最高峰是玉山,不是喜馬拉雅山。
如果沒有上一代留下的痕跡,我們不會知道自己從何而來。獨裁者非常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試圖抹去我們的記憶,給我們新的教科書,然後讓我們覺得自己置身天堂。1975年4月16日,那一天我跪在中華路上為民族救星的殞落而傷心流淚,這個荒謬的情境、這個真實的感情,必須記錄下來,不能忘記。
延伸書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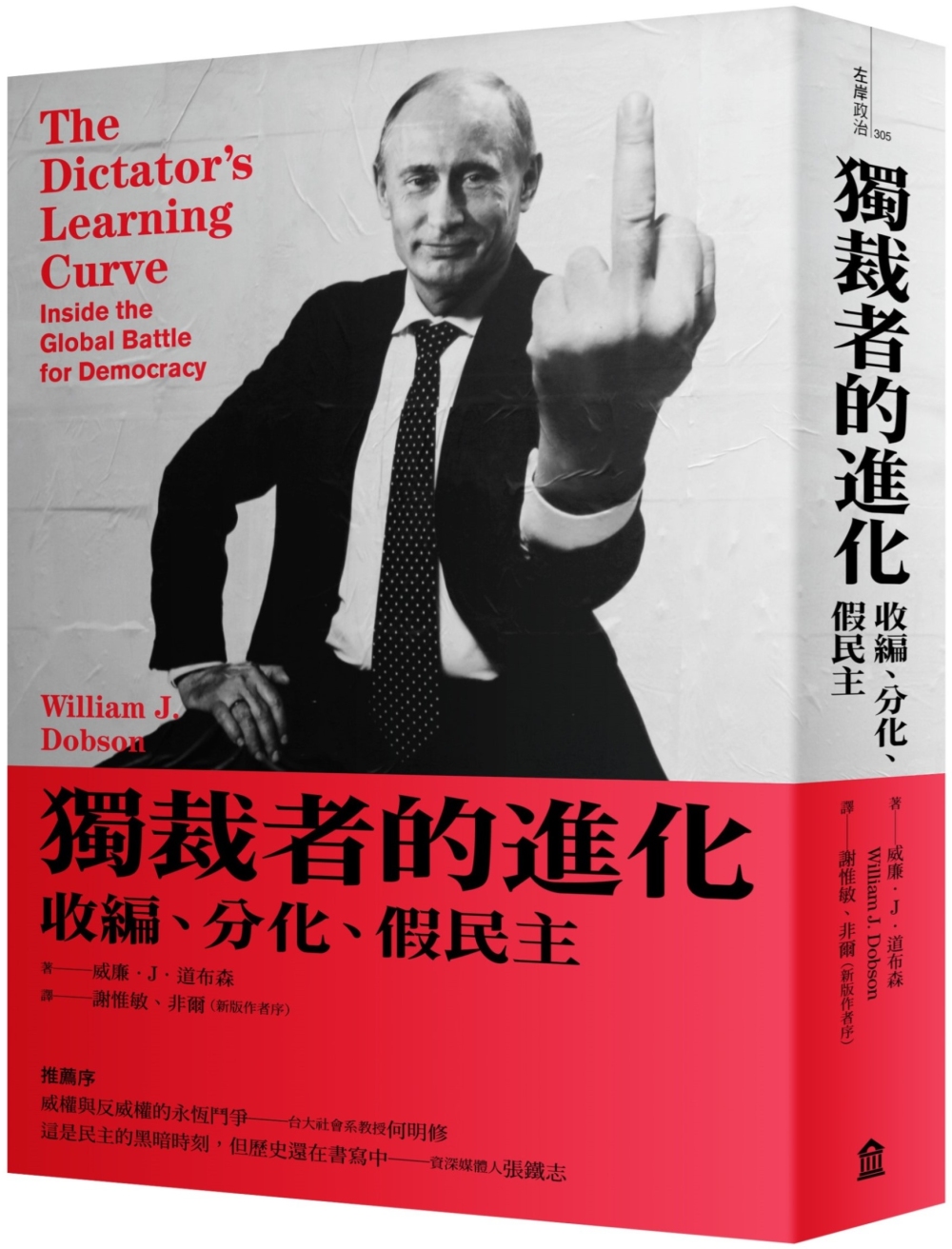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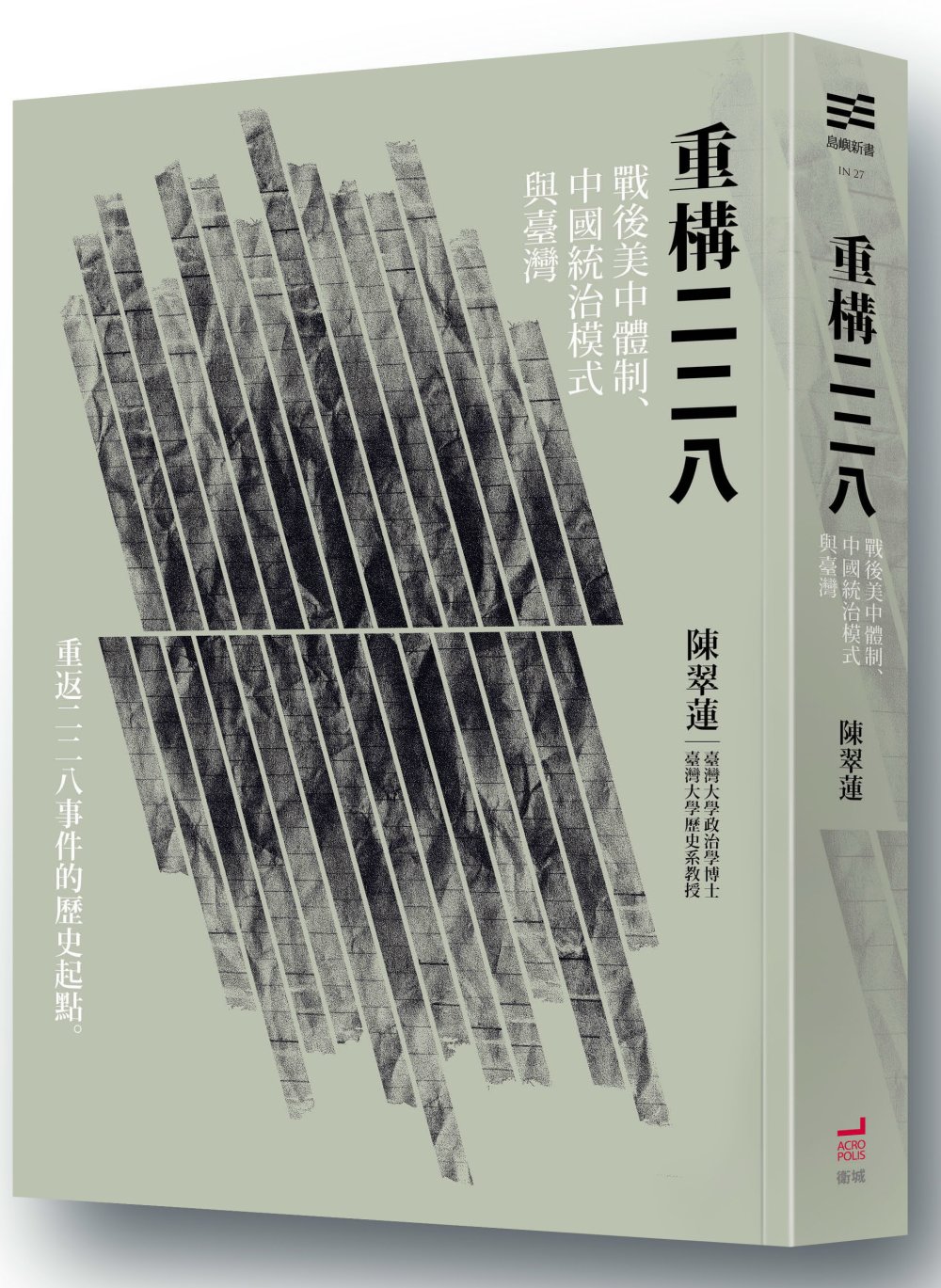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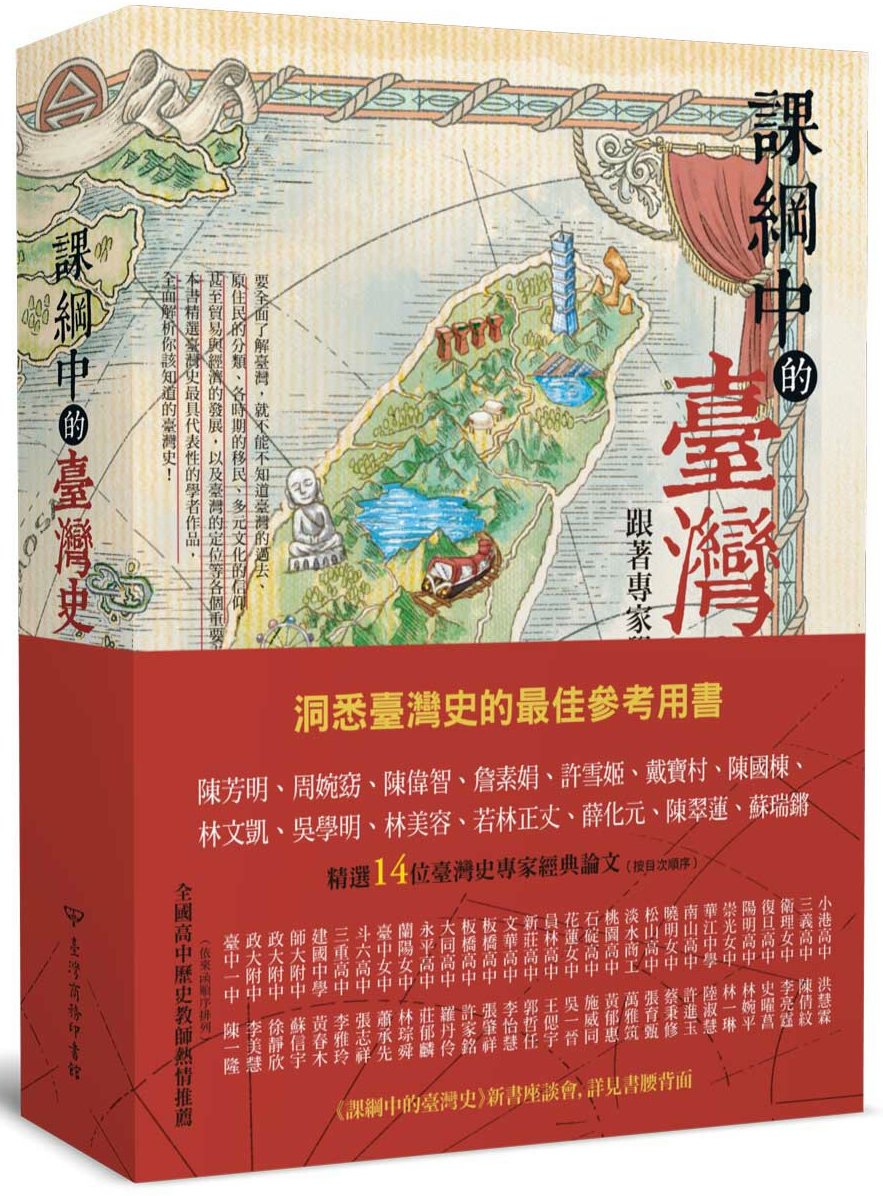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