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演|01〕鄭文堂
台灣電影導演,出生於宜蘭,為台灣著名的獨立電影工作者之一。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畢業,電影曾榮獲「威尼斯影展影評人週最佳影片」「優良劇本」、「最佳台灣電影」及2010年台北電影節「最佳導演」等獎項,並入圍法國南特影展;2010年8月接任宜蘭縣文化局長,並於2013年3月31日離開縣府工作,重回影視圈。
 (攝影/ 汪正翔)
(攝影/ 汪正翔)
那日,王小棣召集了鄭文堂、沈可尚、鄭有傑等六位導演,協商「閱讀時光」經典文學改編計畫的分工,基於尊重大家的意願,王小棣逐一徵詢各導演的偏好,鄭文堂最覬覦的其實是楊逵《送報伕》,卻又不好意思啓齒,輪到他表態時,便從中挑選了張惠菁的作品,因兩人熟識,過去即讀過她的作品,折服於她以女性特有視角,對感官和場域方面纖細又銳利的解讀。幸而最終仍如他所願,由他一人承攬下《送報伕》及《蛾》的改編工作。
就讀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期間,堪稱鄭文堂的閱讀啟蒙期。大學四年,他因沒錢可四處遊蕩揮霍,大多時候皆窩在山上,拍戲、看電影和舞台劇之餘,盡情地讀了四年閒書,「舉凡能拿到的書都拿來念了。」其中尤以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的翻譯小說為大宗,像是舊俄文學代表杜斯妥也夫斯基、高爾基;及至後來,他才發現台灣文學之美,一頭栽進楊逵、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等人的作品。
「台灣文學讓我最驚豔的是李喬的《寒夜》三部曲,因為他,我才開了眼界。我讀了李喬和楊逵之後,在陽明山就不怕冷了。」《寒夜》筆下的人物奔走在台灣最苦的年代,至於楊逵的《送報伕》、《鵝媽媽出嫁》、《模範村》,也盡是描繪一票很苦的台灣人。儘管如此,這些人卻很樂觀,「苦中有一種希望、有一種理想。」從此,鄭文堂在心理層面上不再畏寒,因他自認是一個「背後有力量的人」。「文學真的可以改造人沒錯!」他的表白中難掩熱切。
楊逵的小說《送報伕》原以日文寫就,後經翻譯成中文,語法上有其獨特性,對年少的鄭文堂而言,讀來不易。他從大學起斷斷續續閱讀《送報伕》,及至畢業後,有了一些工作歷練,心境轉換,這才真正讀畢,且讀懂。
 (攝影/ 汪正翔)
(攝影/ 汪正翔)
當年,鄭文堂窮到連坐公車都要斤斤計較,對資本主義頗敏感,所讀的書又多刻劃底層的人,難免特別感同身受。《送報伕》敘述楊君揣著微薄盤纏遠赴日本謀職,冰天雪地裡,好不容易找到差事,高興得簡直要跳起來了。然而,送報第一天,走沒多久鞋便濕透,後又遭資方惡意辭退,一切辛苦頓成烏有。楊君的際遇在鄭文堂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這也是何以在製作經費所剩不多的情況下,他仍堅持飛往北海道拍攝不可的原因。「那個環境對於這個人的考驗,不能用講的,因為是影像故事,他去送報、挨家挨戶敲門推銷報紙的焦慮苦悶,必須藉由實景才能傳達。」
「尤其苦的是,雪正在融化,雪下面都是冰水,因為一個月以來不停地繼續走路,我底足袋底子差不多滿是窟窿,這比赤腳走在冰上還要苦。還沒有走幾步我底腳就凍僵了。」──楊逵,《送報伕》

 (圖/稻田電影工作室)
(圖/稻田電影工作室)
楊逵可說是一位樂觀的理想主義者,一生秉持跨越族群與階級的反抗精神,奮鬥不息。問到是否也承襲了此番精神,鄭文堂說,他家中狀況不好,高中時期,常模仿50年代著名男星詹姆斯狄恩,眉頭糾結,自以為憂鬱,直至進入社會,開始拍戲,才發現自己很樂觀,「不去煩惱明天的事、未來的苦,只想著現在,一直往前衝。」若非如此,他恐怕也不會在如此困頓的拍片環境中一路挺身走來。
鄭文堂坦言,改編《送報伕》實屬不易。首先,要將一長篇小說凝練為20分鐘的影像,道清來龍去脈,讓觀者明白原委,本就不簡單,且不僅要交代情節,又不能失去意境;其次,故事背景為1930年代,如何還原彼時台日雙邊的農村及城市景致,更是一大考驗,此一難度,更甚於漫天大雪中取景。
「她的血進入胃囊,與食物殘渣一起和胃液混合攪散。什麼東在她胃裡騷動著。某種細碎的割裂。
那時她二十五歲,當她忽然意識到,她在胃裡餵養了一隻蛾。從那時起她便不再流失東西了。一切自體循環成一個完美的、封閉的、魔咒解除後的宇宙。」──張惠菁,《蛾》

 (圖/稻田電影工作室)
(圖/稻田電影工作室)
對鄭文堂而言,「拍《送報伕》跟《蛾》是兩個世界。」楊逵筆下的世界雖苦,卻不失溫情;至於張惠菁的短篇小說《蛾》,表面上雖為鮮亮而現代化的世界,但在美學處理上相對比較冷調。在《蛾》中,既有米索和小襄這兩個角色幽微的相互感應,又有米索不同階段的對照,敘事跳躍,構成了改編上的挑戰,「閱讀上有其樂趣,拍很難拍,因為要讓人家懂。如果是長篇很好拍,可以玩很多。米索感知到她自己孕育了一隻蛾的存在,這件事不敢去碰,主要還是拍比較感情面的東西。」
鄭文堂也談及從小說到劇本的改編要點,「小說是閱讀的,劇本是工作用的。最大的眉角是要把閱讀就可以完成的東西,變成可以拿來丈量的尺寸。劇本是工具,有其文學內涵,但要轉換成可工作的影像讀本,把心理的描述轉化成影像。」
《閱讀時光》文學改編戲劇計畫肩負「導讀」的任務,企望以影像為餌,引誘觀眾重讀文學經典,對此,鄭文堂深表贊同,「閱讀風氣應該要被養成,這件事要被重視,剛好《閱讀時光》有此契機。當然做10部不夠,要一直做,才有辦法變成文化上被看到的光環。」
即日起,公視頻道每週五晚間23:30,播出「閱讀時光」文學改編戲劇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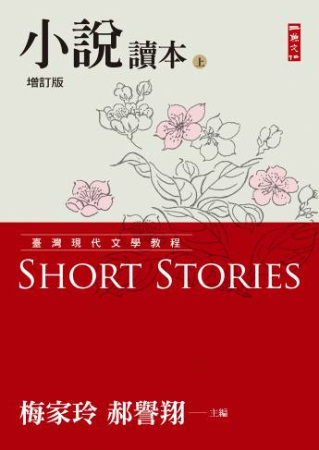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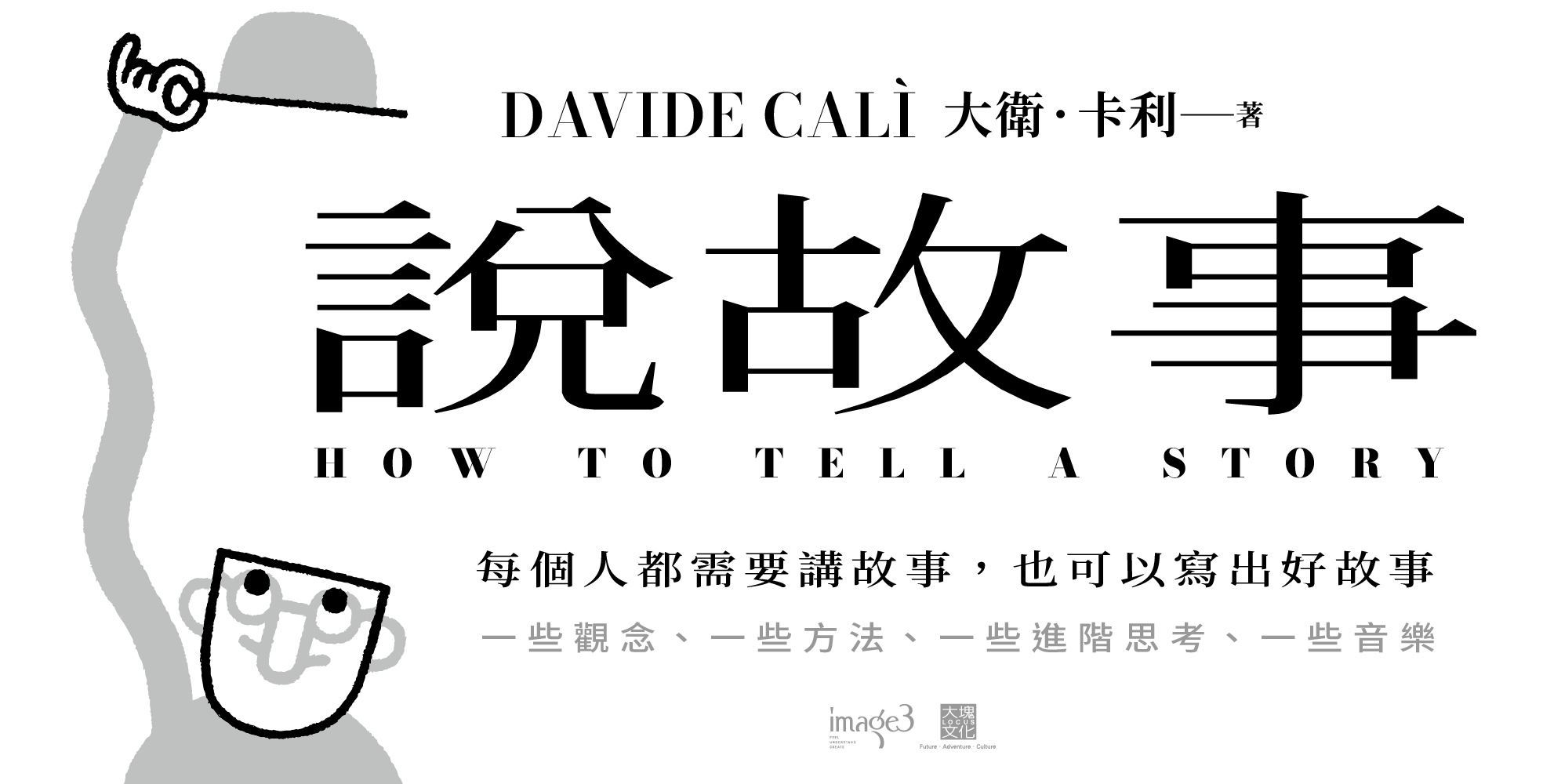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