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汪正翔)
學生對社會現況不滿而出聲抗議,這股純粹的理想主義性讓學運成為社會可貴的改革動力,經歷了今年三月的太陽花學運,九月香港學生占領中環行動仍在持續中,無論這兩場運動如何被批評與質疑,不可否認皆提醒了當代學生關注社會議題、參與公共事務,以及探索民主的重要。
然而1949年的四六學潮沒有帶起民主的反思,只有國民政府大規模逮捕學生的慘烈行動,並開啟了接下來白色恐怖的黑暗時代。
藍博洲在《台北戀人》裡,以多年蒐集來的口述歷史為本,打造出一位在四六事件後出走至中國、50年後才得以返回台灣的老婦人,她一一探尋其餘當事人,尋訪當年失去音訊的戀人。藍博洲不採傳統小說筆法,他讓老婦人自己動筆,向見不到的戀人述說事件爆發後的逃亡生活,主線之外,又有90年代台大與師大學生社團所發起四六事件平反運動為輔線。
「我寫歷史題材,但不願意寫成歷史小說,如果要抽離現代,那寫歷史報導就夠了,但光寫歷史,年輕人不愛讀,我必須站在年輕人的位置去寫歷史,所以要寫一本與現實對話的小說,因為有對話才有衝突,有衝突才有戲。」藍博洲有個念頭,希望能藉由文學開啟統獨對話,1949年時尚無台獨意識,現在台獨意識反成主流,但他指出,「無論台灣人是否同意,台灣未來從來不是台灣人自己決定,也不是中國可以自行決定,這是牽涉到國際戰略的大問題。」他希望年輕人了解歷史、了解現實,了解自己的未來。
有別於一般傳統報導文學以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的報導敘事手法,藍博洲擅長結合口述歷史的書寫形式,以當事者特殊的語言、對白,生動塑造角色的面貌,主角老婦人對著戀人談憶過往,書中出現的每個角色卻又以第一人稱的「我」發言,讓曾向他掏心掏肺說出人生故事的受訪者,適當的剪裁段落、交叉登場,藉著自己的話強而有力還原了歷史。
「其實這是我自己補拙的方式,我知道自己的語言能力不足,沒辦法寫得生動,與其揣寫出假假的對話,不如讓當事人直接說話。缺點是敘事觀點跳動會增加閱讀難度,但讀者就該認真閱讀,一邊讀、一邊思考,而非一頁一頁順順讀完這本書。」藍博洲說。
有趣的是,幾位受訪者讀了《台北戀人》,都說:「這是我的故事啊!」急著對號入座,一位住在上海90多歲的朋友,也是為了躲避國民政府追捕、從台灣逃到中國的學生之一,近年夜裡總難成眠,常常想到初戀女友,那年在逃亡前夕,他與女友在新公園(今228公園)走了三圈,還是沒能牽起對方的手,成了一生的遺憾,「有些人覺得,書裡描述的男女關係太含蓄,但那是我參考一位老太太的回憶錄,她的男友逃亡前,希望能結為一體,因為不知道是否還有明天;但老太太希望等待情勢穩定,結果男友被槍斃了,這件事成了老太太畢生憾事。」每個篇章、每段情節都是有其事有其人,藍博洲將其化為一體,每個人讀來都像自己的故事,最後卻不是自己的結局,「這就是寫小說的優勢。」

(攝影/汪正翔)
藍博洲在15歲時,立志成為一名小說家。從小父親做工,母親不識字,家裡一本書也沒有,偶然間發現姊姊在讀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就此啟蒙了小說之路。他開始在鄉下圖書館大量借閱人文類書籍,讀到赫曼赫塞27歲出版的作品《鄉愁》時,大受感動,「沒想到一個祖父輩份的德國人,那麼久以前寫的作品,經由日文轉譯成中文,還是能感動位於遙遠國度的我,為我解答人生問題。」
藍博洲決定成為一名小說家,期望自己在27歲時也能寫出流傳後代的作品。但還是高中生的他,感覺人生虛無,「人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這個問題深深困擾著他,即便大學四年級他開始發表創作,還是煩惱著寫作應該關心社會、關心現實,但社會經驗不足的他,只能書寫個人經驗。進入《人間》雜誌後,一切有了改變。他寫了白色恐怖受難者郭琇琮的故事,終於進入歷史,那是一位老太太壓抑在心底幾十年的故事,就連故事名〈美好的世紀〉都已想好,她雖然懷疑藍博洲來自情治單位,但又希望能在生命結束前讓這段歷史重見天日。
「寫了白色恐怖,我整個人才醒過來,郭琇琮的人格、理想主義影響了我,我想專心挖掘這些人的故事,後來也開始有人主動找上門,提供他們難友的故事,我想這也是一種心理治療,比憑空創作小說情節還有意義。」他感覺到自己終於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方式,生命因而沉靜。
在長期採集事件經歷者證言、埋首調查各種檔案材料時的日子裡,他不在乎自己是孤獨的少數,「冥冥中有一股力量支撐著我,堅信無論政治環境如何變化,這段歷史、這些人都應該被記憶,這是重要的台灣理想,是台灣的故事。」
〔藍博洲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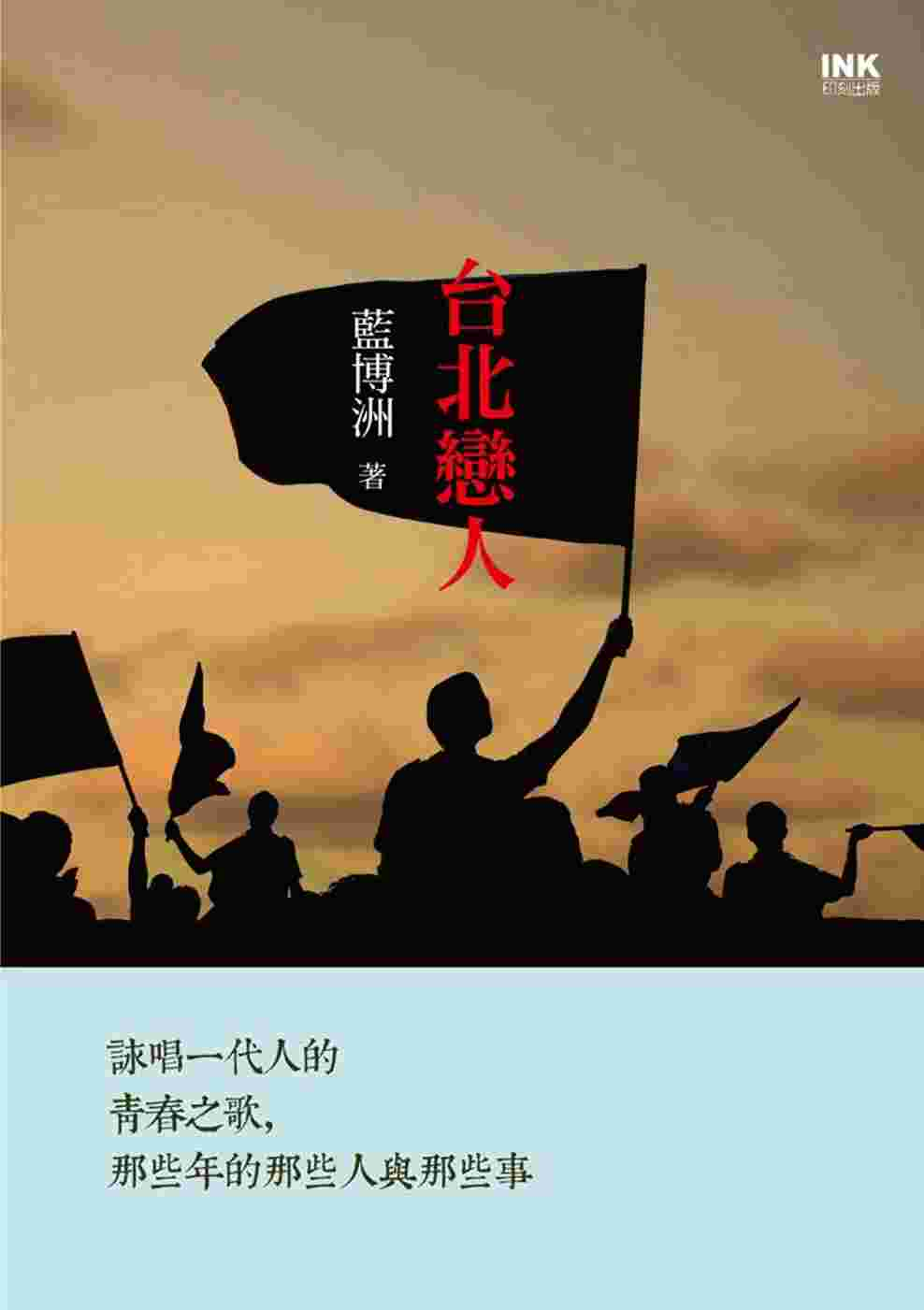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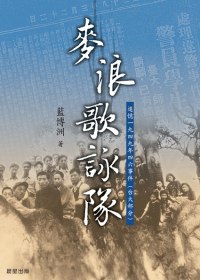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