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為一個天才,一個強大知識的載體,學問是永遠都不會到岸的追求,他的肉身是否能承受這樣的智識追求?天才石神哲哉的確不像其他人,有做好長大要談戀愛的預期。他前半生是單單被知識擄了去,後半生則被愛情這禿鷹整個尋獲,他索性讓它將他剩下的一點都吃乾抹淨,起碼讓他回到自己仍有「人體」意識的溫度記憶。
人們渴望自己不凡,但沒有任何一點庸俗的石神哲哉,被知識大神揀選,卻不見容於這世界上,於是他寧可藉由一次愛情迫降,從知識的仙風道骨裡解脫,讓自己身為人的腐敗一次全到位,任其化為爛泥臭水,至少他揣摩到了一點彷彿是「溫暖」的滋味。
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中描寫的石神哲哉,都很可能是個你我擦身而過時,對他沒有印象的人,沒印象不是指他美醜,而是看得出身上這一套衣服,已反覆穿到如同主人翁乾澀的肌膚上,他年紀不大,臉上卻隱隱透著年輪,致使無從辨識的表情被擠壓在其中,任何訊息都變成壓縮檔,顯然沒有人打開過。那細如縫的眼神,總是看著你之外的地方,只是你匆匆路過,也無暇關心,但其實只消一秒掃過,大約就知道,他是被際遇壓垮的人。
有時際遇是這樣的,它無聲無息的如夜幕降臨,壓得人匍匐前進,不用太久,整個人掛滿了際遇的重量,心頭打著即使日頭下也能結六月霜的哆嗦,際遇讓它的宿主在群眾中消失,連灰塵的存在感都沒有。我們在大城市裡偶爾會見到這樣的人,擦身之際,只覺得彷彿有什麼東西吹進自己眼睛,所謂際遇是可以把一個人變成只有這樣的擾人程度而已。
而所謂愛情呢?
石神哲哉在戲中的為愛情獻身,為了一個不算認識的女性,犧牲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他只需每日買便當時看到她的笑容、聽到她與女兒在隔壁的笑鬧聲,就足夠為她頂罪。那他原本的人生算什麼呢?這份不可思議,促使《嫌犯X的獻身》成為《神探伽利略》系列中最特別的一部,扮案一向以理智的輕快為節奏,羽扇綸巾間就將案件灰飛煙滅的教授湯川學成為配角,在愛情面前,他因不解而變得極渺小,跟觀眾一樣,他不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什麼?──讓石神甘願全然犧牲的,真的是我們認知的那個「愛情」嗎?這對大部份有戀愛經驗的人來說,也超越了合理範圍,甚至也不是梁祝的相互關係,也非粉絲對偶像無涉性愛的求歡,那是什麼?讓將自己塵埃化的石神哲哉,為了幾面之緣,願意窮其所有地做最後一擊?

我一直相信,這樣的故事只有在亞洲才能顯出力量,或許因為我們處於雞犬相聞的擁擠,比如澀谷街頭綠燈一亮,人潮隨時像大浪一樣向你撲打過來,「立錐之地」是就算擁有豪宅的人都無法根除的精神原點,尤其在新興的亞洲市場,強調鳳毛麟角的科舉觀念是怎麼也無法在教改中被滅除的。求職之路也是無論你是否坐擁了幾坪辦公室,「擠」早在我們的基因裡,我們日日像雞群探出頭來咕叫,於是「鶴立雞群」是東亞人集體抱負,其前提是擁擠,「人海」是我們習慣的場景,「滅頂」也是在我們自然的危機考量中。石神的故事,最大的基礎以他智識的巨大,如何容身於龐大的鳥窩思維裡?而他本身因此會感受到的痛苦有多大?
搭滿藍色帳篷的遊民區,是當高中數學老師的他每日上班必經之地,時鐘的制約對他們來講都是鬆脫的,他與他們浪逐於外,他細察那裡乍到「新住民」的時間感,是如何從服裝與作息中喪失,跟自己隨著一方斗室漂流並無差異,他們相同之處都是與外界無連結的。身為天才的他,一生著迷於解開數學謎題,腦中宇宙大到與他肉身所居不成比例,如電影《美麗境界》中的主人翁,拙於(且無暇)應付所有生活,迫使他們回到生活時,是如此的不適應。思考的巨人,很容易成為生活的侏儒,如果此時沒有學術機構保護著他,他會如同鶴錯生在雞群中,從不知有展翅的權利,那生之困頓,將形同將巨人關進火柴盒裡。由於巨人從懂事以來就在「那裡」,到了壯年,因自我保護機制,早已脫離了「石神哲哉」這肉身身分,分裂出來,活在數學的矩陣裡,而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的只是軀殼而已。這是為何湯川學驚訝於石神開始在意外貌,就知識這如太空這無垠的世界來講,屬人基地的波士頓早已跟石神這太空人失去了聯絡,他很早就不在任何能夠偵測到的航道裡,他始終以「死亡」的形態來活在世上。
於是,他在認識花岡靖子、最後為她犧牲一切,那短短幾個月,才是他真正「死而復生」的時間。在花岡靖子扣門時,他正準備要自殺,原著中寫著他的想法:「沒有自殺的理由,但也沒有活著的理由。」那門鈴聲,讓他愣了一會兒,猶如門鈴從未響過,鏡頭停格在他繩圍脖頸尷尬的一刻,到底就此踢開板凳比較方便?還是要應門比較快?這對他來講,像點咖哩飯還是吃湯麵當晚餐一樣無所謂,這人是如此專心地在「死亡著」,死亡成為一個無限循環的進行式。演員提真一是如此呈現「石神」這人:他提起的每一步、每說的一句話,都瞬間散失,沒有發生過的痕跡,這人棄絕了肉身,任由知識在其上漫天生長。因此靖子與女兒如豔陽般笑容出現在門外時,「活」這東西等於溜竄進了他的斗室,漲滿了整個空間,自那一刻起,活跟死劃清了結界,自那時起,他的呼吸才是真正出於自我的意志。但這樣的「愛情」,恐怕是愛情自己都無法想像的最大值,那我行我素、來去不由人的愛情,竟成為一生追求理性知識的石神,墜落前握住的最後一根稻草。
一個靈魂早已死亡的人的初戀,後座力會有多驚人?石神的初戀,跟我們普羅大眾停留在夏季陣雨中的回憶不同。我們一般人從小,大約就知道了成年就要談戀愛,如同隨時預備好要跨欄的哈氣牛群。但石神不同,這個從小活在數學世界的天才,高中時親人去世,無法再就學,期望活在數學裡的他,是自己才華的人質,時間是永遠不夠拿來研究的,所以愛情等於是以綁匪之姿,不由分說地擄走了他。這不禁令人想起村上春樹《人造衛星的情人》的開始,以龍捲風來形容初戀:「就像筆直掃過廣大平原的龍捲風一般熱烈的戀愛。那將所到之處一切有形的東西毫不保留地一一捲入空中……」而從未與外界聯結的石神,更被風吹到毫無落地的可能,已死的靈魂這回被吹得四分五裂,如此的痛,這是他初次感受到「活」在人間,而他願為這份「痛」犧牲所有。
觀影過程中,你幾乎可以聽到他整個人生的乾裂聲,他為了幾乎素不相識的鄰居,不惜滅屍、殺人來製造女方的不在場證據,縝密的布局(包括燒掉指紋與錯亂時間),甚至假恐嚇女方,讓對方認為自己是痴漢,好讓她力求自保,一切都在為自己成為代罪羔羊而鋪路。正因如此,當女方良心不安而自首時,他如同嘔出靈魂般哭嚎著,他自認這像魚乾樣的人生,女方為何不讓它索性獨自發臭碎裂呢?他連戀愛都有求知上的純粹,他的孤單早已被習慣演算成是一個完整的成全,知識是可以這樣淬鍊自己門徒的。
對一個天才來講,戀愛這件事是否是有困難?在《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中,科學家跟智識因實驗而突然發達的男主角查理高登說:「你以後就知道自己智識快速發展,情感年齡卻跟不上的痛苦。」而石神無論教學還是回家,都明顯地處於孤獨的狀態,沒人理解他在課堂上教什麼,或他著迷於什麼。另一方面,活得風光的大學教授湯川學,身邊多半是跟隨者,因此念念不忘唯一能聽懂他話的同學石神。而《獻給阿爾及儂的花束》的查理也因智力過高與過低陷入絕望的孤獨中,最後哭喊:「我寧可不知道他們討厭我……」當智商不在平均值的水平中,情感上是否也能承受自己是個「超人」?身體又是否能承受知識的無限下載?
只為了花岡靖子一個笑容,天才乾脆地將自己自知的「行將就木」狀態放手,讓自己重新活一次,即便幾週也好。他首次從知識的羅網裡逃出來,回到自己「身體的意志」裡,所以湯川學問他:「為什麼你要把自己如此卓越的頭腦用在這種事上?」甚至為了一個不算認識的人。因為,身為一個強大的知識載體,除非是如此殘酷的愛情,才狠得下心讓天才得以平凡一點,並趁最後的機會,讓這「平凡」終結掉自己無止盡的天才刑。
﹝電影簡介﹞
《嫌疑犯 X 的獻身》為 2008 年的犯罪電影,改編自東野圭吾 2005 年同名暢銷推理小說,也是「伽利略系列」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該小說當年驚豔文壇,也成為犯罪人心描寫的重要著作,接連獲得「第 134 屆直木賞」以及「第六屆本格推理大獎」。
此外《嫌疑犯 X 的獻身》在日本重要的推理小說排行榜,如 2006年「本格推理小說 Best 10」、「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2006」、「2005 年《週刊文春》推理小說 Best 10」中均獲得第一名,成為「五冠王」小說,可以說是東野圭吾奠定文壇名聲的關鍵性作品。電影版由與電視劇《破案天才伽利略》同一組演員擔綱演出。本片亦被提名 2009 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亞洲電影獎,2012 年,韓國改編拍攝為電影《嫌疑犯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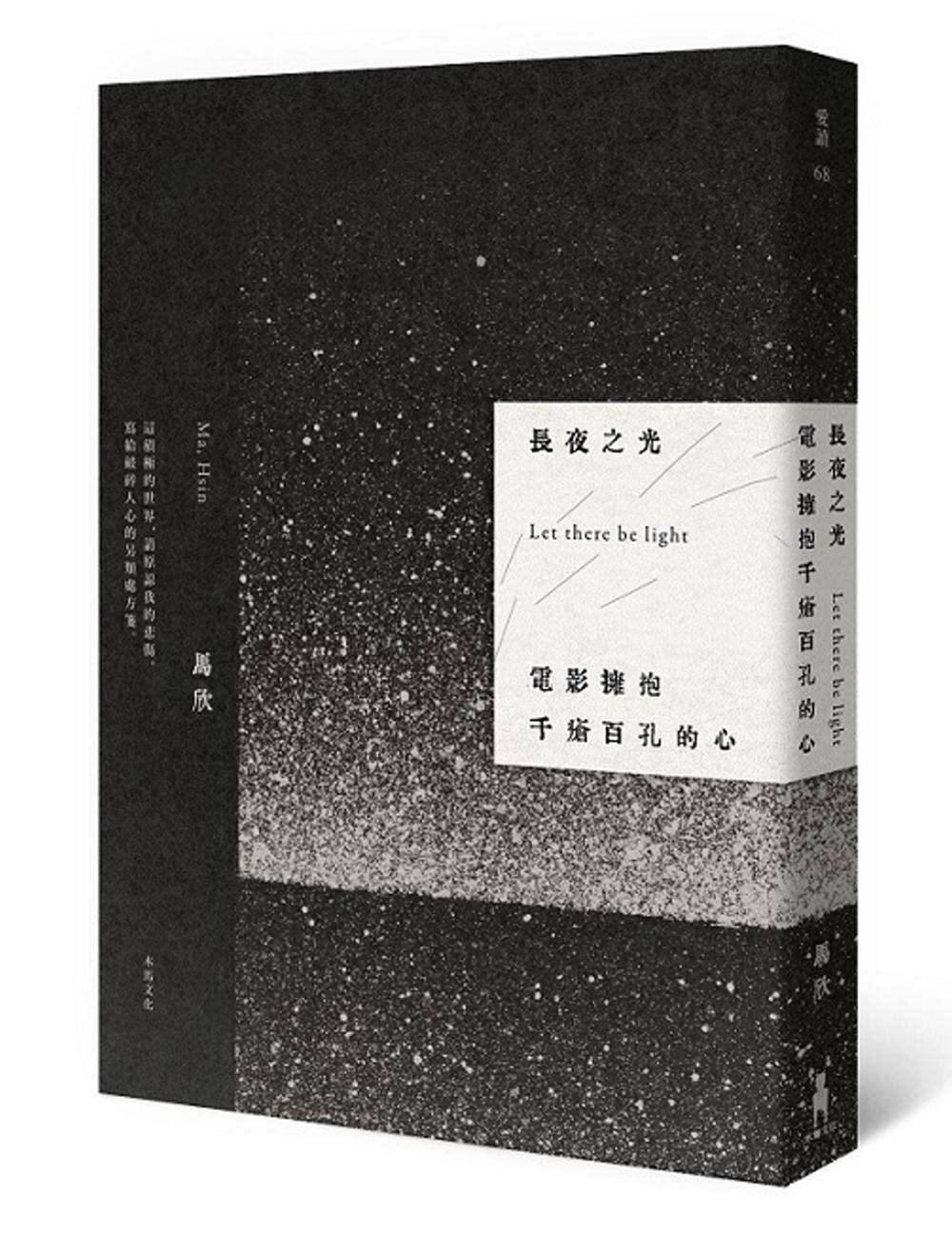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