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史冊走出,巴比倫早已不是巴比倫,它是都會、它是山城、它是看不見的城市,精確且虛幻,模糊且清晰。《晚安巴比倫》重新出版,書中收錄紀大偉1993年至1998年小說創作之外的文章,記錄對朱天文、邱妙津、海明威等作品的看法,深讀《孽子》《鱷魚手記》《荒人手記》的評論,談同志政治,談當時勃發的網路世代,也談電影與劇場。
90年代的台灣酷兒太封閉,只能妄想第一世界國家,要離開台灣,才能夠參加相關的活動,做一些跟同志有關的事情。「當時很多人真的相信,要努力讀書、考上台大,去了歐洲或美國,才能夠追求我的同志生活,要站在卡斯楚街才得以完滿;但現在說這種話,可能就變得有點好笑。」紀大偉說,「台灣很快就趕上了,現在反而是,很多外國人都聽說台灣很開放,甚至傳言台灣同志婚姻已經合法。這不是說可以自我感覺良好,而是在2000年左右,台灣都市的同志生活已經比日本、美國方便,這是所謂後進國家的優勢。」日前,他出差去加拿大多倫多待了幾天,多倫多是知名的同志重鎮,但當地的同志社區規模,大概只有師大夜市的一半。「加拿大國土那麼大,只有那個地方有。這樣是餵不飽台灣人的。」台灣沒有特定的同志區,只是一些散落的地點,加上手機發達,處處都是可以占領的空間。
紀大偉坦言,他其實沒想過《晚安巴比倫》會重出,想著絕版就算了。出版社提議再版之後,讓他在校稿過程中多次為自己當年的「幼稚」而苦惱,一直在逃避出版。「很多小朋友看到但唐謨的書會問,他為什麼會看這麼多電影?這本書出來之後,也有很多人問我為什麼看這麼多書?但有什麼好說的,當時就是這樣。當時的大學生有種焦慮,那些坊間流傳的盜版外文書,即使看不懂也要摸一摸,不然就覺得自己不夠用功。」他後來願意重新面對《晚安巴比倫》再版的原因,跟這些年來台灣的文風衰頹有關,「也想要給這年頭的學生看看:我當學生時的博雅訓練,和你們現在的博雅訓練相比,有什麼相同相異之處。」
這十幾年間台灣的進程,漸漸趨向成熟,社會風氣開放了,卻也養出溫馴乖順的一代。他在大學教書,驚覺現在的學生不敢舉手、不敢發言、依賴網路權威,對於學習的動力低落;直到三月學運爆發,許多出書前的疑慮,都成為微不足道的考量。「他們對於真理和知識的渴望給我打了強心針,我想許多其他老師也被學生們『充電』了。」

「激發一個人的潛能,就要把他逼入絕境,才會有突破。如果都過得很安全,潛能不會被激發出來,也不會有念書、念同志文學的痛苦和快樂。」整個社會都過著小確幸的生活,不去認識自己生長的土地跟環境,不去理解自己擁有的自由,是站立在什麼樣的血淚跟基礎之上,直到遭遇困境,他們才回過頭來思考自己的處境。「去年護家盟11月30日的活動,我其實有點不一樣的心情。之前我在課堂上教《孽子》,學生還會翻白眼,覺得過去的悲情有什麼好講的;現在的小gay小拉都過很好,直到在11月30日被嚇到。有匱乏,才會有絕望,才能去體會當時邱妙津孤立無援的感覺。」他認為,學生們與其坐在教室發呆,不如出去談戀愛,談過戀愛才能夠讀懂文學,看懂一些《紅樓夢》裡的百轉千迴。
紀大偉說話是多線並行的,隨著他的思考進程,一路飛快地開啟新視窗。立足在堅實的學院高牆內,他時時向外窺看,甚至翻牆至另一個世界的風景。但並不固著,始終維持游移的彈性。「有些時候要唱反調,唱反調是很好的精神。」同志婚姻在這兩年是熱門話題,很多人都氣急敗壞,很多人找他站台。「有人認為,有些人要作為表率,表現中年同志可以過得很好、很忠貞,但為什麼要這樣?就是要搞怪啊,出來說冠冕堂皇的話,我會覺得很好笑。文學就是要有些骯臟齷齪的小東西,就像張愛玲不可能出來講女人要忠貞、要愛國一樣。」
不忘唱反調,不忘越過高牆,如果太過正式,太過確定,對紀大偉來說就不酷了。經過十來年,再度跟巴比倫說晚安,巴比倫在台灣,也不在台灣。《晚安巴比倫》是一個青年學者的閱聽筆記,也是上一輪太平盛世給這個世代的備忘錄。
〔紀大偉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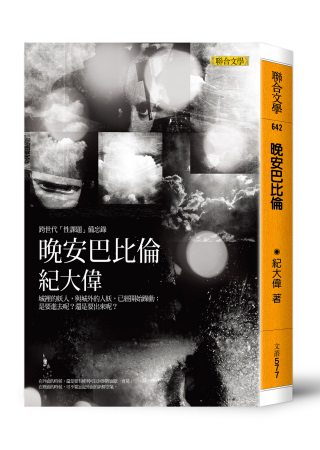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