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新經典文化提供)
近日朱天文的《荒人手記》由新經典文化重新出版,喚醒許多老讀者在1990年代初次閱讀時,對其文字煉金術的驚嘆。
《荒人手記》之後十餘年間,她只有2001年《千禧曼波》、2002年《咖啡時光》、2005年《最好的時光》、2007年《紅氣球》四部劇本創作,2008年才終於出版小說《巫言》。如今,又已過了近三年,我們不免再問一聲:開始寫小說了嗎?
Q:這兩年你的作品在中國陸續出版,中國讀者給你什麼樣的印象?
朱天文:2008年寫完《巫言》去南京,那次讓我非常震驚,有那麼多年輕讀者,以前都是研討會的大陸老師說學生看都看我的書,我想是客氣吧。但那次有從廣東、上海專程坐火車來的讀者,甚至長沙來的讀者。
白天沒事,我看了五家百貨公司,從最高檔的百貨公司,我不知道有誰可以進去消費,到最庶民的都有,當成現代博物館在逛,迅速吸收他們的生活,一直到晚上九點多回到旅館,一回去發現有四個當地的讀者在旅館堵我堵了一天。
大陸就是大,人太多了,每一省攏一攏,攏出來的讀者數量就比台灣多很多。讓我覺得像我們年輕時1970年代的台灣,當時在台灣辦三三集刊,到各大學巡迴、煽動讀者,那時台灣也有那麼多的文學人口。
我們這一輩作家,不大有四十五歲以上的大陸讀者,他們不大能欣賞我們的東西,都是大學畢業二十幾歲到三四十歲的讀者。可能因為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在他們進入現代都市的生活經驗中,看不到這樣的作品,你說小資情調也好,他們更需要有生活的質感。改革開放、城市化三十年還不夠,文學需要消化,不是馬上可以反應出來。到底城市生活的質感是什麼?他們的困境是什麼?他們要在港臺文學中才能找到。
就像我們在KTV唱歌,阿城說我們唱的美國歌他一首都沒聽過,他們都唱東歐的歌、蘇俄的歌。我們在1970至1980年代,很快就接觸到他們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派,當時覺得台灣作家別寫了,他們苦難那麼多、題材那麼多,台灣怎麼比啊?我們當時在補修學分,補修我們不知道的那一半。現在是他們要補修學分,補修他們不知道的那一半,他們在莫言、王安憶的作品中也找不到。
Q:可以說《世紀末的華麗》《荒人手記》《巫言》都是在續胡蘭成的〈女人論〉,而這三部曲都是同一個企圖,只是三本各有不同的嘗試嗎?
朱天文:每次都以為到此為止。
《世紀末的華麗》當然是最後那兩句話在回應女人論,「有一天男人用理論與制度建立起的世界會倒塌,她將以嗅覺和顏色的記憶存活,從這裡並予之重建。 」
結束後寫《荒人手記》,一開始寫的時候,怎麼可能想到用一個同志為主角來回應女人論呢?可是寫到一半之後,開始很想將陰性書寫、陰性烏托邦等很多東西偷渡進來。胡老師的東西對很多人可能歸不了檔,但是小說可以收納、吸收這些看起來歸不了檔的東西,寫到三分之二之後就都在偷渡這些東西了。
寫完之後跟天心說悲願已了,當年發誓「不管用什麼方式都要續完女人論」,當然我絕對不可能用論文形式完成,但我萬萬沒想到是用小說完成,而且是用一個同志的故事還了當年一個悲願。
那應該就結束啦?寫《巫言》是對《荒人手記》的負面列表。1990年代有酷兒等時代氣氛,寫《巫言》就會想「不要」寫什麼,不要用那麼詩化的語言、文字鬆一點、不要那麼凝結,都是負面列表。但寫完的時候發覺,還是在回答陰性書寫,而且相較於《荒人手記》,敘事更是到零,荒人還有一條微弱的線,非常細微的敘事者跟幾個人的情感。《巫言》就完全沒了,完全是岔題再岔題,變成歧路花園。
回看這三本,1990年《世紀末的華麗》、1994年《荒人手記》到2008年《巫言》,都是對〈女人論〉的回應,以三本書回答過往與胡蘭成老師七年的相遇。當時還很年輕的時候遇到他,他也只在我們家隔壁住了半年,其他就是通信,以及我們去日本兩次、每次住一個月。用三本書回答他,我覺得應該已經回答夠了。之後想要寫短篇小說集《時差的故事》。
Q:所以可以說是續〈女人論〉三部曲嗎?
朱天文:可以說是陰性書寫的三部曲。

(圖/新經典文化提供)
Q:妳曾引用吳清源的話「當碁子下在正確的位置時,每一顆看起來都閃閃發光」。從寫完《荒人手記》到寫《巫言》的十年間,應該有很多碁子可以用,妳怎麼選擇題材?
朱天文:講2001年哈金座談會的事情很單純,因為現場真的是災難,我說話是那樣語無倫次,而哈金的風度真的太好了,他非常理解我的狀態,所以他開口就說:真抱歉打擾了你的生活。我回來之後沮喪到極點,謝材俊要我寫出來,要正視我的創傷,就像某種心理治療吧。
題材的選擇,應該是對「巫」這個字,環繞著巫選擇。「巫」相對於社會、主流,是非社會化的、沒有用的,就像世界有月亮這一面、也有月亮的另一面。「巫事」就是沒用的事情,「巫途」是到卜洛克小說主角馬修在紐約的動線,巫的路途也是沒用的。
Q:為什麼要選擇「沒有用」的題材?
朱天文:為什麼要比「荒人」更過分,索性變巫呢?就像《紅樓夢》吧,必須先有賈府,一個講究進退禮儀、有秩序、儒家的的社會建構,在賈寶玉眼中他們就是追求功名利祿,賈父看他就是不成材。因為有賈府這個非常實的體系跟存在,因此才有我們看到離經叛道的大觀園,而我們難忘的賈寶玉是個廢人、整天混在女人堆中。
為什麼會寫沒用,是因為跟有用的東西對話,才能寫無用。無用不是要到山林裡跟鳥獸為伍、當和尚,而是若畫一條從右到左光譜,右邊是社會化,左邊是非社會化,最左邊、左到不能再左了就是巫,因為再左就沒有語言可以溝通了、變成瘋子了。而你的眼睛望向全部的右手邊,跟他對話,採取這樣的位置跟有用的世界辯證,才能寫最左邊的巫。在邊界上不斷講話、不斷發聲。就像有儒家的禮儀,才有賈寶玉的離經叛道。所以寫沒用的東西,是跟社會熱情的對話。
Q:為什麼要採取「歧路花園」的寫作方式,不要有結束?
朱天文:離題再離題,就沒有敘事,沒有敘事就沒有時間。為什麼不能大家都永遠繁盛呢?小時候就感覺到了,為什麼一定要盛極而衰、曲終人散?所以寫《荒人手記》時,本來想寫一個不要有衰老死亡的小說。而《巫言》根本不走敘事,將敘事不斷蔓延,歧路再歧路,在不斷岔題和迂迴之間,時間就會迷路、死神也找不到你,就可以將時間變成空間。
《荒人手記》只能做到最後一句:「因此書寫,仍在進行中。」這是自壯形色,但還是悲傷的。《巫言》一開始就想將時間變空間嗎?沒,也是一路寫下去一直岔題,最後才名之為波赫士的歧路花園,在空間中看花、看草、看星空、看布置。
你說太天真也是吧,希望大家永遠不要散,這是不可能的,這是永遠的惆悵和悲哀,自古以來大家用不同的語調在攻打這個主題:人生為何不能有不散的筵席?在這個落差中產生了文學,產生了哀嘆。
Q:現在如何看自己早年的作品?
朱天文:2008年在印刻出版過往的文集,校對時很痛苦,很多內容都很想劃掉,但我都不去改,很感謝當時寫下來,當時如果不寫就壓根忘光光,如果不寫,以現在的年紀來看也就不值一寫了,不同年紀在乎的東西不一樣。如果當時的作品對讀者有所貢獻的話,就當成一個化石展覽吧。我們不像張愛玲一寫就很成熟了,當時那樣青澀的文章可能可以鼓勵現在的年輕創作者。
Q:從《荒人手記》至今已17年,年紀對寫作的影響?
朱天文:以前哪知道寫作要靠體力,集中精神非常容易。年輕時毫無紀律可言,愛寫就寫,可以一寫就寫通宵。寫荒人時體力最好,可以衝啊衝的寫。現在發現體力需要鍛鍊,不是靈感的問題,而是寫作要靠體力、要生活規律,一星期希望有三天到辛亥國小去走一個半小時,希望一天有四到五個小時專心,那就不得了。《巫言》大半是最後一年寫的,那時下定決心,用有紀律的方式寫。
要是早個十年理解、覺悟就好了,竟然空了個十年!現在後悔了。不能貴族式的想寫就寫,那是太業餘的方式。四十到五十歲,應該可以寫出更多更厚實的作品。那幾年寫了四個劇本,現在很後悔。
Q:現在寫長篇容易還是短篇容易?
朱天文:對現在的年紀,長篇反而比較好寫,「開始寫」難,一旦開始就像找到一條路,可以順著走下去。年輕時沒那麼多東西可以支撐長篇,現在有很多東西可以支撐你走一條長路,長篇的文字也可以放鬆一點,就像在作坊中工作,每天花三、四個小時走一段。而短篇小說每篇都是開始,就像短跑衝刺,需要爆發力,反而適合年輕人寫。
《時差的故事》在2008年就說要寫了,竟然現在還沒寫,哈哈哈~又三年過去了。做了一些雜事,包括胡蘭成的專輯,為舞鶴的簡體字版《餘生》寫一篇長序,雖然是寫序,但其中在反省:寫小說已經是太蒼老的手藝,現在還要怎麼寫呢?另外還寫侯孝賢的新電影《聶隱娘》的劇本,做了很多田野調查,讀了很多唐朝的材料,今年秋天總算可以開拍。這次我找天心的女兒謝海盟當劇本的助理,劇本第一稿的粗活我不要做了,而且她對唐朝也熟得不得了,開會時也可以提供很多意見。
Q:《巫言》中「菩薩低眉」的意象怎麼浮現的?
朱天文:那是我自己的生活經驗,假裝沒看到。人分成兩種,有些人愈老,身體的硬殼就愈來愈硬,但我的心簡直就沒有一個保護膜,心臟是裸露的。我們曾經都像張愛玲那樣很殘忍看世界,喜歡把傷疤揭開來看。但現在無法再如此,無法再揭開傷疤了。
就說貓貓狗狗吧,我的眼睛幾乎是半閉著,眼睛一打開自己的心就戳一大堆洞,自己負荷不了,所以就只好半睜半閉。因為一睜眼就必須接手,而且是終身負責。年輕時很濫情,到處去煽動讀者,結果就是始亂終棄。所以現在眼睛半閉假裝沒看見,因為無法很輕易付出、睜眼接收對方的眼光。對我來說,如果出去跟別人碰面,回來就會沒完沒了。因此用菩薩低眉總括這個狀態,這是我切身的經驗。
所以就知道哈金那場座談,會讓我沮喪到不行。書中描述,我發言時用眼角看到一個人轉頭不敢看、整個將頭埋進去、簡直是不忍卒聽的就是蘇偉貞。
這大約是寫完《荒人手記》之後這十年的狀態,最強烈的感受就是在街上看到貓,跟他對上眼睛的時候要怎麼辦咧?是不是要帶回來呢?年輕時心臟強健,可以去國民所得低的地方,1980年代年輕時可以跟父母去埃及、印度,我現在無法再去這些地方了,看到遍地乞丐要怎麼辦?有人找我去西藏,我根本不要去,世界有很多地方我都是打了個叉,根本就不要去。
Discovery頻道、國家地理頻道也不能看,例如獅子捕羚羊吧,又希望獅子捕到、又不希望羚羊被捕到,該怎麼辦?看到北極熊站在浮冰上面要怎麼辦呢?寧可不吸收知識了。報紙也不看進去,常常只看標題。
Q:這樣對你博物誌式的小說寫作會有影響嗎?
朱天文:所以下一個要寫《時差的故事》,試著做一件自己一向不在乎也不在意的事情,試著來說故事。就是挑戰自己吧,敘事已經到零了,那故事要怎麼說呢?希望手邊的事情在二、三月完成之後,春天天暖時,短篇小說集就能開始動筆,預計一年半之內完成。
延伸閱讀
1.【專訪】《三十三年夢》朱天心:只有自己誠實,才有勇氣去質問別人
2.【專訪】鍾曉陽:交出《遺恨》,我可以和不斷改寫重寫續寫的自己告別了
3.【新手上路】以人類學視角紀錄《聶隱娘》──謝海盟《行雲紀》
4.【書評】陳栢青:後來的我們──讀郭強生《作伴》
5.【閱讀時光|改編《世紀末的華麗》】沈可尚:內在青春的澎湃就是華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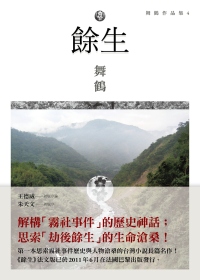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