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多人認識馬志翔是一個演員,這麼認識他的人,也許記得他曾以電視劇《孽子》與《赴宴》的阿鳳與馬志強,兩度入圍金鐘獎最佳男配角。這幾年也有人因他的族名「Umin Boya」認識他;作為公眾人物,花蓮出生的他,兩種原民血統的混血,在這樣的時代裡,他很自覺地關注並樂意標榜自己的原民身分與文化傳承,或者也不自覺地成為不少人眼中,當代新世代原住民在台灣與世界找到自己生活方式的範例之一。
但他還有一個身分是編劇與導演,《KANO》是他首部執導的電影,但累積經年,他以編劇與導演的身分,入圍金鐘獎七次,由《十歲笛娜的願望》與《說好不准哭》,各拿回一次編劇獎與導演獎。
這是他熱愛的事物,若你有機會與馬志翔聊天,聊到原民議題或編劇導演工作,他會有很多熱情可以分享,與因為慎重深思而欲言又止的思索片刻。「當時是宣傳《賽德克.巴萊》一個雜誌拍攝,場景設計是要我和魏導一同在床上放鬆聊天,後來我們真的聊開了。當時我問他最近在忙什麼,他說忙一個『小的』,關於棒球。我當時馬上指著我自己,說『我我我,找我』,其實我當時想的是要找我演。」
直到後來魏德聖寄了劇本給他,他都還不知道魏導準備將這部電影交給他導;當他後來知道這部片將成為他首部電影導演作品,「第一個感想是非常興奮,我手心都冒汗了。」
之前馬志翔的所有作品,都是他自己編劇,即便《飄搖的竹林》是改編自瓦歷斯.諾幹〈番人之眼——飄搖的竹林〉,也是他與作家訪談討論後,自己著手將散文改編成電視劇劇本。第一次拍別人寫的劇本,馬志翔作為導演,很自然會在分鏡對白等等,都有些改動。「其實在拍攝時的工作本上,我還是一併掛名編劇;但我後來覺得,這發想不是我,雖然導演需要用鏡頭影像去說故事,會有很多參與創作,不過這本就應該包含在導演的工作內容裡,我想,我就先專心把導演這塊做好就好了。」
雖然這次拍攝一開始,他和這次轉任監製的魏導,說到這次的電影工作要「豪邁」,但很快地在拍攝時也感覺到了壓力,開始覺得十分緊繃,他曾用過「以往是短跑衝刺,這次是長跑,開始會衝太快」來比喻首次擔任電影導演的調適,問他究竟具體的工作上,這樣的緊繃是什麼,「比如說哪個段落,你很喜歡一個鏡頭,你會想著一定要怎麼怎麼拍出來,花了很多時間和資源,但其實在整體說故事上面,有其他的方式,觀眾看起來也不錯,甚至又可能更好,」他用了另一個比喻來說明導演的工作,「就像拼圖,你有時拼到這裡,就少了那一塊,你就專心鑽到這一個小細節,就鑽在那裡,非先找出來不可。但其實若先拼另外一個部分,這個缺失的一塊輪廓,不是反而更清楚、更容易找到嗎?」

這次電影裡會有相當多的棒球場面,用這些比賽過程來鋪陳角色心境、情感厚度也很重要,但用影像來描述一場棒球賽,在風格、技術上就是個未有太多明確範例、很不容易的挑戰。「我看過一些棒球電影,但我這次沒有參考任何一部,」打過少棒、也是重度棒球迷的馬志翔說,「棒球真的很難拍,因為在場地上,人這麼分散,不可能像轉播那樣去拍,人和人之間的互動和緊湊的張力就很難講出來。」
「我一直在想怎麼把我的『棒球』拍好。」這是他在講到不同拍攝階段心境時,重複提到的話。而棒球,是和馬志翔一說到同樣會很投機的話題。或者在一個尺度上,棒球作為國球,台灣人人都算是棒球迷;但總有一些棒球迷,是能在電視上隨時看到一個打席,投補怎麼配球、打者哪些策略、球一出手,未等球評解說就自然講出這是什麼球種,還能示範、講解這位投手這種球路細微的特色在哪,為何這時捕手會選配這樣的球種。每一位這樣的棒球迷,也都有自己的一套獨門角度、專門說法,要告訴你「棒球是多麼特別的運動」,而馬志翔的版本是:「你有看過其他哪一種運動,是由防守者持球,進攻者只能被動等待的嗎?」
很接近的板球當然不能當作破綻,何況比起那些曾聽到不只一次的「非時間制,真正原則上永遠都有可能改變勝負」這類說法;這是從未聽過、頗為原創的心得,來自他從小擔任投手與一壘手,曾投到拇指指甲都翻起來的親身經驗、一輩子的喜好。

不過馬志翔坦承,在準備拍攝這部電影之前,他與台灣多數棒球迷一樣,對嘉農的歷史並不熟悉,也以為紅葉少棒是台灣棒球的起點故事。但承續著果子電影從前一部拍攝台灣歷史的電影《賽德克.巴萊》時,在歷史考據與田野調查的努力程度,這部電影於此也沒打算放鬆。
他們訪談了當時嘉農幾代的球員,例如蘇正生、人稱「台灣最強第四棒」的洪太山等選手,找了王貞治當總顧問,他給了「要把訓練的部分拍扎實」的建議(馬志翔將他的神采作為戲中近藤教練的教練佐籐先生的原型,找來曾演出《刺蝟的優雅》的伊川東吾演出),也找了謝仕淵擔任歷史考據的顧問,他與謝佳芬合著的《台灣棒球一百年》,於2003年出版時入圍金鼎獎,成為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推薦書,是這十年來一整波要追溯台灣棒球歷史,找到早於紅葉少棒真實起源風潮的原因之一,也是許多人重新發現「嘉農」棒球的原因。
這本書裡,當然也提到了台灣更早的「高砂棒球隊」、「能高團」;馬志翔自然也知道,但他要強調,擇定「嘉農」故事,以此為「起源」,是有過考慮的。
「我已經開始有些壓力了。大家對我們在這方面好像要求會很高。」關於歷史考據,馬志翔苦笑著說,「『能高團』當然更早,而且也很強很轟動啊,去日本比賽以28比0打敗對手,但這些球員有些就留在日本發展,並沒有依舊延續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而『嘉農』更不一樣,這些球員去打過了甲子園,回來後仍繼續在棒球場內外努力,影響力一直到今天,比如之中這位球員東和一。」馬志翔指向旁邊海報上的選手,「他的兒子是這幾年台灣青棒冠軍平鎮高中的總教練,到現在還持續很有影響。」

他說的總教練是藍文成,若很關心台灣職棒的球迷,甚至還記得他曾是三商虎隊的外野手。東和一後來改為漢名藍德和,與同是原住民、在隊伍裡名叫真山卯一,後改為漢名拓弘山等隊友,回到台東繼續推廣包含棒球等許多運動的基層教學。其實包含嘉農1936年參加甲子園的隊伍名單裡,有位叫浜口光也的原住民,後來改為漢名郭光也,現在除了他的孫子郭岱詠、郭岱琦都是中華職棒選手之外,他還指導了一位童蒙時代的姪子,郭源治。別說他後來的鼎鼎大名,1969年,台灣棒球史上很轟動的一頁、很有影響力的一代:台中金龍少棒,他就是之中的一員。光是這麼簡單幾條線,「嘉農」與台灣棒球的整個系譜也就牽連至今,每年都從這些後繼者的身旁,培育出更多的台灣棒球員。
「我們說『起源』,不是因為最早,而是因為嘉農棒球還延續著,回鄉扎根,一直到今天還持續著。」馬志翔補充,「選這個時候的這群人,在這電影裡說的棒球;不是日本人的棒球、不是漢人的棒球,甚至不是原住民的棒球;就是台灣棒球,台灣人的棒球。」
曾親口從蘇正生口中,聽到他說當時的「嘉農棒球隊」裡,沒有族群問題,「外圍當然有這樣的歧視風氣,但在這支球隊裡,用人唯才,誰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就是誰去表現,這也是蘇正生前輩親口說的。」
「我們在這部片裡,想表現當時的歷史氛圍,呈現抓緊土地的精神,只是用的是一個真實發生的棒球隊的故事;所以這電影不只是熱血,也不只是棒球而已。」
其實對於不少認真的電影工作者,在考據與創作呈現上的拿捏,往往是最難的,也都需要有所取捨,「我們在這部電影裡,是有一個改動,嘉南大圳的開通是在1930,所以1931就已經存在沒錯;但我們把開通時間移動一點,到嘉農第一年進入甲子園的1931年,」馬志翔又用了一個比喻,「就像梅花開得很美,櫻花開得也很美;我們讓梅花開得晚一點點,配合櫻花的時間。不過最主要是希望讓觀眾有一個感覺:這塊土地上,廣闊的嘉南平原,曾經有很多精彩的故事發生,而之中有些還同時綻放。同樣是想讓觀眾感受到歷史氛圍,與抓緊土地的感受。」
說起來這樣的創作權限是很不小,但他也分享了一個簡單的苦惱,「像是球衣背號這件事,不只是好看,比如一群人遠遠在那裡,背號能讓觀眾很快辨識與認識角色,當我查到資料,1931年的春季甲子園球員有背號,我多興奮啊;但繼續查下去,那年的夏季甲子園,故事裡嘉農參賽的那次是沒有背號的。考慮了一下,也就不能放上背號了。」
我們談了許多的棒球、包含當年的時代裡的棒球,馬志翔覺得應該要提醒,「其實這部電影不只是棒球,甚至不只是熱血。你若進到電影院來,除了能享受到好看的故事之外,也希望能讓你對自己的土地更認識一點、更有信心一點。我們好像一直在期待著別人對我們的肯定,但我們確實應該能更認識自己、肯定自己。」
嘉農的傳奇、熱血的故事,大概會從此刻到電影上映,被許多人觀賞記得之後,無論深淺寬窄,都成為認知的一個部分,如同《賽德克.巴萊》這部賣座商業電影之於歷史裡的「霧社事件」那般。我們問導演,這部電影有沒有哪個部分,是觀眾進場後,值得額外注意的?我們原以為他會如許多創作者,舉些具體的段落拍法,或者情節轉折,但他認真想了一下說,「創作很奇怪,你想著故事與作品,但創作最棒的是重新認識自己。做劇本與導演這些年,我以前一直沒有發現,原來『父親』這個角色對我的影響這麼大。在這部電影裡,近藤教練的角色對於之中的球員,其實也就像是一個父親面對孩子。這個層面是我到殺青那篇,看著飾演近藤教練的永瀨正敏,他靜靜走過來拍拍茫然放鬆的我的手臂,才又再次發現。」
在這距離上映前不久,經過一整日最後緊鑼密鼓後製與宣傳行程的他,從談起棒球時的活潑稍微安靜下來;但又在談起劇中這些球隊裡的孩子,每個人分別的故事,比如飾演主角吳明捷的曹佑寧,本人是中華青棒國手,還是世青賽的明星球員;比如飾演虛構角色的學長投手齋藤,演員在拍完戲後重新去嘗試棒球路,去年被選進城市隊的故事;他這時的神采飛揚與口中的口氣,其實也像是個父親一般。
想起方才他說「這電影的內容是關於成長的故事,但對我來說,拍攝這電影也是一個成長的過程」、「創作最棒的是重新認識自己」;你就完全懂了他的意思,也知道這部片,除了會是馬志翔導演的第一部電影作品,也可能正在此時,你是見證著一位新興電影導演將如何繼續成長下去、有著更多更豐富導演歷程的成長故事。

《KANO》預告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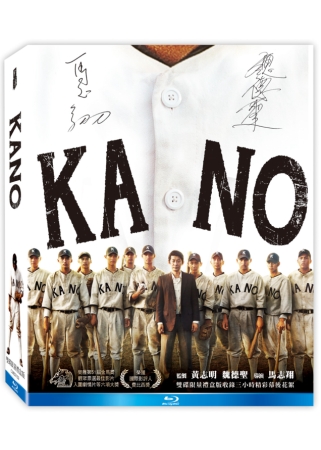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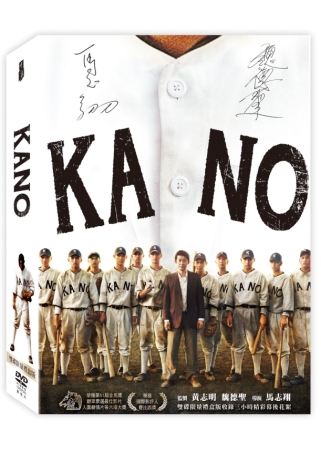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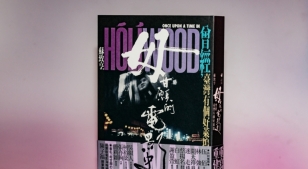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