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離電影,已經一年了。一年的時間,讓我閱讀井上靖的《我的母親手記》原著小時說,有著距離入味的美感,更加能夠感受電影和文字互相提示呼應的用意。
究竟要先看小說?還是先看電影?在我來說,沒有絕對的順序,但是中間相隔一段時間是必要的發酵過程。小說有電影無法交代的內心世界,而電影有小說無法抵達的聲光空間,不管是原著小說或改編自小說的電影,都是獨立的作品,沒有誰不得背叛誰的問題,影像與文字各自呈現的力量不同,倘若真的喜歡,小說和電影,缺一不可。
我看電影當時,對於影像飽滿的昭和風味與色澤,非常入迷,役所廣司和樹木希林的母子情分,已經超越洗鍊的演技,彷彿他們就是現實生活裡的真實母子關係,而宮崎葵的孫女角色,更凸顯於小說之外,有更多延伸,因而變得很關鍵。直到一年以後閱讀小說,我更加喜歡井上靖的文字,以及譯者吳繼文的翻譯功夫,影像回歸到文字之後,回沖還原成另一種味道,是非常動人的。
對於失智的母親,在年老之後,逐漸在記憶和遺忘之間反覆折磨的種種,井上靖以「私小說」的形態書寫,猶有一種超越小說的真實坦率。老派文豪的用字向來都有再三琢磨的功力與誠意,井上靖的文字更加優美,但那優美不是不著邊際的炫技,而是有著扎實的情感後座力,我十分羨慕這樣的文學表現,然而那已經超脫文學的範疇了,畢竟書寫的,是親情的內裡,很深層的心境。
小說故事中,逐年失智的母親,卻常常憶起少女時期愛慕的少年,「被時間所侵蝕的母親,言談與表情卻帶著一種與老衰無關的哀愁。老年人獨特的樂天笑聲也好,偶爾瞥見的釋然表情也好,我們都應該有退後一兩步默默注視的必要。」
一般人進入老境,過往的一部分記憶或許牢牢記住或許消失無蹤,「對自己兒女的關心程度和年輕時候比起來,也所剩無幾……或許母親是讓橡皮擦將自己一路走來長長的人生之線,從一端開始抹除淨盡了。當然這並非出自母親的本意,拿橡皮擦的是老衰,教人無可奈何的老衰,它將母親數十年人生之線,從最近的地方逐漸擦拭一空。」
電影之中,飾演年老失智的母親角色,是樹木希林,她在高大的兒子役所廣司面前,反倒變成率性的女兒那般身形渺小,經常在深夜的屋內,尋找那本紀錄著老伴過世當時參加告別式親友的奠儀冊子,偶爾跟寫作空檔休息的兒子坐下來喝杯茶,然後看著不遠處書桌的方向,對兒子說,「以前每天在那邊寫東西的那個人死了。」
「母親那親飄飄的肉身充滿難以捉摸的無常之感……」我回想一年前看過的電影,樹木希林的模樣,確實有那樣的味道。
作者書寫到母親過世之後,長年照顧母親的妹妹以手指止住即將奪眶而出的淚水,替母親說出臨終感言:「沒有拖拖拉拉,說走就走,很像奶奶的作風,『現在開始我就自由自在,無憂無慮啦,你們應該不知道吧,我坐的可是貴賓席喔!』」
井上靖在小說之中提到一個名詞,所謂的「塵勞」這種東西,「或許只會積壓在女性的肩上,那是漫長的婚姻生活中,無關愛恨,做丈夫的只會留給自己妻子的東西也說不定。一天天,說不上是恨的恨意緩緩積存在妻子肩上,如此一來,丈夫成為加害者,而妻子就變成了受害者……」
也因此,本來應該肩負起照顧母親責任的長男家,母親始終神經質地充滿警戒,「給自己的女兒照顧就罷了,住到有外人在內的兒子們家,門兒都沒有。這輩子從沒謹小慎微生活過一天,到這麼老了還要在兒子家為了怎麼拿筷子而戰戰兢兢我可不幹……這些話母親說了又說,不管在誰看來,都是脾氣古怪、冥頑不靈。」
然而,這樣被老衰的橡皮擦拭去記憶的母親,「在漫長而激烈戰鬥中,一個人孤獨地奮戰著,奮戰終了,如今成為一小撮骨頭的碎片……」當井上靖寫到家裡的長男捧著骨灰罈上車時,總覺得,電影也好,小說也罷,那不就記錄了身為人母人子的某種深沉的情感嗎?我因此慶幸在這樣的人生階段,讀到如此動人的文字,那無疑是種貼心的提示了?
闔上小說,會想要找個時間,跟母親坐在午後的廚房聊些事情,或是,牽手去散步。而總有一天,我們終將無可避免地,也被老衰拿著橡皮擦,將一路走來或長或短的一生之線逐漸抹去,然而,也沒什麼方法做準備了,那就盡力過好眼前的每一天吧!
其它作家的母親手記——
瞿筱葳:幸好,還有文學能盛接親情
貝莉:我開始看的第一本漫畫、第一本小說,都是母親拿給我的
張萬康:一隻狗、一隻貓、我媽,和我,我們都宅,相處時間多到有剩
楊富閔:或許我捨不得虛構她
當我們討論母親,我們想像的「她」是什麼模樣?女性如此複雜而美麗,由女性身分羽化而生的母親,亦擁有千百種不同個性與樣貌,今年五月,「OKAPI」精選「母親」相關主題文章,各世代親子溝通、婆媳相處、夫妻對話,還有母親節推薦讀本、電影,還邀請多位作家來分享記憶中母親的拿手菜。(點圖看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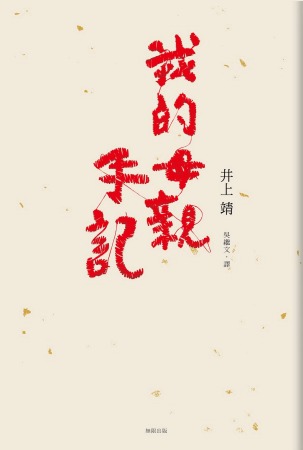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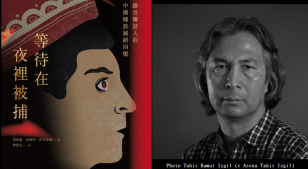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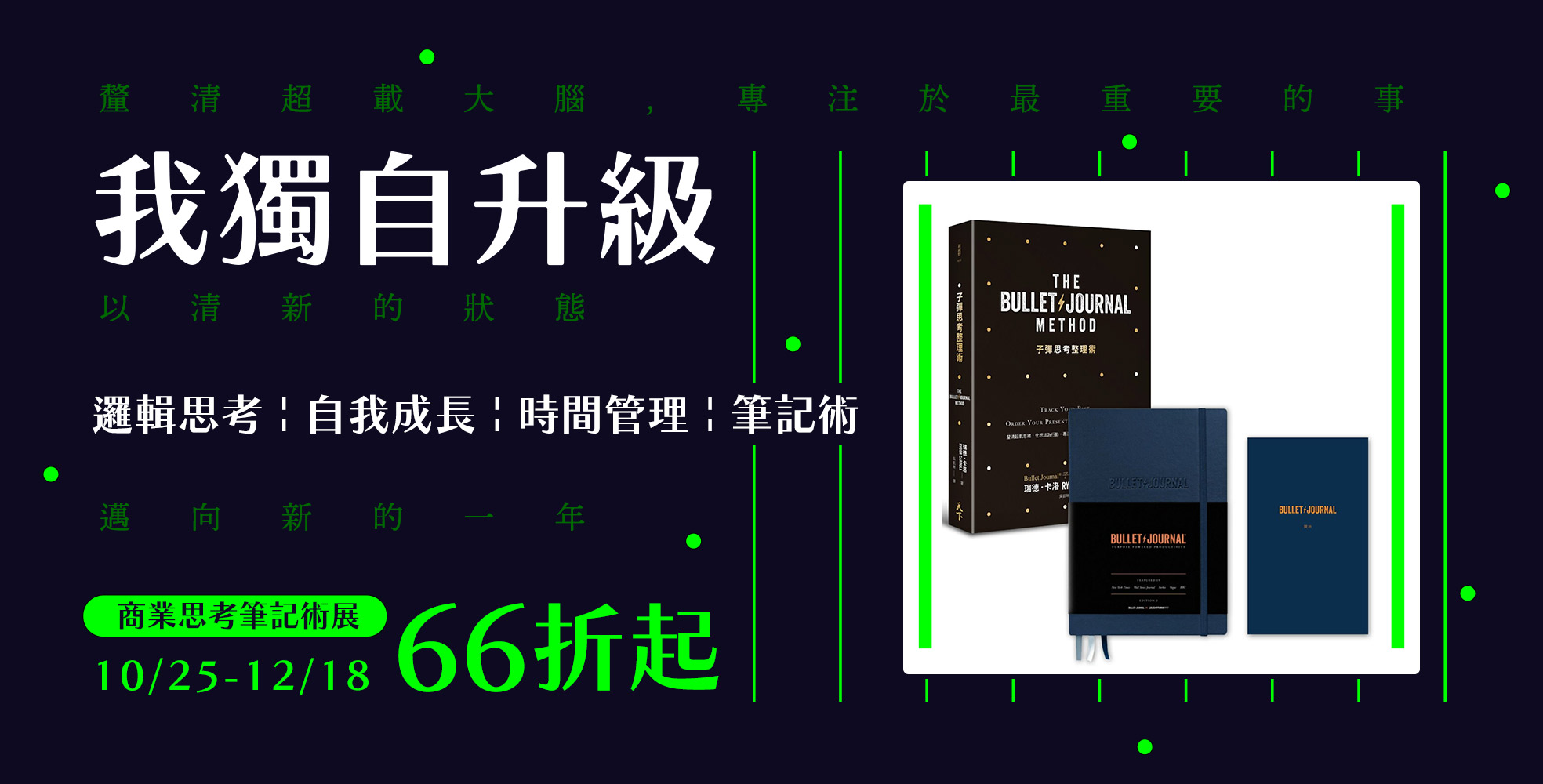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