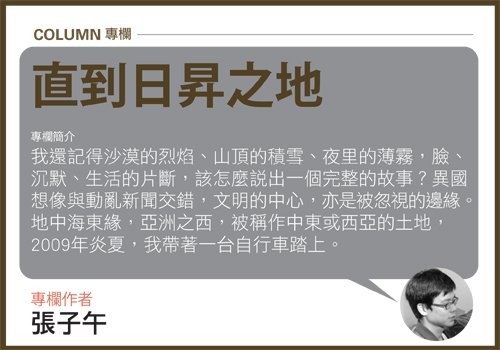
直到日昇之地 地圖
遠方山脈籠罩著層層烏雲,風一陣一陣,從南方吹來。
托魯斯山脈(Taurus)的風。
已經到了安那托利亞高原的邊緣,耳際咻咻的風聲,伴我走過綿延草場、積雪山頭。空氣乾燥、雲層又厚又低,看不見太陽的影子。
山與海截然不同,海岸山脈儘管陡峭如雲霄飛車,目光投進一旁的海洋時,那巨大的蔚藍彷彿有種牽引之力,能為肉體一再注入新的能量;高聳嚴峻的山就不同了,它們像銅牆鐵壁般橫阻面前,並掩蓋住下一段路徑,我渺小的身影被團團包圍,看不見前方的地平線。
只能勉力或推或騎,度過一重重關卡。上坡時,每每像是要呼出最後一口氣一般的,從身體最深處喘息、換氣;下坡時,疾速俯降在滿是碎石的爛路,震得魂魄都要掉出來,迴旋轉動的山脈閃著堅硬的色澤,忍不住仰望它的崇高,卻不希望多待一會,恐怕會就此被吞噬進裡面。
但在人跡罕見的廣闊山脈中,我才真正感受這片土地的脈動。柏油路不時飄來新鋪設後刺鼻的焦味,自行車輪胎壓在其上發出細微的吱嘎聲,未完全貼服路面的小碎粒劈哩叭啦的捲入輪框,彈飛出去,砸到小腿上的那一刻,實實在在感到,跟隨著這些道路,我也隨之流進土地內裡交錯分布的血管,蔓延、交會、湧動,連結起遙遠而模糊的過去,以及充溢所有感官的現在。

離開伊斯坦堡那天的早上,天空也布滿厚厚的雲。躺在黛芙妮家的客廳,因為兩天不停的行走以及剛抵異國的興奮與時差,身體疲累而沉重,模模糊糊中,一陣醇厚的歌聲將我喚醒。
You got a fast car
But is it fast enough so we can fly away
We gotta make a decision
We leave tonight or live and die this way
你弄來一台快車,
但它能否快得帶我們遠走高飛;
我們得做個抉擇,
今晚就走或者這麼活著然後死去。
熟悉的旋律,從房間的音響傳來,八○年代美國的黑人民謠女歌手Tracy Chapman。黛芙妮揉著惺忪睡眼走出房門,我說我以前也很喜歡這首歌。我們相視而笑。時候到了,在她家樓下的馬路旁握手道別後,我騎向碼頭,度過博斯普魯斯海峽。不久,大雨落下。

短短幾天充滿音樂的日子,彷彿是非常久遠以前的事了,廣闊的高原只有風聲與我自己的喘息。清涼的風持續吹來,吹乾身上的汗。冒著熱氣的茶被端到我面前,鬱金香形狀的小巧玻璃杯,擺放在刻滿精緻花紋的小錫盤上。兩個茶壺交替的注入一半濃茶湯、一半沸水,丟進兩顆方糖,在小湯匙輕脆的攪拌聲中,身子暖了起來。
看我的杯空了,穿黑色長袖較年輕的女人殷勤的為我再添茶。在這遠僻的山間公路旁,經過杳無人跡的草原,彎過一個緩坡,我遇見搭起草棚賣櫻桃的一家五人,後面就是一大片櫻桃園,年輕男人剛剛才得意的帶我去參觀。停在路旁喘息,跟他們買些櫻桃來撫慰乾渴的唇舌,一家人就邀我與他們一同午餐。
不論年長或年輕,他們全都有著粗糙滿是皺紋的皮膚,尤其是一笑起來,整張臉像海潮推擠般,漾起層層摺痕,像是有一種擺脫不了的憂鬱在臉孔深處。年輕的女人拿出一大盆拌了紅色醬汁的通心粉,分裝到每個人的盤子上時,再加入自製的鹹優酪乳,配上麵包,又酸又鹹帶點微辣,我稀哩呼嚕的大口吃著。
令人畏懼的高原之路,還好有這些人們,令人熟悉無比的「土式熱情」。年輕男人一下子斜八字手刀比畫在胸前,一下子笨拙的用兩根細竹籤夾起盤中的通心粉,用他所知關於我全部的一切象徵:李小龍和筷子,來穿越語言的隔閡,交流、對話。
一種接近,土耳其給我的接近感,在剛開始上路的時候自自然然顯現。
坐在對面的老媽媽,眼神穿過我的肩膀,憂慮的望向遠方山脈間的雲層。接著她咖啡色雙手手掌朝上,臉朝向一側,嘴裡喃喃恍若滿腹心事欲吐,頓時牽動臉龐一道道深刻的皺紋。男人比手畫腳對我說,她在為你祈禱,前方不要下雨。

土黃色的丘陵漸次展開,遠方壟罩在層層的煙霧裡面,蕭瑟的風被潮濕空氣取代,微鹹發熱,已不再帶著中高海拔所獨有的松針清香氣息。托魯斯山脈在我身後急速閃逝而去,終於快要抵達海岸旁富庶的平原。
沒有下雨。

張子午
 生於台北。在力有所逮時,希望以自己的身心,紀錄下世界的真實與差異。2007年獨自以自行車橫貫歐亞大陸,從中國出發,一路向西,抵達陸地的盡頭葡萄牙。2009年帶著同一台自行車穿越中東,旅程結束於埃及開羅。
生於台北。在力有所逮時,希望以自己的身心,紀錄下世界的真實與差異。2007年獨自以自行車橫貫歐亞大陸,從中國出發,一路向西,抵達陸地的盡頭葡萄牙。2009年帶著同一台自行車穿越中東,旅程結束於埃及開羅。曾獲第三屆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第四屆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評審團特別獎、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類創作補助、行政院客委會98年度築夢計畫。 著有《直到路的盡頭》,同名部落格不定時更新。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