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陳昭旨)
採訪當日午後下了一場陣雨,甫自日本返台的張維中剛結束一個廣播通告和餐會,拎著白傘,穿著今夏新裝,坐定咖啡館,主動拿出手機拍了OKAPI,侃侃而談聊起散文新作《夢中見》,和他的東京生活。
出版過多部散文、小說、旅遊隨筆,專欄作品散見兩岸三地雜誌與網站,張維中的書寫大多來自日常生活的片段,「我很容易被環境影響,換一個城市、換一條街道,我會很敏感地去察覺當中的變化,找出可以探究的角度。」是以,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略、被放過的小事,都被張維中用筆記本或電腦即時記錄下來,「筆記對寫專欄來說,能讓我針對題材再去發揮和延伸,也比較有效率。唯一擔心的是,有一個很好的點子,但找不到適合的敘述方式。」
「小時代裡卻充滿著大幻想,每個人深陷在智慧手機的APP裡,幻想對方消失的真正理由,然後等待一次爆炸。」──〈消失的,消失的理由〉,《夢中見》
張維中除了固定關注社會新聞事件,對電子商品也極感興趣,平常除了逛街,他也熱愛逛電器賣場,於是,跟網路電信解約、換手機……等事,都成了他的書寫題材,「寫這些不只是產品新知,而是跟我體會到的人際關係作結合,我希望自己的散文能夠傳達人與人相處的情感。」
《夢中見》以親情破題,輯一「生命的模樣」詳細描述他與父親在世時的互動、父親過世後的思念,兼及日本311大地震後的生死議題,這些,皆是他過往作品較少碰觸的。他提到,父親因帕金森氏症長年臥病在床,行動不便常亂發脾氣,行為舉止亦有些暴力,受苦的,不只是病患本身,家人也各自承受著壓力,「父親以前常要求我們陪他去中正紀念堂看國劇表演,我們都覺得不耐煩,輕易地拒絕他,直到他過世,竟然連一次都沒有去過。回想起來,與其說後悔,不如說是殘忍。」
張維中說,《夢中見》算是一部獻給父親的作品,落筆成文也多少有些告解之意,他寫來節制,將傷懷轉化成堅固的力量,「父親離開後,家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緊密,我和姊姊們更懂得珍惜和母親相伴的時光。」也是透過書寫,張維中才瞭解到自己和父親有許多相似之處,「我父親17歲就從大陸來台,多年後我陪他返鄉探親,他才赫然發現,原以為的家鄉已成異鄉;而我則在東京找到我要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我們性格中都帶有離家遠行的基因?」
定居東京已邁向第六年,身分不僅從學生變成上班族,也度過了311地震帶來的震撼,與災後社會瀰漫的「自肅」狀態,舉凡日本的國民病「花粉症」、市場推出的期間限定產品、下班後的居酒屋等現象,他都站在第一線實際體驗,也走出了屬於自己的城市步調。
「因為賑災捐款的關係,才讓日本對台灣人有比較深刻的印象,也開始對台灣產生興趣,甚至有雜誌、電視節目來製作專題報導。」不過張維中提醒,「台灣人對日本很有好感是危險的。」他周遭有些朋友剛到東京都碰了不少人際上的軟釘子,因為日本人客氣委婉的一面,常讓人摸不著對方的真正意涵,「我也吃過悶虧,後來才知道別打破砂鍋問到底,他們不喜歡主動Say No、不願把事情說破。」
「事實證明,快速的回信代表你很有效率。有效率,就會加快下一件事情進場的速度。結果,事情非但沒有減少,還做得更多了。」──〈消失的,消失的理由〉,《夢中見》
進入職場後,張維中對日本人「不愛打電話,但回信速度超快」也感到訝異,他說,公司同事幾乎連休假都會回覆公司郵件,一長串的寄件副本來來往往,有時週六剛睡醒,一上網點開信箱發現全部都是新信件,他咧嘴苦笑,「即使假日想自我區隔,但為了不耽誤進度,不回都不行!」
傍晚採訪結束,張維中趕赴與母親之約。隔日,南下高雄舉辦新書座談會,與東京設計學校時期的同學相聚。接續還有旅遊本業的工作會議與新書宣傳,固定的專欄寫作、截稿、朋友餐敘,密集滿檔的行程,就如同他喜愛的歌手藍心湄唱的「一路狂奔不回頭……」
〔散文.快問快答〕
Q1. 您最喜歡的散文作家是?
張維中:很難挑出最喜歡的,但最常拿出來重看的是張愛玲,我也喜歡張惠菁、張曼娟。我不喜歡張愛玲的小說,卻極愛她的散文。她是很聰明刻薄的女人,書寫的角度很有意思,而且她也很愛城市生活,善於觀察城市裡的小事。
張惠菁的散文很冷靜,文句中帶著歷史的觀點。她也善於描述生活細節,尤其是看待事情的切入點,常以時間的縱軸與位置的座標,定出散文中獨特的敘述感,呈現人在宇宙中存在的意義。
張曼娟散文的情感面比較濃郁,對時間的流逝極為敏感,也會感到惶恐。她對於美好的事情很容易察覺,但很清楚那美好的剎那容易消失,而這部分也是我從高中讀了她的第一本書之後就非常喜歡的。
Q2. 看過印象最深刻、至今記憶猶新的一篇散文是?
張維中:張愛玲《流言》中的〈公寓生活記趣〉(現收錄於新版《華麗緣》)。
她觀察公寓裡鄰居的動靜、雨天時雨水滲進牆壁的痕跡、電梯的聲音,甚至寫到她午夜從公寓樓上往下探,望著收班的電車廠,每班電車在月光中袒露著白肚皮……哇,那些細節真是太棒了!
Q3. 您自己在散文寫作時,對真實與虛構的態度是?
張維中:什麼是「真實」呢?這很難定義吧。我現在寫散文主要是來自於自身的真實故事,我同時也寫小說,對我而言,後者能夠展現虛構的聯想力,就像電影導演、編劇那樣發揮,不過小說其實也經常運用真實的素材。我年輕時曾寫過虛構散文而拿了獎,但我後來很快決定不寫虛構散文了,並非因為嚴肅的文學虛實問題,而是回歸到這樣的文字對自己有沒有意義?我希望散文能純粹地記錄生活,就像一部比較精煉的日記。
此外,這個議題有個癥結點在「文學獎」。我後來發現,國外並沒有「散文文學獎」,日本的直木賞、芥川賞都是比評小說。散文的得獎者因為經過評審認可,獲得獎金,受到媒體報導,所以讓文章的虛實性受到關注。散文是不是該獨立成為一種獎項呢?若沒有文學獎,作者寫的文章是真是假,交給讀者判定就好,作者文責自負。
〔張維中作品〕




![華麗緣 散文集一.一九四○年代 [張愛玲典藏新版]](http://im2.book.com.tw/image/getImage?i=http://www.books.com.tw/img/001/046/62/001046621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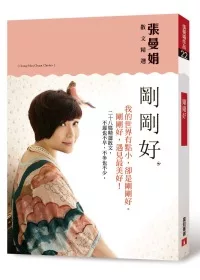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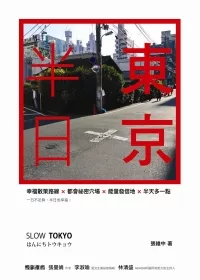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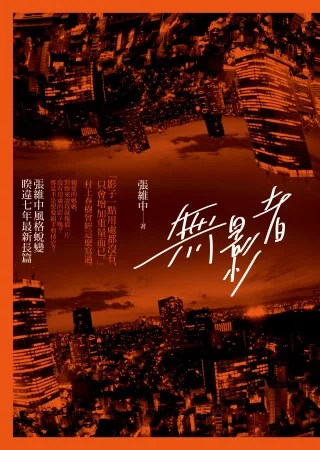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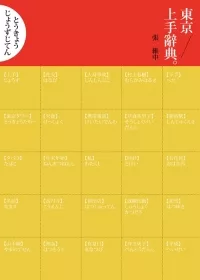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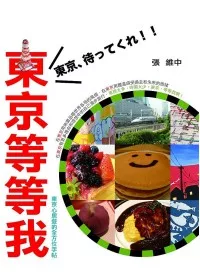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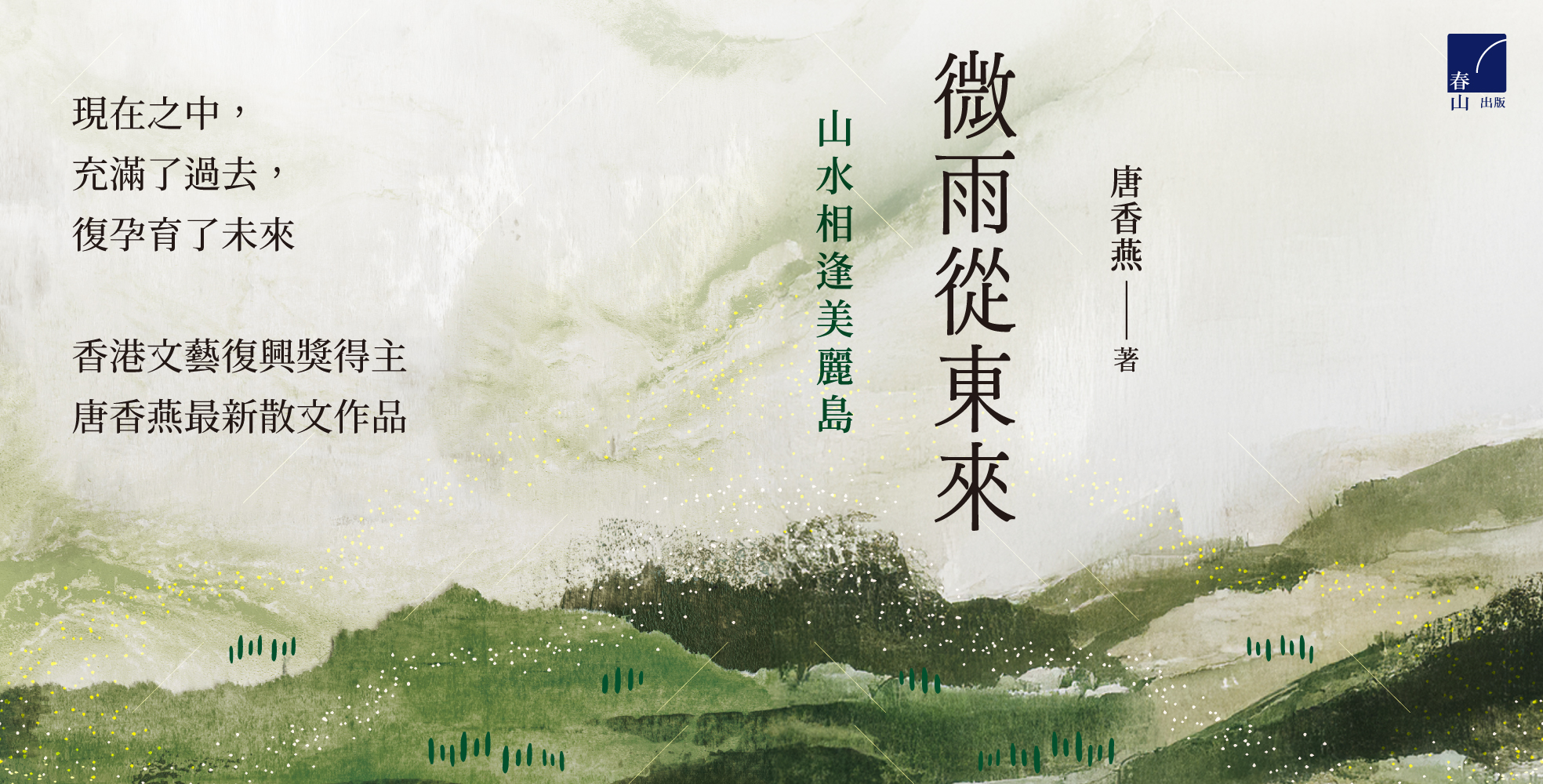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