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睽違七年,張贊波再次來到台灣,是為了宣傳剛上市的新書《大景:內蒙古「皇家」草原上的奇異風景與欲望遊戲》。張贊波從2018年夏天開始「潛伏」在內蒙古風景區,近身觀察以野狼為「道具」的網紅,穿刺光怪陸離的直播亂象。上下冊加起來共八十萬字,採訪前我迅速看完,得意地跟作者炫耀,我應該是全台灣第三個讀完這本書的人(前兩位是出版社總編、編輯)。
「不,你是第四個,前面還有富察,富察是第一個讀完的人。」
富察(原名李延賀)是八旗出版社總編輯,2014年八旗出版張贊波的第一本書《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以新人之姿連續得到開卷好書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將近十年後,富察終於等來張贊波的第二本書的書稿,2023年3月13日晚上,他和富察通了長達一小時的電話,討論出書計畫。幾天過後,3月19日富察回上海探親被帶走,杳無音訊,失蹤消息要到一個月後的4月20日才在社群媒體上爆開。張贊波看到先是張嘴大叫,接著一股惡寒湧來,全身如浸冰窖。
2023年春天,張贊波一腳踏入詩人艾略特的荒原,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五月也是,六月還是,七月仍是,八月繼續,恐懼完全吞噬他的心靈。台灣文化界300多人發起聯署聲援富察,身為八旗作者、往常大鳴大放的張贊波只能噤聲,為此他更痛恨自己,來到九月,富察被失蹤半年後,張贊波終於在臉書貼文,提到「最近幾個月,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時刻,我過得像一隻陰溝裡的老鼠,盡量把頭埋在陰暗之處,任由自己被悲憤、恐懼和恥辱吞沒。」
「說起這個我就很沉重,覺得好不容易出來了,見到大家是很高興的事,但背後卻是這樣的底色。」落地台北,來到面前的張贊波,眼神一如七年前的清澈透亮。《大景》後來由春山出版社接手,總編輯莊瑞琳從前是會和富察在辦公室抬槓的同業,兩人常辯論誰是中文圈最好的非虛構寫作者。《大景》因富察失蹤而難產,莊瑞琳接力助產,瓜熟落地,書籍自身曲折的命運,彷彿與跌宕起伏、極富戲劇性的內容相呼應。
《大景》原名「風景」,觀光風景區網紅直播的素材,張贊波原本要拿來拍電影,2017年11月來台,帶著「風景」參加金馬創投會議,第一次張贊波有了拍劇情片的念頭。劇情片不比紀錄片能單打獨鬥,需要資金,在台北除了參加創投會議,也和一些中國電影投資人喝咖啡,張贊波堅持「不要龍標(通過當局審查,在中國獲得放映資格的標誌)」,讓投資人紛紛打退堂鼓。
在台北找資金的同時,張贊波居住了快二十年的北京發生驅逐低端人口事件。張贊波立馬趕回北京,去往現場,卻發覺攝影器材很難拿出來了。再後來,他發覺只要待在北京,連手機都很難拿出來拍攝,即使公安城管不阻擋,也時有「熱心」民眾圍堵上來。張贊波想,是離開的時候了。
「一個人做主,興之所致,不拿別人一點錢,我在中國到處走,即興創作」;「比起在城市在北京,那裡地廣人稀,還是能找到一點點自由的感覺,雖然還是有國土局會擋我鏡頭,但相對寬鬆。」2018年夏天,張贊波因緣際會來到內蒙古草原,他先認識鳳凰馬場老闆彭闊,是草原觀光業的新霸主,彭闊介紹他認識當地最有名的網紅主播「養狼的姑娘柳靜」,柳靜在中國直播平台「快手」上有將近兩百萬粉絲,她的男友鄭總自稱是捧紅柳靜的人,山東人,《大景》第一男主角出場。張贊波化名張贊,是來自北京的紀錄片導演,一開始鄭總對他十分熱絡,柳靜則從頭到尾保持冷漠,後來張贊波對他們的印象產生反轉,「鄭總是我最討厭的拍攝對象,以前我從來沒遇過這麼討厭的人。」張贊波偶爾要幫忙掌鏡,當鄭總的直播幫手,鄭總被狼群撲倒在地上,下標:「被群狼非禮的男人」,哭笑不得的張贊波在書裡寫:「我做為一名攝影師,在直播宇宙的首秀作品,竟然有著一個這麼令人難以啟齒的名字。」

紀錄片的累積時間非常漫長,張贊波一拍就是三年五年十年,這次他將鏡頭對準中國抖音、快手十分鐘以內的短影片,極緩慢與最快速,拍攝者與被攝者處在光譜的兩個極端。張贊波追蹤很多底層的直播主,有卡車司機,還有開靈車的司機,發覺抖音、快手是做社會調查的利器,「北京的知識圈看不起這些土味視頻,我還力挺它,我說直播就是獨立紀錄精神最好的載體,它比紀錄片更強。我採集的素材要經過編輯,很漫長才能傳達出來,直播同時就能做到。打破話語權,現在一個最底層的人也能做到。」
「當然他們後來為了流量去做很極端的事情,所以我說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在中國就是這樣。」鄭總隨身攜帶四隻手機,無時無刻不沉浸在直播宇宙中,直播中的鄭總熱心公益、關愛動物,濾鏡外的鄭總冷酷無情、剝削員工,PUA女友讓她墮胎,對妻兒不理不睬。鄭總對動物尤其殘忍,用來漲粉的狼不停死去,像免洗筷一樣用過則丟。《大景》充滿被污辱與被損害的人還有動物,被強迫放倒的馬、殘忍割角的鹿、吃生蛆腐肉在冰天雪地裡毫無遮蔽的狼……凡此種種都能成為衝流量的鮮活素材。「我和鄭總吵過幾架,甚至吵過一大架,後來死了那麼多狼,他又不打疫苗。我就受不了了。……他說他千萬身價,其實根本都沒錢,是可憐人,這種人在中國特別多,一方面他是大環境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他又去加害比他更弱小的人或動物。」
十年前的《大路》是底層和體制,雞蛋與高牆之間的碰撞,十年後的《大景》是雞蛋與雞蛋之間的碰撞,張贊波說:「底層互害,更讓人難受」,「這本書看起來說的是網紅、觀光經濟,其實最核心的是底層和權力之間的同構性,他們其實是一樣的。在《大路》時期,在底層和公權力的對抗,雞蛋和石頭之間,我肯定是站在弱者這邊。到了《大景》我不像以前對底層完全敞開心扉,覺得他們僅僅只是受害者。我現在會更複雜地去看,在這本書裡我對底層的批判肯定超過《大路》。」
在內蒙古,張贊波唯一一次拿起攝影機,對準公權力的強制拆遷,石頭輾壓雞蛋的場景,後來他發現那其實是一場「戲」。「部分」拆遷只是做做樣子,沒有取得經營許可證的景區,不惜花大筆錢去通關打點,積欠民工幾千塊的薪資卻遲遲不發。諷刺的是被嚴重欠薪的工人,老闆手一招又回去工作,因為他覺得待久了老闆就會掏出錢來。

被鄭總請來養狼的老朱,是張贊波在書中少數有感情的人物。老朱說了一個從前在工地發生的故事,有個工人從高處摔下來,工頭老朱先帶他去市區的醫院,一拍片發現腳後跟粉碎性骨折,老闆說趕快把他從醫院弄出來,以免花大錢。老朱接著帶工人去市郊的醫院,治療費用帶押金要先繳兩萬四,老闆說還是太貴了,趕快把他弄出來吧。工人經過轉院的折騰腳腫得更大了,老朱對他說:「你自己琢磨,要是你要堅持在這裡不走,老闆也拿你沒輒。」工人逆來順受地說:「老闆說讓我出來就出來吧。」最後工人被帶去更偏遠的城郊整骨所,蒙古大夫捏一捏,說不用開刀,上石膏就好。
被剝削被踐踏卻依然同理強權的「弱者」充斥《大景》書中,鄭總和女友柳靜鬧翻後,聘請東北人月兒當他的直播徒弟,月兒剛在東北生下孩子,為了賺奶粉錢來到遙遠的內蒙古草原。草原的鐵絲網內,狼媽媽也剛生下小狼,鄭總卻將狼母子強制隔離開來,只是為了要讓小狼更親人一點,好利於拍攝。狼媽媽在鐵絲網的另一邊看見小狼格外激動,母狼剛生產完體力耗盡又面對其他狼的挑釁而傷痕累累,也剛成為媽媽的徒弟月兒,對這一切無動於衷。一股冷漠麻木的悲哀力透紙背,張贊波說:「書中有一章叫〈動物樂園〉,那簡直是地獄!」


我問:「記錄這些殘忍的現實,會有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嗎?」
張贊波恍然大悟,原來自己近一兩年的「症狀」就是PTSD,「我現在連出門都不願意,我受傷很嚴重,已經開始厭惡人了,我都不願意出門買菜,我完全用網購,只要一接觸人,那真的是一片惡土。」
「如果需要再去做田野調查進行非虛構寫作,我不願意了,我的PTSD已經來到頂點,其實我原本很堅強、百無禁忌,包括很多痛苦的場面,死亡我都見過了,但這次我真的是厭倦了。我不想再做這種非虛構寫作,我想去寫小說,因為那不需要再去跟人發生關係。」
「那些人都是受害者,但另一方面他們更可惡要去欺負更弱的人,包括《大路》裡的老何。我對老何有一種深切的感情,從他58歲開始拍到今年他72歲,我常去找他,我們持續保持聯繫。有一次來台灣去聽音樂節,音樂一出來,我就馬上想到老何的一生,我都哭了。」
老何是來自四川的挖樁人,建造公路雖可引進大型機具鑿地挖樁,但人工樁便宜許多,挖樁人是工程的最底層,層層轉包出去,低薪過勞且充滿危險。張贊波在《大路》裡這麼形容老何:「在這個充滿了不公平的生態裡,對這個微小如芥子般的小人物,你反而會讚賞他的智慧和生命態度。」也時常反省自己對老何的成見:「那本來就是一個『局部』的老何……他勤勞、堅韌、熱情、樂觀、開朗……至於所謂的『忘本』,也許是艱難的生存困境所逼迫出來的一種本能反應。」2024年的老何卻讓張贊波再也無法忍受,老何給他的PTSD尤甚於《大景》中的鄭總,「上次我去找他,感覺我跟他的關係已經到頭了,完全不能忍受那個底線。」
老何老朱老鄭……這些張贊波從前能同理,來自底層的小人物,通常是被洗腦得厲害的堅定「愛國者」甚至「小粉紅」。張贊波說:「有兩個網路新詞專指這類人:一個是『地命海心』──吃地溝油的命,卻操著中南海的心;另一個是『韭命鐮心』──韭菜的命,卻替鐮刀操著心。」2019年8月,中國官方宣布暫停中國影片報名金馬獎,張贊波忍不住在臉書發文批判「可恥的電影局,狗急跳牆的節奏。遺憾今年沒有新片出來,要不我一定報名金馬。歷史定會記住你們所做的一切。」這則貼文隨即被搬運回「牆內」,在一些愛國網紅的鼓動下,引發大規模的討伐與隨之而來的網暴。
張贊波一一點進他們的頭像裡頭看,網暴他的正是他長年拍攝的民工、快遞員、建築工、北京被清除的低端人口,底層的面孔像兩頭蛇反噬回來,張牙舞爪喊著要殺他全家,「這件事讓我受傷也很深,對底層觀念的改變。那陣子我其實很恍惚,走到大街上尤其我經常坐公交車、地鐵會看到底層民工,我就會想這些人裡面有沒有要打斷我的腿,強姦我家女人的。這麼多年我完全是站在底層那邊,到頭來他們卻跟強權共情。」
從來不附屬於任何團體與組織,總是潛伏於民間拍片的張贊波,在這一波猛烈的網暴中彷彿被X光照得透徹。親朋好友側目,老家的村委會說副鎮長要找他說話。湖南地方性的自媒體紛紛「起底」張贊波的老家,說他是敗類、叛徒。張贊波還記得,十年前他拍《大路朝天》紀錄片入圍幾個國際影展,吸引《鳳凰網》來報導,同樣是這些人說他是家鄉的光榮。
張贊波的照片像殺人犯一般全網流傳,遠在內蒙古的鄭總也得知那個跟前跟後拍攝的「張導」原來拍的都是一些「負能量的東西」,無益於正面宣傳與行銷,鄭總自此與張贊劃清界線,不再往來。鄭總午夜夢迴時或許會回想起,原來「維權」是張贊擅長的事,他總是在拍維權嘛!張贊波曾幫忙鄭總維權,鄭總無意間發現有一則點擊率超過八百萬的狼影片盜取自他的影片。偷他影片的是中國軍網,來自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官方快手帳號,標題是「新疆軍區邊防某部官兵在夜間值勤途中遭遇狼群……」
影片中的狼群並非新疆的野生狼,而是內蒙古的圈養狼。鄭總無意間拍來衝流量的「午夜幽靈」狼系列,被移花接木之後,成了新疆維穩工具,軍人鎮守邊疆夜半遭受野狼威脅,看了影片之後深感軍人好棒棒的「地命海心」「韭命鐮心」,沒有一個人去問,新疆為什麼需要這麼多軍警?張贊波說:「在中國就是這樣,看起來很微小的事情都能關聯到最堅硬的部分。」
即使是最討厭的拍攝對像,張贊波都願意教他怎麼維權。經歷過中國新公民運動的時代洗禮,張贊波詳記法條,理直不屈,十分嫻熟怎麼維權。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地鐵都要過安檢,如果有隨身帶水,必須喝一口水才能通過。張贊波通過安檢堅持不喝一口水,堅持十年,為此還寫過一篇文章〈我喜歡喝水,但我不喜歡你強迫我喝水〉。2023年張贊波到鄭州去玩,經過富士康大門外時臨時起意拍攝工人下班場景,結果遭到阻攔,被帶到當地警局問話,要求刪掉拍攝素材,為此被扣留在警局一段時間。「要是往常我立馬就去鄭州市公安局上訪,不受理我就去公安廳,我走的都是他們的程序喔,河南省公安廳不行,我就又會往上一層去北京公安部,我沒犯任何一條法律,憑什麼扣留我?以往我就會耗著跟他們較勁。」
「以往」張贊波總是較勁,近幾年他不維權也不較勁了,「現在要我刪我就刪,就一個鏡頭,和他糾纏會很麻煩。」「以前我據理力爭是因為我覺得是有用的,這會促進社會改善。後來放棄了,這只會消耗我,因為我還想做事。我現在能脫身就脫身,完全不想糾纏。」
張贊波在《大景》第一次透露自身的軟弱。第一是2009年的作品《天降》,拍攝火箭殘骸砸落造成平民死傷,接到軍方電話後,張贊波曾阻止媒體繼續報導。第二是2016年《大路》在中國出了簡體版,書本暢銷馬上再版,但隨即成了禁書。編輯要他不要將這件事對外張揚,這違反張贊波一貫的大聲「維權」原則,但為了編輯口中出版集團一千多人的飯碗,張贊波妥協了。他在書裡寫「透過犧牲自由和權益、透過妥協和退讓換來的平安,並非真正的、永久的平安。」最終出版社仍因種種因素遭到整肅,負責《大路》的編輯被吊銷編輯資格,終生禁止進入出版行業。

來到台灣第三天,張贊波就去電影院看了他一直很想看的婁燁新片《一部未完成的電影》。看完電影他紅著眼眶,卻說對這部拍中國疫情封控的片很失望。隔天他在新書座談再度提到這部片:「對於經歷過巨大苦難的當事人,這部片輕飄飄的,對體制的批判不夠。」上海封城的那幾個月張贊波搬到山裡,仍關注網路訊息,徹夜難眠,「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如果那些被封控的人,從來沒有為自己或他人維權過,那麼我要說:活該!」「以前我會為了一點小事打官司起訴,我的公民意識被其他人當成神經病,像我這樣的人如果多一點,凡事都要較勁,就不會走到這一天。」
這一天的來臨,是被剝削的,被欠薪的,被壓迫的,並不起而反抗,而是「無差別殺人事件」遍地開花,近期就有開車衝進運動場輾壓(廣東珠海,35人死亡)、沒有拿到實習工資的大學生在宿舍裡砍殺(江蘇無錫,8人死亡)。在中國網路上一度被稱為「張獻忠現象」,張獻忠是明朝末年的叛軍首領,曾殘忍屠城,是無理性「暴行」的代名詞。
「我感覺更壞的還沒有來臨,真的會全面崩塌,還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現在自殺的也特別多,跳樓、跳河,只要有橋的地方每天都有人跳,以前沒有那麼頻繁。」
世道艱險若此,有沒有「潤」(離開中國)的打算?
「我們這個圈很多人都出去了,在疫情之前就走了一大批,那時候我都說我不出去,我要待在這裡。疫情之後卻也想過是否要走,但後來覺得還是要留下,尤其感覺百年未有之變局真正要來了,對於一個關注現實的創作者,這個時候不能缺席,更需要在現場。」
在「大變局」下,拿出攝影機或者手機出來拍攝是越來越困難了,張贊波只得坦然面對自己的局限性,他說沒法拍了,他還可以寫,把所見所聞都記錄下來。他很多年前就提倡「多聲部創作」,運用文字、影像還有行動藝術等多種手段或媒介表現關注的主題。疫情期間他做了行動藝術作品〈春山來客〉和〈春行即景〉,從淘寶買來全套防護服裝備成「大白」(疫情防護人員),進到人煙稀少的山裡宣講「動態清零」政策,並在自己租住的山居前架設一個「全世界最小的疫情檢測站」,懸掛寫著「新冠疫情不可怕 只要大家聽黨話」的橫幅,假日來山裡郊遊踏青的人們都乖乖前來做檢測,沒有人察覺到這荒山野嶺的荒謬設置。
「我能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而且還能掌握一點媒介,擁有一點技能,百年未有之變局來了,所有人都去迴避它,總要留下一些什麼吧,這是我比較自大一點的使命感。」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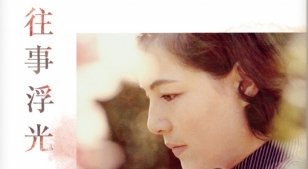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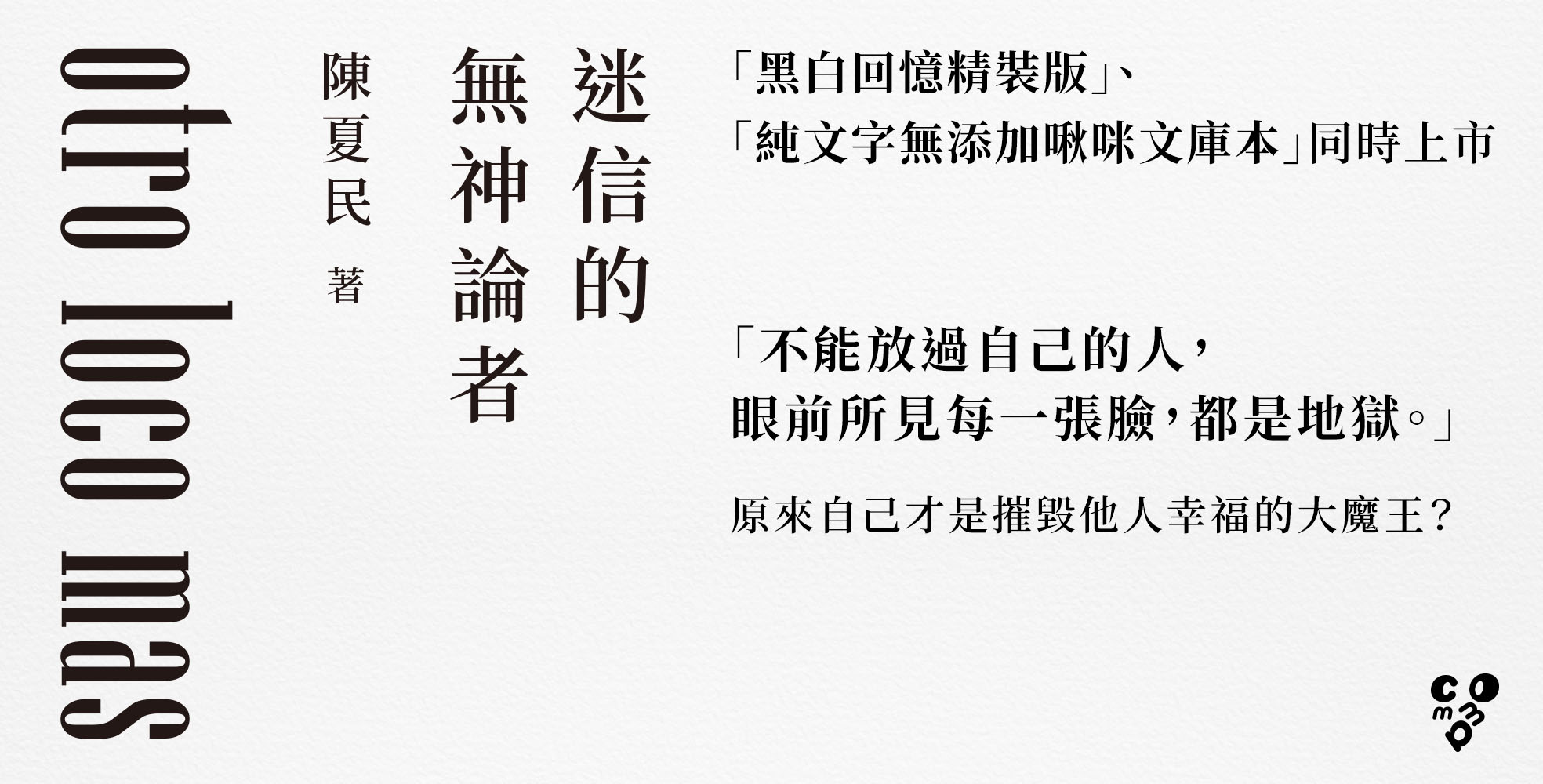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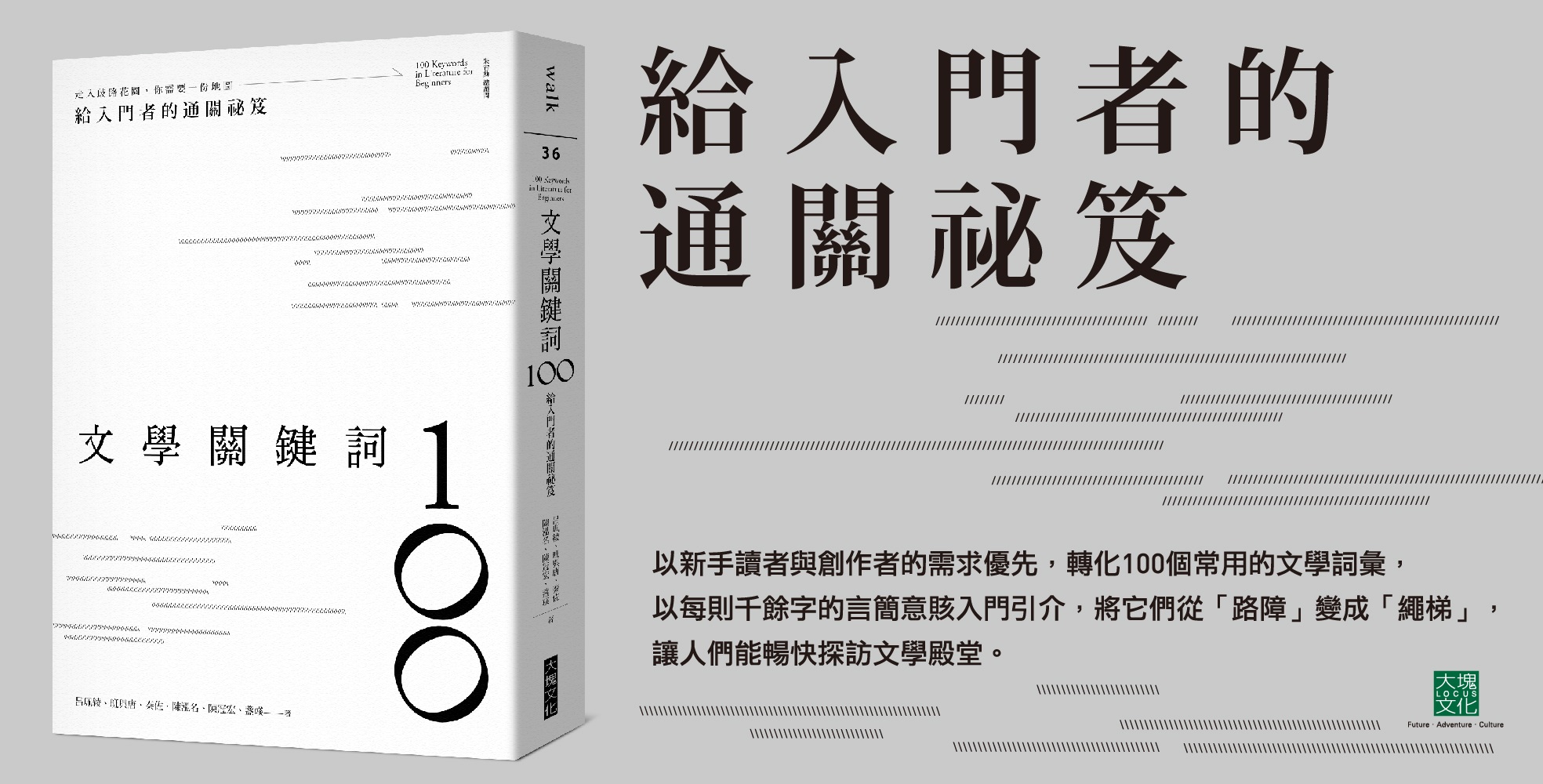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