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如果說1996年朱天心〈古都〉是透過私我記憶的戲劇化與抒情化,在公眾記憶中布下疑陣,那麼李佳穎《進烤箱的好日子》則選擇了另一個極端:「難道,我的記憶——最私密、最無涉宏旨的那種,都不算數?」小說家於是說:
「既然如此,那就來寫一本回憶錄。」類似《進烤箱的好日子》主角「阿丹」。有天,她的小說寫不下去,轉而改寫一本前青春期的回憶錄。這位嚴守寫作倫理的創作者,認為回憶錄必須是真實的,所以一面寫一面去找被她寫的人,核對其依據記憶所寫出的內容。因此,儘管《進烤箱的好日子》故事非常簡單,卻有著複雜近乎互搏的結構:一線是當下此刻阿丹的敘說,一線是阿丹書寫的過去;兩線不時既干擾又補完,卻因磕絆而綿長。
就在這看似跌撞只能自己扶持自己的故事裡,阿丹為我們盤點一眾文學名家的小說學養,也重述了一遍她的前半生。引援自普拉絲頭進烤箱自盡的典故,因而翻轉出新意:寫作是叫停時間,也是斷尾求生。
所謂謀殺與創造之時。
但阿丹的書寫,不只是為了創造,更是為了連結——連結散沙的友情,連結離異的父母,連結過去的自己。但不是說書寫過去是斷尾嗎?《進烤箱的好日子》最有趣的張力也在此,阿丹進烤箱是一種薛丁格,是死也是生。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於是乎,書寫成為永動。
▌一樣進烤箱的《贖罪》與《免責聲明》
書寫存在一種永動的張力,關乎李佳穎對寫作是一種捕捉無法捕捉之物的看法。在《進烤箱的好日子》裡,我們可見得她以波赫士的地圖寓言為例,說出:「你變成蜘蛛,變成毛蟲,想像死亡,變成神,俯瞰自己,終於明白人的凝視可貴在它的局限,如同你的地圖。」以及,「這些時刻在沒有記錄下來之前是人,寫出來之後就變成屍體了。」或者,一開始阿丹喊出,那句響亮的:「真實未免也太囉唆了!」
對照李佳穎於2008年《小碎肉末》後記的娃娃屋比喻,我們也會發現,她對小說的詮釋,這十多年來並未特別飄移:「那些地方,那些罅隙,只有在東西擺對位置的時候才會出現;只有在灰姑娘一天的苦難結束,躲進去哭泣的時候,才會發亮;只有在不問灰姑娘家裡怎麼可能出現抽水馬桶時,才會看見。」
書寫的意義,是試圖抓住轉瞬之物的「試圖」,只有在我們賦予意義時存焉——當灰姑娘「想」躲進去哭泣,或我們「反諷的意識到」灰姑娘的窘境。可以說,李佳穎對寫作(或說寫作賴以為生的語言)一直抱持著非先驗的思考,在她終於將這思考發為小說時,反倒畢現了文字的力量。
類似案例,也如伊恩・麥克尤恩的《贖罪》。小說描述主人翁白昂妮一生都在為幼時撒的謊「贖罪」——透過講述一個不存於現實的現實版本。然而,或許是因為2007年喬・萊特改編的電影版本太成功,讓小說最後的辯證失卻,讀者以為白昂妮的寫作「等於」贖罪,是輕易洗白自己。其實不然。
小說尾聲,白昂妮說道:「這五十九年來的問題在這兒:一名小說家,她有絕對的權力來決定結局,她同時也是上帝,那麼她要如何贖罪?她無法求助於任何人、任何實體、任何更崇高的力量,沒有人能幫她調解,也沒有人能原諒她。」白昂妮知道,在她創造的小說裡,她就是上帝,其上無他。她的寫作,在明知不可能被原諒的情形下持續了五十九年,近乎苦刑。也正是知道自己不可被原諒,書寫才有意義,才是「贖」罪本身。如同阿丹,明白自己無法窮盡真實,書寫才有了近乎悖論的力道。
若說《贖罪》以無法原諒為核心悖論,近期改編成影集的《免責聲明》就是反例。這是一部藉由小說主角誤認真相可被敘事贖回,來進行道德教訓的故事。然而,作者沉溺於小說的道德,試圖讓虛構為道德提供補償,未於形式上用力,因此削弱了力道。可並觀的,則是艾方索的改編。他選擇從形式下手,不但一開始就告訴觀眾:「小心敘事跟形式。」還調動了四個敘事聲音,讓這部稍顯俗濫的故事顯得嶙峋,但也更具警惕。
 免責聲明
免責聲明
回到《進烤箱的好日子》,博學如阿丹,其實也向我們展示了說故事的悖論。那是她所援引,看似與主線無關的兩個童話(或鬼故事,畢竟她讀的版本,很可能來自世一文化出版的《靈異怪談系列1:世界恐怖故事》一書):〈牛角上的主人〉與〈藍鬍子〉。
阿丹發現〈藍鬍子〉這個故事存在蹊蹺,因此認為結局應該會是更平淡也更恐怖的「她假裝沒事般等待藍鬍子回家,在心底哭泣著/一切像平常一樣」。至於〈牛角上的主人〉,阿丹為我們拆解了這故事其實是透過語言的不斷延異——推遲真正的主人——才建立,「要能欣賞『人老到可以住進牛角掛在牆上』這麽華麗的畫面是需要準備的,需要七個老到哭爸的人拉開助跑道才行。」這兩個「鬼故事」透露了,阿丹其實十分掌握故事的成立:現實是不戲劇化的,與敘述作為一種添加物。
▌把寫作擺低縮小一點,更有力量?
循此來看,阿丹的寫作不只是為了想記下些什麼。另一個側面印證的線索,是阿丹在十六歲時把十一本筆記本燒掉了。曾經記錄又毀棄的她,重來了一次。這時,她或許有足夠智慧,深諳寫作不可能百分之百記下,寫一寫也可能變鬼故事——這兩者的反例,就是〈古都〉。
因此,「進烤箱」也是為了真實的、物理性的連結。一個有趣的點,是阿丹一開始就透過昭示寫作意圖來迴避寫作意圖:「我第一次覺得,乾脆來寫回憶錄,是在我對小說的虛構性產生越來越多問題的時候。」但我們可以繼續追問:阿丹為何要寫回憶錄呢?
其後,阿丹遇到父母、友人詢問為何寫回憶錄,始終未正面回答。其寫作之路夥伴周可儀也問:「如果我說不可以(讓你繼續寫)那你要怎麼辦?」阿丹的回應是:「那大概就是用一些方法搞混時間跟名字讓你沒辦法告我吧哈哈哈哈。」並自忖:「周可儀說得很有道理。也許這一切我自以為是的回憶錄寫作法底下有某種我還沒參透的深層結構在支撐。」
恪守寫作倫理,飽讀文學名家(寫作論)如阿丹,被還沒參透的深層結構推著跑,明明可以不管那些人,卻花大把時間邀請他們參與回憶錄。背後原因有沒有可能是她明知而不說?或那個道理太簡單了,以致於被忘記、不想說:
不過是想找機會碰一碰只會在臉書互戳、相互偷菜的失聯朋友(由此可知,小說裡大概是2010年左右的時空),已經疏遠的父母,並在這付諸行動的過程中,主掌那個曾以為被拋棄、被排擠、被輕薄的自己——那麼多個「被」,那麼客體的自己。
那麼寫作真的有力量嗎?卻除結局,小說裡,阿丹遭遇何維光不懷好意的詢問月事的回應,是最顯著的例子。阿丹透過一次四歲時的性侵經驗,意識到何維光意在占她便宜,心中響起「被騙了!」的警鈴,同時調動記憶裡母親的月事經驗——裙子紅了,是水彩、桑椹、紅糟在搞鬼(這個敘事其實很像〈牛角上的主人〉),搪塞何維光。這段最有意思的是,阿丹在她講求真實的回憶錄裡,記錄了一個謊;而這謊言的達成,暫時迴旋掉現實的成功,又來自她對四歲記憶的檢驗,以及她對敘事的掌握。
但別忘了,阿丹我手寫我口之餘,也真的動起來,在現實中重新找回人的連結。最終,《進烤箱的好日子》成為不那麼雞湯,試圖以一己之力重振寫作的作品,並且,讓習慣認為文字很權威的我們鬆一下,把書寫從緊挨記憶與大敘事中鬆脫開來。如阿丹告訴我們的:「任何熬過童年的人都有足夠支撐他後半輩子的人生素材。」讀完這本小說,最好的致意,是拿起筆或打開電腦、手機,對自己說說:今天過得怎樣?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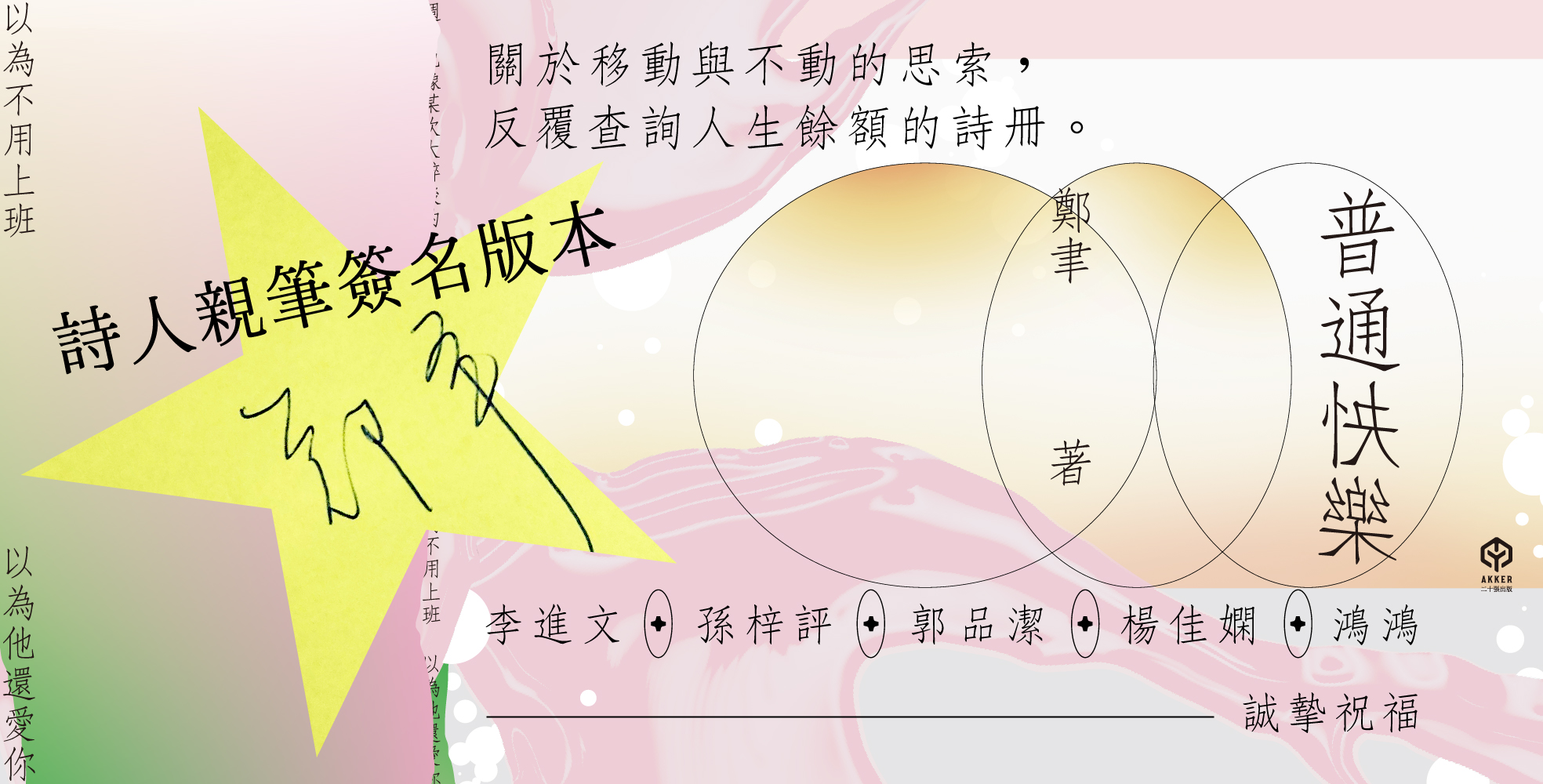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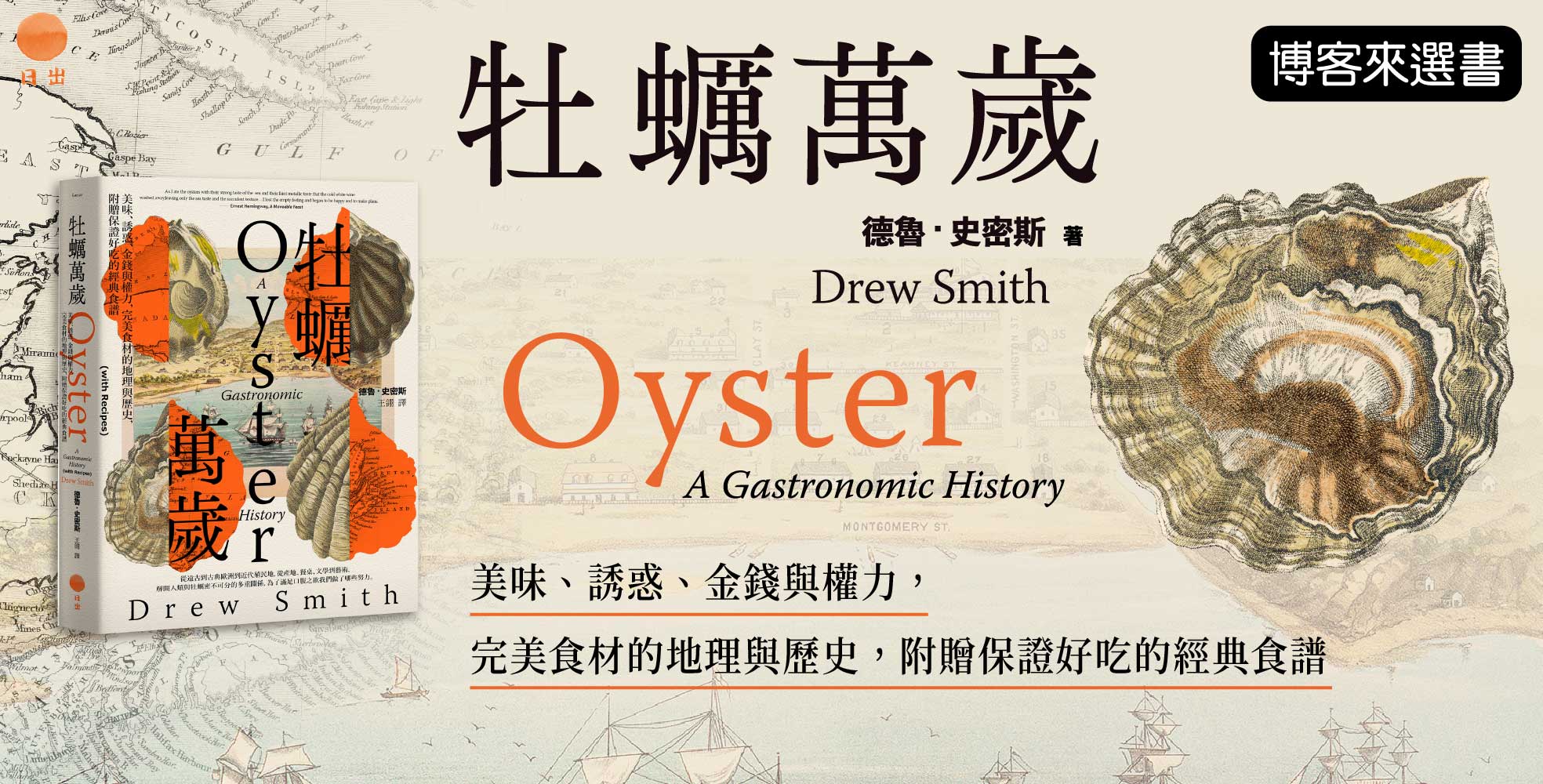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