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瑞在女書店以「美術館裡的生化威脅」為題演講。(照片提供/紀大偉副教授)
我第一次遇見韓瑞(Ari Heinrich)教授,是在2019年春天。我在當時他任教的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系課堂上作了簡短的報告。那時是我研究生涯的最初幾次英文報告,緊張萬分,手足無措,不曉得在場師生會怎麼評價我這個從遙遠的台灣飛來的短期訪問學生。
韓瑞教授面帶微笑聽完報告,引導同學發問,然後在下課之後跟我說:「謝謝你為我的課堂帶來獨特的觀點。」
再次見到他,是2024年11月,韓瑞教授來到台灣。這次來訪,他帶來兩場演講,一場在女書店,一場在政大。在政大的演講是由他和政大台文所紀大偉老師對談「從英譯台灣文學贖回『跨性別』」,主要談論韓瑞教授英譯的兩本台灣跨性別文本: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以及紀大偉的《膜》。在對談開始前,紀老師的課堂學生上台報告《膜》;而後對談開始,韓瑞教授的開場白,是感謝那位上台報告的學生並給予回饋。
時隔五年,韓瑞教授仍然如當年鼓勵我一般,親切而誠懇地鼓勵每一個來到他面前的學生。
在面對要翻譯的作品時,韓瑞老師也是真心相待。對談一開始,紀老師就拋出靈魂拷問:大家都知道翻譯對學者而言是額外工作,韓瑞老師大可只顧自己寫邱妙津的論文(有利學術生涯),為什麼要翻譯邱妙津(不直接有利學術生涯)?
韓瑞老師坦言,最初,他的確猶豫過,邱妙津的書這麼難又沉重,恐怕沒有讀者。但是,「翻譯一部作品,你必須找一個真正打動你的。如果這部作品打動你,它一定能打動其他人。你得相信這件事。」這種「動之以情」的原因並不只是勵志的話語,也有實際效用。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彷彿跟作品和作者關在一間牢房裡面面相覷。要這麼長時間近距離的密集相處,如果不是跟自己喜歡的人事物在一起,會非常辛苦。
另外,辛苦並不會在翻譯結束就結束。韓瑞老師提到,進到出版環節、和編輯討論及校對,思考怎麼將語言調整到會讓讀者喜歡這部作品,都是重重考驗。「美國市場看似很大,但其實對於翻譯文學的需求並不成等比。而且美國市場非常商業導向,出版一本書,所有考量都是能否賺錢、能賺多少。」這時,在美國書市上較小眾的翻譯文學,就成了難以舉起的敲門磚。譯者在此過程,必須不斷在尋找人脈、說服出版社、制定翻譯策略等等過程耗神費力。
在推廣邱妙津作品時,社群媒體也成為一大變因。紀老師提到,在英譯文學中,白先勇的作品雖說是台灣同志文學代表作,但較少有能夠吸引外國讀者「貼標籤」(hashtag)的議題點,所以在社群媒體上較無引發討論。相反地,邱妙津作品似乎因為「跨性別」、「台灣女性作家」等當下受討論的標籤,特別被演算法青睞。韓瑞老師補充,邱妙津創作的年代,還沒有現在這些身分政治的標籤,且從跨性別的角度理解她的作品,也是相當近期的事情。他認為邱妙津如果還在世也許不會同意這些標籤,但有趣的是,她的作品提供了能夠用這些角度理解的可能。「身為跨性別者,你會非常渴望找到能代表自己的作品。邱妙津寫出了那種『拒絕分類』的曖昧狀態。所以我們才能以後見之明的方式說她的作品是跨性別文學。」
但是,跨性別標籤可以被後見之明的貼上——或如講座主題所謂的「贖回」——卻不能成為閱讀作品的唯一索引。「如果只用跨性別視角來讀《蒙馬特遺書》,大概會很讓人失望。對我來說,跨性別只是敘事者的一部分;敘事者的命題是抵抗:他想自由探索而不被擊倒。」
反思跨性別標籤也是重新探索身分政治中幽微地帶。韓瑞教授提到,跨性別這個詞彙意味著從一個性別到另一個性別,好像從一個明確的地方去到另一個明確的地方;但他個人的性別轉換經驗並不完全相符,「我總覺得,自己是從一個不確定的狀態,進到另一個不確定的狀態。」
被「抗拒分類」的作品和作家、藝術家吸引,似乎是韓瑞老師的美學視野。在女書店的演講「美術館裡的生化威脅」中,韓瑞老師向大家介紹自己最近投入跨性別藝術家范加(Jes Fan)的生物藝術作品研究。韓瑞老師說到,儘管范加是跨性別者和酷兒,但這些身分不會成為他作品的唯一面向。「在面對各種身分分類時,每個人都很害怕惹到不同陣營的人,但是范加似乎毫不畏懼爭議也勇於對抗爭議。這是我非常欣賞范加的地方。」
范加是生於加拿大的藝術家,在香港長大,近期居住在紐約。在大學時期就讀羅德島藝術學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並擁有玻璃工藝的藝術學士。他的作品時常以體液、生化元素為玻璃作品的上色材料。例如韓瑞老師介紹范加在雪梨雙年展中展出的「行事為功能之父」(Forms Beget Function),即是以尿液、睪固酮、黑色素為原本透明的玻璃填上仿若金屬色與黑色斑紋的色澤。
透過將生化元素放在人體之外的藝術作品上,范加的作品拆解了自然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尿液、睪固酮、黑色素這些本身不具任何社會意義的液體和分子,在被人類「發現」之後就被「發明」出某些社會意義。例如黑色素是所有生物皆有的生物色素,但卻因為黑色素影響了人的毛髮與皮膚顏色,而成為特定種族的象徵。
韓瑞老師解釋,就像是睪固酮和黃體素是每一個人身上都有的,但是這些生物元素會被人類社會歸類為「男性賀爾蒙」和「女性賀爾蒙」。如同《睪固酮藥癮》所揭示的,沒有任何性別意涵的生化元素被人類社會賦予性別特徵,進而成為規範「性別正常樣態」的科學化/自然化指標。而一旦這些社會意義被科學化/自然化,「正常」性別樣態就成為一種「天生如此」的本質化規範。這也正是今年「林郁婷事件」所引發的討論——任何性別、任何種族,真的有可以被標準化的生物元素嗎?
在兩場演講活動之外,我在韓瑞教授訪台期間另外找時間請教他,這趟來台灣談雪梨雙年展和范加,和台灣的關係是什麼?韓瑞教授說,范加的酷兒實踐和多重的族裔背景,或許可以讓台灣人在思考國族身分定位時有更流動、寬廣的空間,容許更多無可名狀的曖昧性,且不急於貼標籤。而雪梨雙年展的策展人Brook Andrew肯認澳洲當代美術館就蓋在原住民的土地上,這件事也許也能讓台灣的策展與藝術圈參考:台灣的各大美術館蓋在誰的土地上,而這個土地上又經歷過多少層的殖民歷史?或許當台灣殖民歷史被更多元、更多層的拆解,我們也將能找到更多理解「台灣作為酷兒」的途徑。
在和韓瑞教授道別時,我謝謝他曾經給我的許多鼓勵和支持。他溫和笑說沒什麼,「我還記得你2019年的報告,那非常獨特又有啟發性。」我羞愧地說其實我只記得自己多麽擔心當時表現很差。他搖搖頭,留下一句話給我:「Be kind to yourself。」
五年後,當我不再是那個緊張慌亂的報告者,而有機會在韓瑞老師的演講行程之外訪談他時,我才明白他面對人、對文學、藝術與學術的誠懇與耐心,一直始終如一。我記著韓瑞老師的話,等待下一次見面,能夠交出更多成績與他分享。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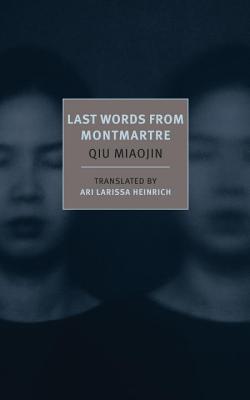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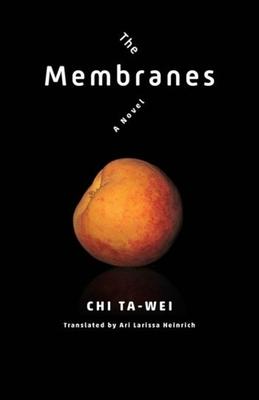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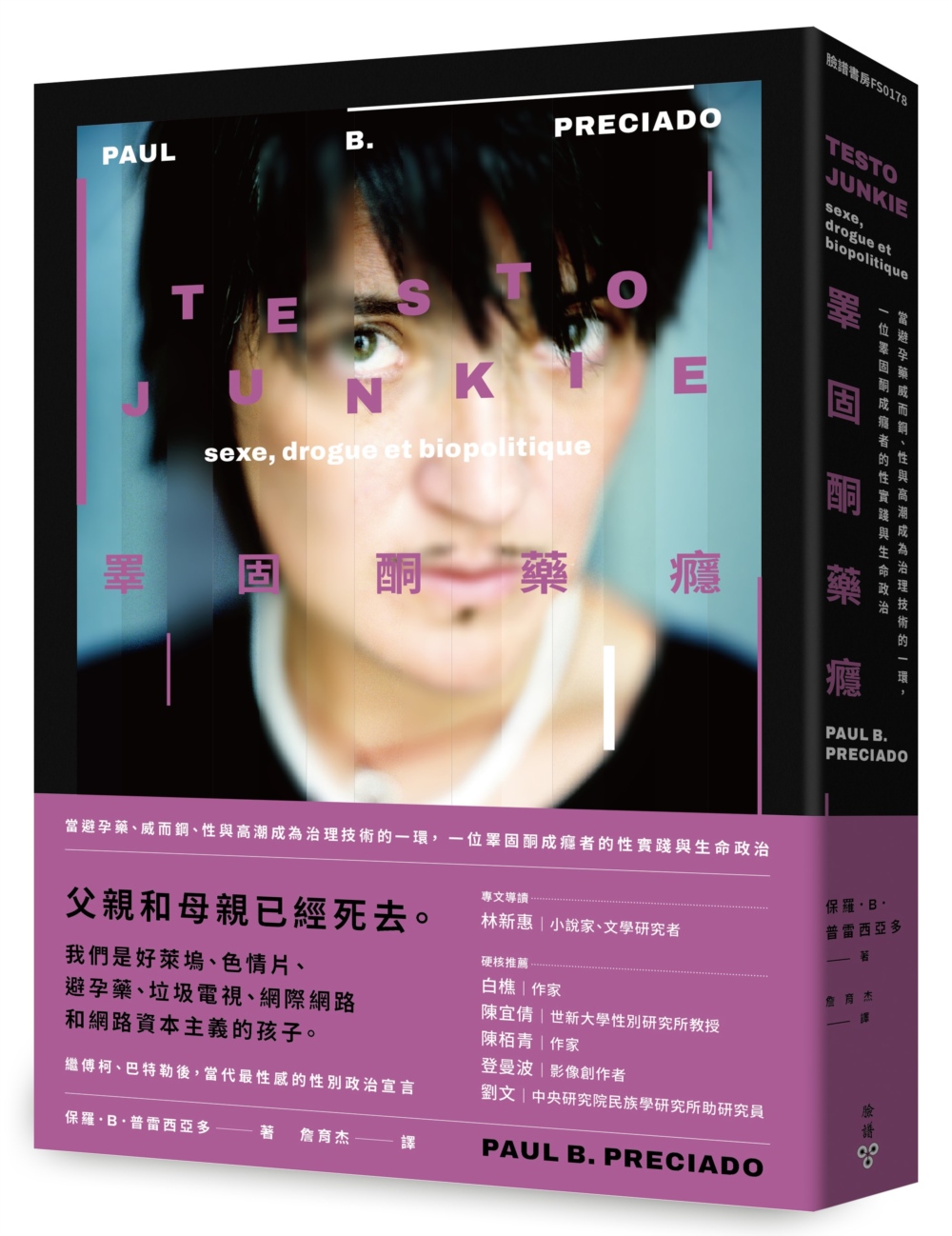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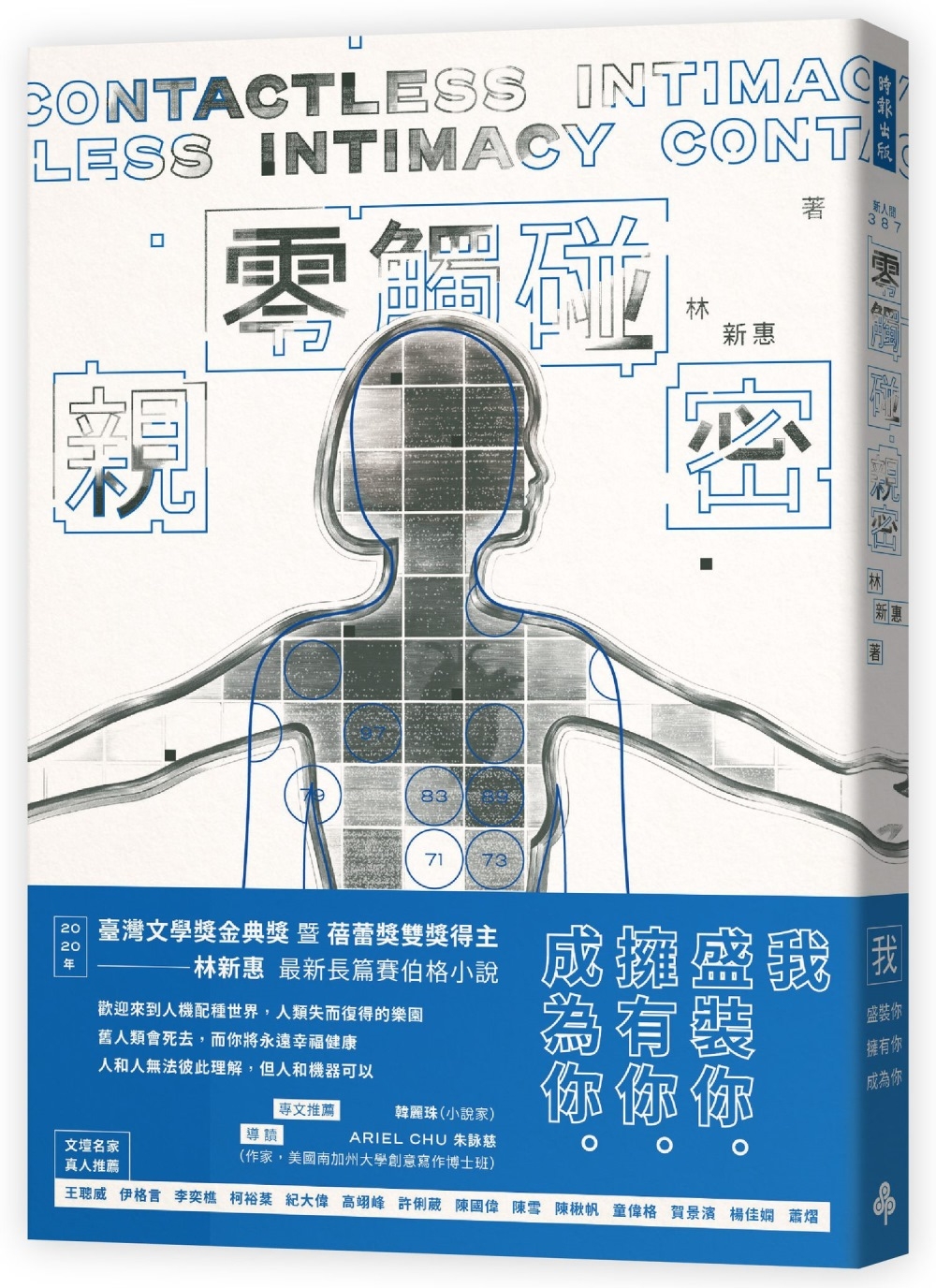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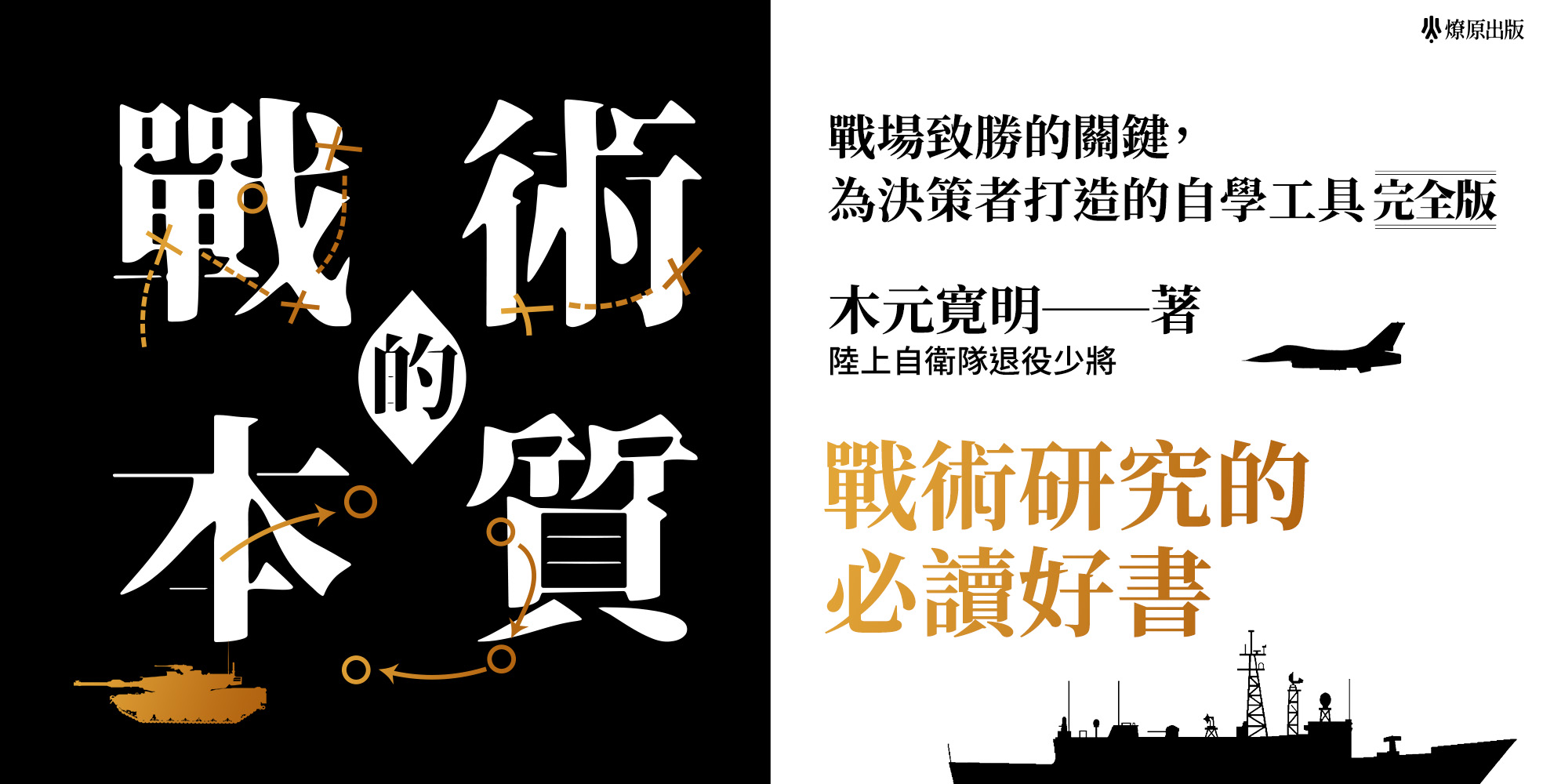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