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大逃殺》的人,應該很難記得月岡彰。
他只出現一小節,基本上是雜魚,比雜魚還慘的是他娘娘腔又愛漂亮,還三不五時調戲班上帥哥,因此被同學還有作者本人冠上「人妖」之名(日文原文是「おかま」)。但他不做小伏低,反而有股謎之自信——這是我看《大逃殺》小說少數眼睛為之一亮的時刻。不過在一部1999年出版的殺戮小說裡,你知我知,這種人大概不會活太久。果真,場子都還沒坐熱,他就身首分離了,即使之後出現在他人口中,也是憑藉「人妖」這個並不怎樣厲害的印象。
月岡彰是清掃《髒東西》之前,我想先請出小說人物之一。他們不是陳栢青寫的,卻在他的書寫之內,是《髒東西》的系譜,也是陳栢青小說大廈親愛的房客。另外一位,則是《RING:七夜怪談》的山村貞子。不同於月岡彰,山村貞子在「環界」系列是頭號女一,至今仍是女鬼天花板,但有多少人記得貞子在原著裡其實是雙性人,且她需要「被人拷貝」這件事,也與雙性身分息息相關呢?
到了電影裡,他們有更微妙的慘況。《大逃殺》與《RING:七夜怪談》在千禧年左右搬上大銀幕:月岡彰成為普通混混,貞子就是被強暴的女性。不變的是,他們都得死。
死了比活著有用,是90年代性少數的點綴功用;多出來的,跟社會主流有點不一樣,會讓多數人困惑的部分,就剪去,則是進一步的清潔。例如月岡彰的娘跟愛男人,還有貞子的性特徵。這種欲求乾乾淨淨的一點絕操作,正是《髒東西》企圖推翻及重建的。
一個復原到潔本之前的文學工程。
▌無愛也無能繁殖的性
從陳栢青寫的後記中,我們得知《髒東西》原想寫一部同志編年史,且時序本是由古到今,而非如現今層層挖掘般由淺至深。時空上,可辨識約在兩千年後的,有〈世界之胃〉、〈How to Die Young in Tokyo〉、〈羅賓簡史〉三篇,屬於比較標準的同志小說。時間再上溯,就不免混雜歷史的考古,小說成立的標準也突然嚴峻:既得貼合真的舉措、規定,又得從中挖掘虛構的可能;真的不夠真,假的不夠真,都會讓小說不成立。
可以說,《髒東西》全書有個斷崖式的技術難度層級:前四篇〈世界之胃〉、〈How to Die Young in Tokyo〉、〈羅賓簡史〉、〈外出點乩〉一致的較輕鬆,〈晚安,總統先生,晚安〉以降困難度驟增——這也剛好反映在小說的好入口度,前幾篇滑溜順讀,給讀者頭過身就過的輕薄假象,到了後四篇,閱讀門檻忽然抬高。
儘管〈世界之胃〉、〈How to Die Young in Tokyo〉諸篇較好讀,但也值得探究:為何當下此刻,或者說兩千年後的台灣於《髒東西》缺席了?這牽引出的是,同婚過了,然後呢?得不到愛,無法或不想成家的同志,只得跟著資本主義的大部隊走,到泰國三溫暖體驗吃與被吃,去東京找過氣GV男優買春。亞洲第一個同志婚姻合法的國家又怎樣?不被愛的是永遠的第三者、局外人。
因此,當陳栢青把慾望寫得多好多凌厲多全方位用文字重建擬真,其實就是在反寫愛的不存在——例如〈How to Die Young in Tokyo〉把抽插寫成列車穿越月台軌道,「可連那樣,都抵不到最深處/明明已經不會痛了,可為什麼,在更裡面,總有一股癢,搔不到。抵不著/或者我們將永遠在山手線晃蕩。無始終無無明亦無無明盡。」這是陳栢青的文字絕學,也是其正言反說進化而來的喜事喪辦。
▌真話本該的樣子
不過用歡愉寫無愛,在人群中尋找鬼的狂歡,畢竟是陳栢青的舊功夫。〈晚安,總統先生,晚安〉以降諸篇,才是他的新招式,或者用他的話來說,「忍不住想冒犯」的真正對象。
〈晚安,總統先生,晚安〉把愛滋跟老總統關在一起,不可不謂是愛滋狂想,但瘋狂看待疾病的年代需要瘋狂手段,想把愛滋隔絕在島外的政治人物最後跟愛滋患者一室,諷刺非常;〈男人誕生後〉把老戲院的「插片」寫成一個同志的自我證明與全國性的告白,既吹噓又深情(這兩件事竟然可以同時存在,足見陳栢青的功力)。
〈反共之妻俱樂部〉也是同妻俱樂部,將反共義士追求的自由置換成愛男人的自由,最具張力的時刻,儼然諜報小說;〈台灣星戰計畫全史〉雜糅電玩史與黨外運動,設想幫助施明德出逃的,其實是一位名叫艾立恩的跨女(而不是他第一任妻子「艾琳達」),並且在幫助鼎鼎大名的政治犯過程中成就了作為女人的自我。
以上四篇,從黨外到黨國,陳栢青自言全部冒犯了一遍。不過我卻以為陳栢青真正冒犯的地方在於,撬開那些參與、改變歷史事件的主人翁是異性戀或順性別,這個過去顯得理所當然的鎖頭。確實,誰知道歷史會不會像是我們看到《大逃殺》與《七夜怪談》電影版,上了一層自刀的濾鏡呢?小說家有權力想像一個可能史,一個可能被悄悄換置的版本。如同白蘭琪說的,她不說真話,因為她的謊話是真話本該的樣子。
然而,讀者也有權拒絕跟上或跟不上。這反映在陳栢青對敘事聲音的「裝扮」——基本上,《髒東西》全部的小說人物被都套上了「另一個角色身分」,而且越後面的篇章越明顯。例如〈羅賓簡史〉用羅賓與蝙蝠俠的關係/世界觀去錨定主角的身分與在暗戀中的地位,技術上看似就虛寫實,實則是就實寫虛:羅賓與蝙蝠俠的發展是真的存在的,而小說裡的情節不是;如果讀者熟稔並認同羅賓這號DC人物,就能同理主角。這技巧某程度而言,也是迴避,迴避了對兩位角色的經營。
因此,《髒東西》後幾篇中,被套上的角色與敘事者本來身分越遠,小說的力道就越弱。〈羅賓簡史〉正是我認為相對弱的一篇,反之,〈反共之妻俱樂部〉最成功:安娜陳的廣播主持人、同妻、中華民國好公民身分,與胡八一的反共義士、同志、中華民國安全威脅者身分,在故事裡共存不悖,既對話也抗拮,小說因而極具張力。
〈反共之妻俱樂部〉跟〈台灣星戰計畫全史〉應是《髒東西》最具野心,同時最困難的兩篇。後者的完成度雖未達到前者,但〈台灣星戰計畫全史〉是很美很有力量的故事——做女人竟比民主革命困難也更偉大,我願意為這樣的情懷(與謊言)買單。
▌偽第三世界酷兒
雖然我有些小看了《髒東西》前兩篇,但〈世界之胃〉、〈How to Die Young in Tokyo〉拉遠來說,也可解讀成異類與群體的難以和諧。甚至,再拉遠一點,也可把朴相映的《在熙,燒酒,我,還有冰箱裡的藍莓與菸》和安東尼.維斯納.蘇的《餘興派對》放進來討論。
例如朴相映〈大都市的愛情〉與〈遲來的雨季假期〉中主角「映」在曼谷的同志生活,可與〈世界之胃〉無縫接軌,而即使是看似謳歌同志與直女姐妹情的〈在熙〉一篇——說出了「在熙經由我學會同性戀者的生活有時真的很受屈辱,我則經由在熙知道了女人的生活也非常不容易」這般句子——這篇小說其實仍是「映」與在熙輕鬆而決絕的告別姿態。
因為在熙即將結婚,晉身「映」無法到達的新階級。「映」是被遺留下,且無法叫停在熙的人,儘管如此還是要到她的婚禮上主持,好維持「跟群體的和諧」。〈一片石斑,宇宙的味道〉則混雜了二戰的遺緒,讓同志身分變得更複雜:同志是自我認同還是美帝的粉紅清洗呢(台灣某些「左派」應該也會同意這觀點)?
身為柬埔寨移民第二代的安東尼.維斯納.蘇寫的《餘興派對》「最年輕」,卻也最沉重。全書篇章幾乎都寫到了赤色高棉的跨海延續,在《餘興派對》最好的幾篇裡,酷兒身分與大屠殺陰影相疊,卻沒有喪上加喪,反而變成一種想罷黜全世界的憤怒,以及對這種憤怒的自我嘲諷。
其中〈人類發展〉把異類跟群體的辯證推到最高,也是對資本主義勾連婚姻制度侵蝕酷兒的反擊:主角遇到了同為柬埔寨裔的同志情人,對方打算打造一個 App「安全空間」,連結少數族裔、殘障人士、LGBTQ,主角卻有所懷疑,「我思索著,是否有可能對抗谷歌這般龐大的科技巨頭、社會大勢,只為了保持不確定性的價值能夠延續下去。」這個遲疑可以扣回到〈世界之胃〉、〈How to Die Young in Tokyo〉。
無論是年紀最長的陳栢青(抱歉了陳栢青,真的必須在此提到年紀!),次之的朴相映,最年輕(28歲)的安東尼.維斯納.蘇,三人都因為地緣政治加酷兒身分觸碰到了類似的難題:當第一世界的同志過著第一世界的快樂生活,第三世界或者說面對戰爭遺緒(兩韓對立,台海局勢)的同志,已瞥見第一世界的同志生活(甚至同他們一般可結婚了),卻仍需要處理身為第三世界同志的國族乃至離散問題。與此同時,也要煩惱第一世界同志會遇到的問題,例如視覺資本主義帶來的外貌焦慮。
《髒東西》、《在熙,燒酒,我,還有冰箱裡的藍莓與菸》、《餘興派對》三者究竟如何亞洲,怎樣同志,就留給研究者大書特書。回到《髒東西》,這本小說是陳栢青的高難度示範,像是在跳高比賽上一下就給自己設定六公尺這種難度。於小說家,我相信是一個有效的自我證明。
至於對讀者如我的意義是,讀完,我也開始想像月岡彰這樣的娘娘腔贏得了大逃殺比賽,並在多年後成為 GV 男優,出現在〈How to Die Young in Tokyo〉,幹了一名想死的台灣人(「當年我都活下來了,這樣就想死啊。」)。還有,山村貞子其實仍以雙性的身分美美的潛伏著,在大家的錄影帶裡,不,現在都升級成線上了,J·K·羅琳打開雲端連結,就會看見她⋯⋯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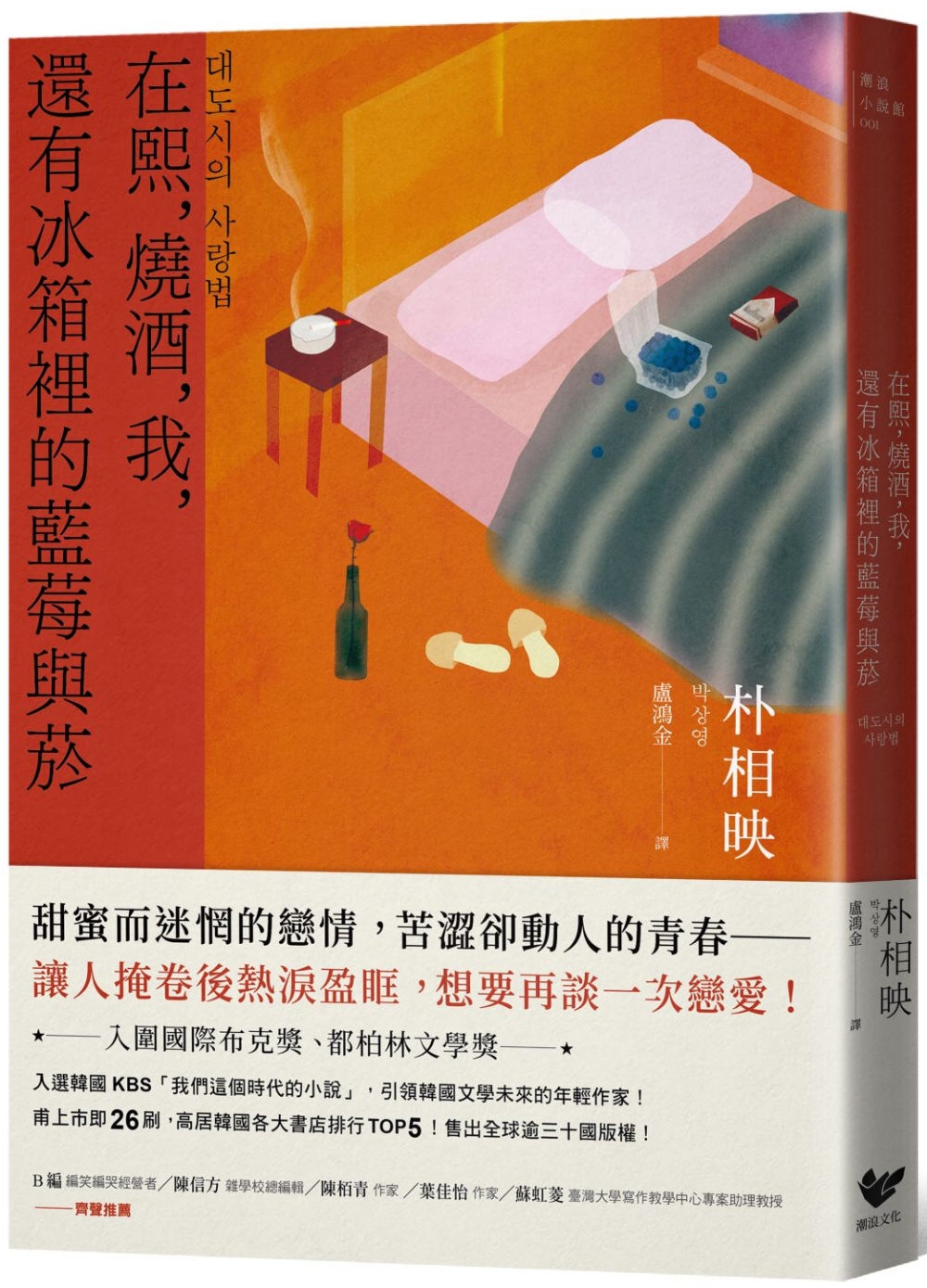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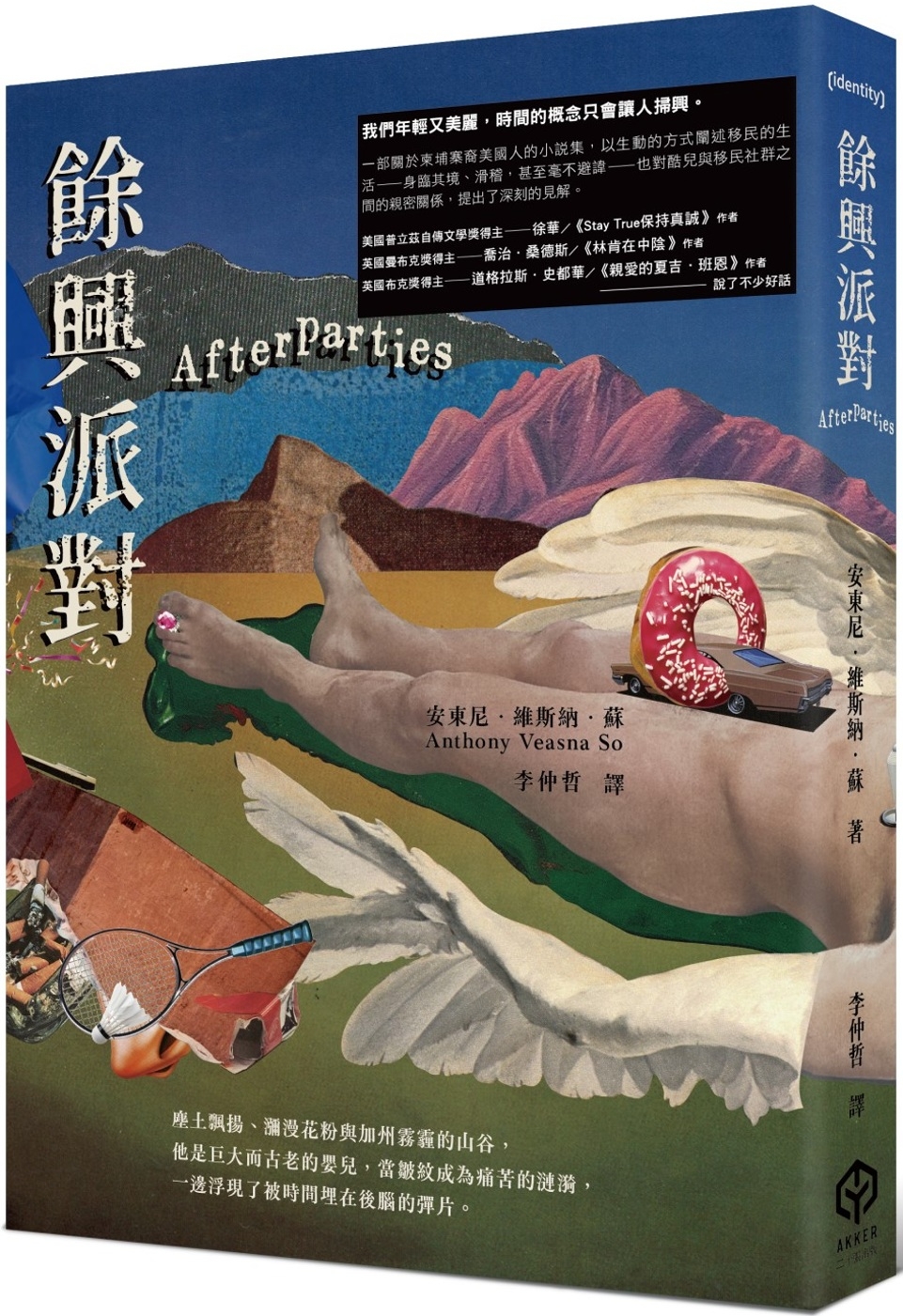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