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OKBOOK高升小故事
BY
大學老師代表
作者簡介
高雄人,定居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現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臺北詩歌節協同策展人,性別組織「伴侶盟」理事。長年於清華大學開授現當代文學與寫作課程。著有詩集《你的聲音充滿時間》、《金烏》等四種,散文集《小火山群》、《以脆弱冶金:楊佳嫻私房閱讀集》等六種。另編有散文選與詩選數種,最新出版為《刺與浪:跨世代台灣同志散文讀本》。
作家的惡夢很多,截稿死線固然使人生不如死(這痛苦是普世的,請參考《死線已是十天前:日本文豪的拖稿地獄實錄》),書籍出版才發現顯眼錯字,沒救的感覺也常使人內心一灰(這尷尬也屬於普世,請——參考你身邊任何一本書)。
拖稿拖過死線變成理由伯,可以轉化為文人傳說,寫錯字,則難登大雅之堂,甚至變成了反向的污點。網路上的萬年哏,說文學科系的人就算災難臨頭還是只會糾正別人「在」「再」寫錯;一開始是嘲弄,意味著文學科系的人沒三小路用,現在文科人也會拿來自嘲了,上街抗議一起去,手拿標語牌「在」「再」要寫對啊。又比如一度看到某些更年輕的讀者或作者,認為在意錯字乃是漢字霸權、華國心態,我明白政治總在區分敵我,分判越簡明越擴大就顯得越純粹絕對,卻可能剝除了事物的複雜脈絡,在意「字有沒有寫對」,我以為是講究文字者的基本功,至於把這件事情上綱到什麼地步、引申為何種含意或階序,當然可以仔細辨明,但未可一概而論。一概而論正是文學的敵人,因為文學總要求我們更寬闊地去想像、更細緻地去理解。
而我,則確實在意「在」「再」是否用對了,在意林「燿」德不要寫成林「耀」德,濫「竽」充數不要寫成濫「魚」充數,是「播」出節目,絕非「撥」出節目,是富有「潛」力,絕非富有「淺」力。
對於錯字的不在意,正折映出對於文字精確性的輕忽,甚至涉及語感欠缺斟酌、口語和書面的混淆。例如,學生寫信來詢問事情,回覆後收到學生的再回覆寫「知道了」,是雍正皇帝批奏摺嗎!書面報告陳述小說內容,「然後白流蘇就回上海了,然後她其實沒有死心在那邊等,然後范柳原真的來找她了」,我是范柳原然後我都想回香港了。事實上我完全同意《語言癌不癌》中何萬順老師的觀點,口頭報告時,「然後」一詞稍稍給予口說和思考上的緩衝,不見得就是語病,我自己緊張起來大概也如此;書面寫作卻是比較有餘裕的,表意乾淨精準,也能顯示出寫作時的用心。
● ○ ● ○ ● ○ ●
王國維自沉於昆明湖,寫成自「沈」於昆明湖,視覺感受就有差異,「沉」更具沒頂感。有時看到寫作者以「轇轕」代「糾葛」,以「髣髴」代「彷彿」,更纏繞,或更飄蕭,未必需要,卻能提供視覺上小坪數的動感。我不常使用僻字,但是我不排斥在讀他人創作時讀到僻字,只要它不是連篇累牘地出現(除非是夏宇又舉行降靈會那就合理),且具有合理的功效,從上下文略可理解其義,兼能點眼(必然的風險:可能變成礙眼)。
究竟是不是錯寫,可能與時代變遷、字音形義衍化有關,古代時通用,現代不通用,學生寫出來時要不要指出來呢?我想還是需要的,順勢補充其變化。另一個情況是,表感嘆與狀聲的字眼「啊」和「啦」,學生多作「阿」和「拉」,「我好難過啊」變成「我好難過阿」,也不是不行,雖然看不太習慣,如果筆下人物大叫「啊啊啊啊啊」寫成「阿阿阿阿阿」,主觀感受上我覺得他真的「狠」驚訝——
讀早期現代文學常能看到的「狠」作「很」用,胡適寫「我不知何故,心裡狠歡喜」(〈三溪路上大雪裡一個紅葉〉,1917),晚二十年出生的張愛玲就困惑了,和姑姑辯論「狠」「很」的用法,姑姑不得不承認這字的意義改變了:「現在沒有人寫『狠好』了。一這樣寫,馬上把自己歸入了周瘦鵑他們那一代。」周瘦鵑是更上一輩的作家了,姑姑身為大都會時髦職業婦女,一想到以「狠」表示「很」會給人過時之感,「果然從此改了」(〈姑姑語錄〉,1945)。現在因為不這麼用了,讀起來反倒帶著陌生化的力量,「狠歡喜」,好像歡喜到皮膚上都出現一條條紅痕了,快樂與痛並存。
不過,我教書生涯中,錯寫而讓我大笑出聲的,是學生交上來的報告把張愛玲〈第一爐香〉寫成〈第一香爐〉了,通篇都是「香爐」。不知道學生是因為也讀過《北港香爐人人插》而搞混呢,還是台灣的中文使用裡,「香爐」比「爐香」常見,所以下意識寫錯,或根本從頭到尾都以為是「香爐」。然而,這確實就是一個早熟少女變成純愛香爐的故事,〈第一香爐〉比起〈第一爐香〉,猶有另一番滋味,創造性的改寫讓人激賞(嗯?)。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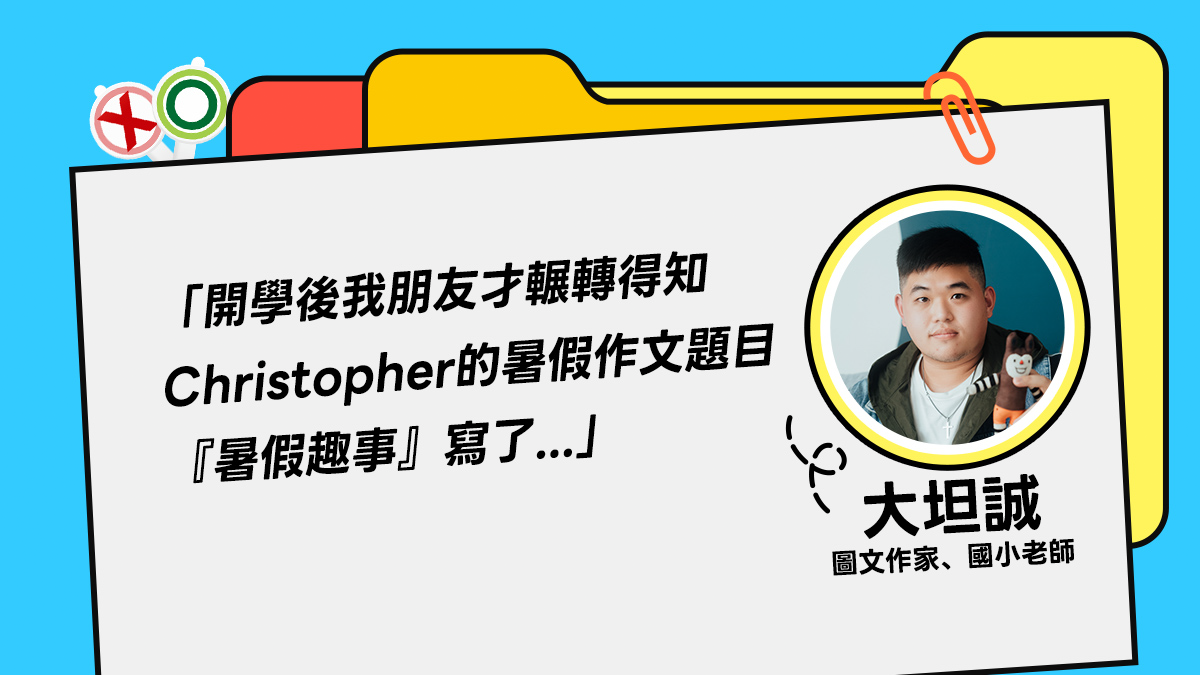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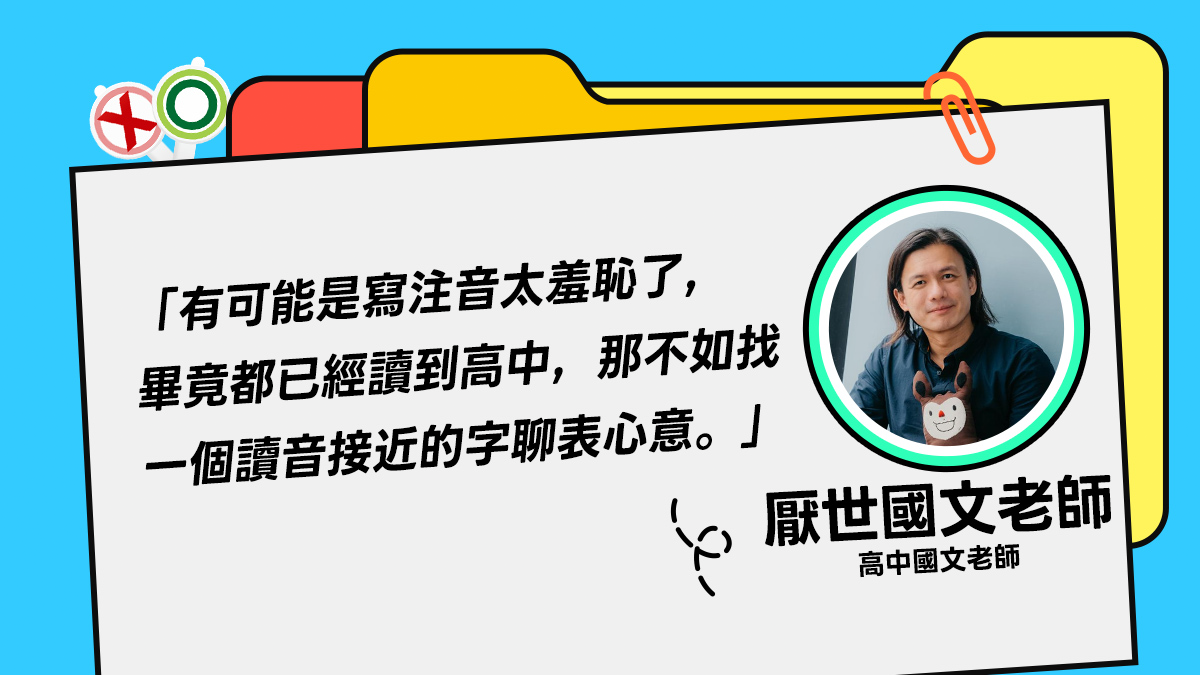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