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譯者又漏譯了,這次是夾在〈第一篇〉和〈第一章〉之間的兩段話,不是原文版美編說明字體的專頁。這一本是馬來西亞英文作家歐大旭(Tash Aw)的回憶錄《碼頭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on a Pier)。
第一段有五句,不是英文,我全看不懂,但知道作者隨後在〈第一章〉有解說,所以我先打個記號,等潤稿階段再處理,結果最後那記號離奇失蹤了,我也忘記有那麼兩段,交稿後經編輯提醒才回頭捕獲。第一段原文一字不漏如下:
Pom mai ben Thai. Watashi no nihongjinde wanaidesu. Jaesonghaeyo, han-guk saram ahniaeyo. Bukan orang Indonesia. Ma Nepali ta hoina.這段下面附有一句英文,我趕緊補譯:「以上用語都能闡述我們不屬於的族裔,都能為我們的歸屬故事起個頭。」
我再讀那段外星文,逐字唸出聲,讀到第二句 Watashi(私) 和 nihongjin(日本人),發現這句是我還沒忘光的日文,不太合語法,但句中有否定詞 nai,猜得出作者想傳達「我不是日本人」,而 Pom mai ben Thai 也出現在正文第一章裡,作者以英文說明為「我不是泰國人」。第三句聽起來像韓語,第四句有「印尼」,第五句含「尼泊爾」。為慎重起見,我向作者求證,整段果然是:
不懂泰、日、韓、印尼、尼泊爾語的英文讀者怎麼辦?有些人能從「以上用語...」那段英文去摸象,有些人上網查一查之後放棄,想必更多人索性跳過。英文裡偶爾出現的外語不構成閱讀障礙,因為英文讀者見慣了外文。
以拼音語言來說,作者借用外語是為了原音呈現,多數是英語人士耳熟能詳的招呼或稱謂,可製造身歷其效境果,相當於以「畫外音」烘托巴黎風情的手風琴聲,或像亞洲人物的進場曲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的〈East Asian riff〉,曲尾還敲個鑼聲強調。電影《星際大戰》的大毛獸丘巴卡(Chewbacca)講著只有韓索羅懂的語言,觀眾不都猜得出牠的意思?
以德文 schnell 為例,發音「虛內爾」,在納粹主題的創作裡常出現,美國圖像文學巨著《鼠族》(Maus)裡用了五次,場景全是納粹士兵在狂吼猶太人「動作快一點」,英語人士受傳媒薰陶,也對這吆喝聲耳熟能詳。在電影改編原著《情,敵》(The Aftermath)中,虛內爾也出現五次之多,故事裡是戰後駐德的英軍驅趕德國野孩子的用語。
英文 Tommy 是外國人對英軍的俗稱,sprechensiedeutsche 是「您說德文」合併為一字,是德語初級班的用語,英美人士多半聽過,但不懂也無妨,從 You 和 good 就猜得出這小孩在拍英軍馬屁。在德文裡,schnell 是日常用語,別無上對下的權勢含義,但在英美,在場有猶太裔時禁講「虛內爾」,理由可想而知。
在《情,敵》原著裡,德語可說是一個配角。戰後英國軍官帶妻兒前來駐德,兒子學德文,從而同情德國老師和孤兒,德文愈講愈溜能象徵兒子的見識和心胸逐日開展,而軍官夫妻倆的德語程度也暗喻兩性溝通,可惜這部分全被電影版刪掉,可能是「電影少了一點什麼」的癥結所在。小譯者我保留少數幾句德文和幾個德文單字,希望給譯本讀者多一份猜謎的趣味和異國情調,以免讀者嫌「好像比電影少了一點什麼。」
西班牙文是美國文學的常客,招呼語「歐拉」(hola)、早安(buenos días)、謝謝(gracias)已成西式美語,幾乎無人不曉,所以文學裡夾雜西語並不構成閱讀障礙,有時候甚至能截長補短。在《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中,少壯漁民視海為對手甚至仇敵,把海洋說成陽性的 el mar。老人情繫汪洋,暱稱大海為陰性的 la mar,是個「會施大恩或吝於施恩,有時也會忍不住撒野作惡」的女人(余光中譯)。英文沒有陰陽之分,非借外語擬人不可,海明威的借用已超出情境釀製的範圍。
作者零星套用一兩個外語,讀者從上下文或許能概略領受。作者也可以在外語後面緊接著解釋,例如華裔混血兒作家丹尼爾.聶(Daniel Nieh)的文化驚悚小說 《Beijing Payback》第一頁出現:Cóngróng ziruò, cóngróng búpò,隨即以英文說明父親這句口頭禪的含義,但唯有懂中國漢語拼音的讀者才知這句是「從容自若,從容不迫」。問題是,作者一口氣飆兩三句又不解釋,而且頻用外語裡的俚語,讀者怎麼辦?
《The Brief and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是當年「必讀」的普立茲獎傑作,聽說英文讀者抱怨裡面穿插太多西班牙語,但我仗著自己大學受過西文老師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兩年的教誨,而且在西語當道的美加西岸混了多年,書買到手急著展閱,讀到 bachatero 這字,不懂,沒關係,先跳過。Ese muchacho está bueno! 我懂,是「這男孩好帥!」Tú eres guapa! 是「妳是個美女!」愈讀愈得意,慶幸沒把西班牙文還給鮑老師。然而,繼續讀下去之後,我發現,故事含太多我沒學過的單字和俚語,查過幾次,手痠就懶得再查了。有時整句西文看不出端倪,跳閱再跳閱,最後,唉,我又不是來補修西班牙文的,《Oscar Wao》遂被我列入「避讀」黑名單。
這小說採美國西裔貧民窟視角,作者朱諾.狄亞茲(Junot Díaz)用了不少西裔土話,有些是像「舞棍」(bachatero)這類多明尼加裔才懂的俚語,連見慣了西語的美國讀者都叫苦,讀來一知半解,直嘆作者簡直是在寫一本雙語小說。「建議讀原文書」的人有膽拿這本跳上台喳呼。台版譯本《阿宅正傳》由擅長詮釋語調的資深譯者何穎怡擔綱,工作期長達一年半,她在譯後記說:「委請精通西文的 Ana Cristina Perez(父親美國人,母親委內瑞拉人)幫忙翻譯成英文。」可見吃足了苦頭,而讀完譯本的人也該明白,翻譯有失有得,你讀這譯本的收穫大於原文版讀者,賺翻了。
除了語音加料外,有些作者更把腦筋動到視覺上。美國名導伍迪艾倫(Woody Allen)早期小說寫得精靈鬼馬,短篇〈庫格瑪斯插曲〉(The Kugelmass Episode)曾獲歐亨利獎,收錄於《副作用》(Side Effects)一書中,故事主人公是個陷入中年危機的已婚男教授,求魔術師把他變進《包法利夫人》小說裡。和情慾噴張的夫人嘗過幾次甜頭後,他竟被變進《西班牙文法補救寶典》裡,被毛茸茸的不規則動詞「tener」(擁有)追著跑。受過西班牙文百變動詞苦毒的讀者見狀能同情他,不懂的讀者光看 tener 有四隻腳加一條短尾巴,也能會心一笑。
華文小說人物取英文名、對話夾雜外語日漸頻繁,以外語調味的例子不在少數。陳思宏新作《第六十七隻穿山甲》從巴黎雨夜揭幕,以法文 Pétrichor 詮釋「風送來雨味」,隨後全以字典解釋的「潮土油」翻譯這字,帶出「聽不懂卻懂」的內涵。吳明益小說《單車失竊記》是一部擺渡多種語言的小說,內容穿插許多台文和日文,較為生難的語句則附拼音和中譯,以兼顧情境和語意,作者不解釋的部分想必讓譯者石岱崙教授(Darryl Sterk)下了不少功夫。
喜劇《歐洲歌唱大賽:火焰傳說》(Eurovision Song Contest: The Story of Fire Saga)在疫情最晦暗的夏天送來一股冰島清風,主題曲〈胡薩灣〉(Húsavik)曾獲奧斯卡提名最佳原創歌曲獎,劇中男女主角以英語詠讚冰島家鄉胡薩灣「鷗啼山吟」、「北極光七彩迸發」的仙氣,歌詞當然要飆幾句冰島語以饗父老(1:26)。但詞曲創作陣容裡,一個是瑞典人,一個是美國人,一個是印度裔,演唱者也是瑞典人,都不通冰島文,於是叫 Google 翻譯,結果想當然爾,其中一句卡卡,歌手 Molly Sandén 模仿冰島語音稱職,但歌詞錯就是錯,騙不過三十萬冰島民眾, 冰島歌手翻唱時不得不聲明:「歌詞稍微更動以合乎冰島語法」。
譯者撞見不懂的外語,可查資料或請教達人,無解才勞動作者,作者不回應時,譯者還得祈禱作者不要亂飆錯誤的外語,因為若照作者的怪奇外語跟著誤譯,錯在誰身上?讀者當然直指翻譯有問題。我曾聽法文譯者抱怨說,英文作品每用法文必錯。《碼頭上的陌生人》各國僑民人來人往,不懂日文的馬來西亞人講一句怪日文不足為奇,韓文、印尼文、尼泊爾文那三句正不正確也非重點,意境讀到就行了,請放下你那查字典的手,繼續和陌生異鄉客雞同鴨講吧。
同時,也請別忘記感謝只懂一種外語、為你超譯的譯者。
Ps. 美國報紙標題也可見外文氾濫的實況。比如,mangia 是義大利文「吃」;下一個標題是西班牙文「我是孩子的媽」。

(圖片來源 / 2024-3-25 紐約時報)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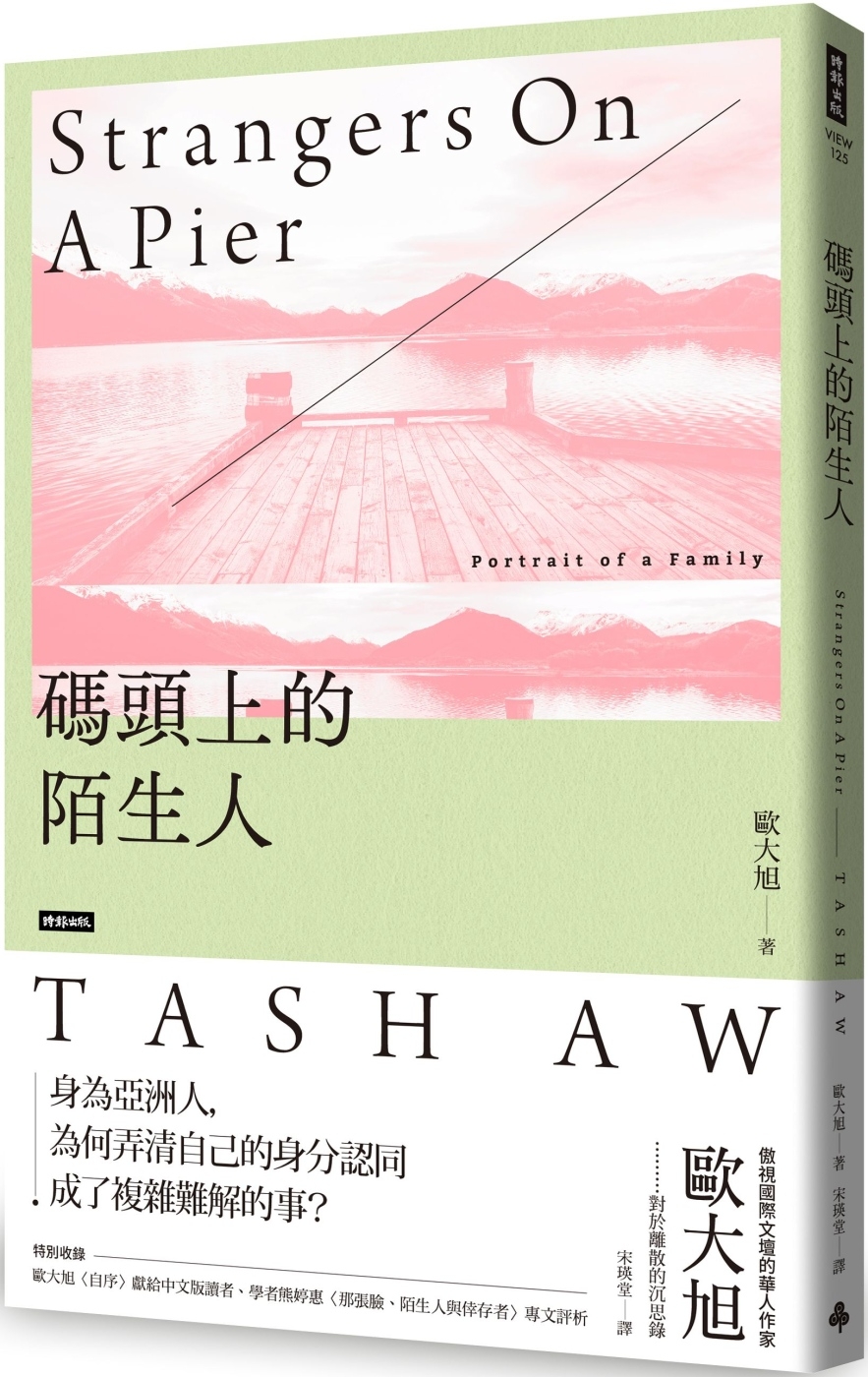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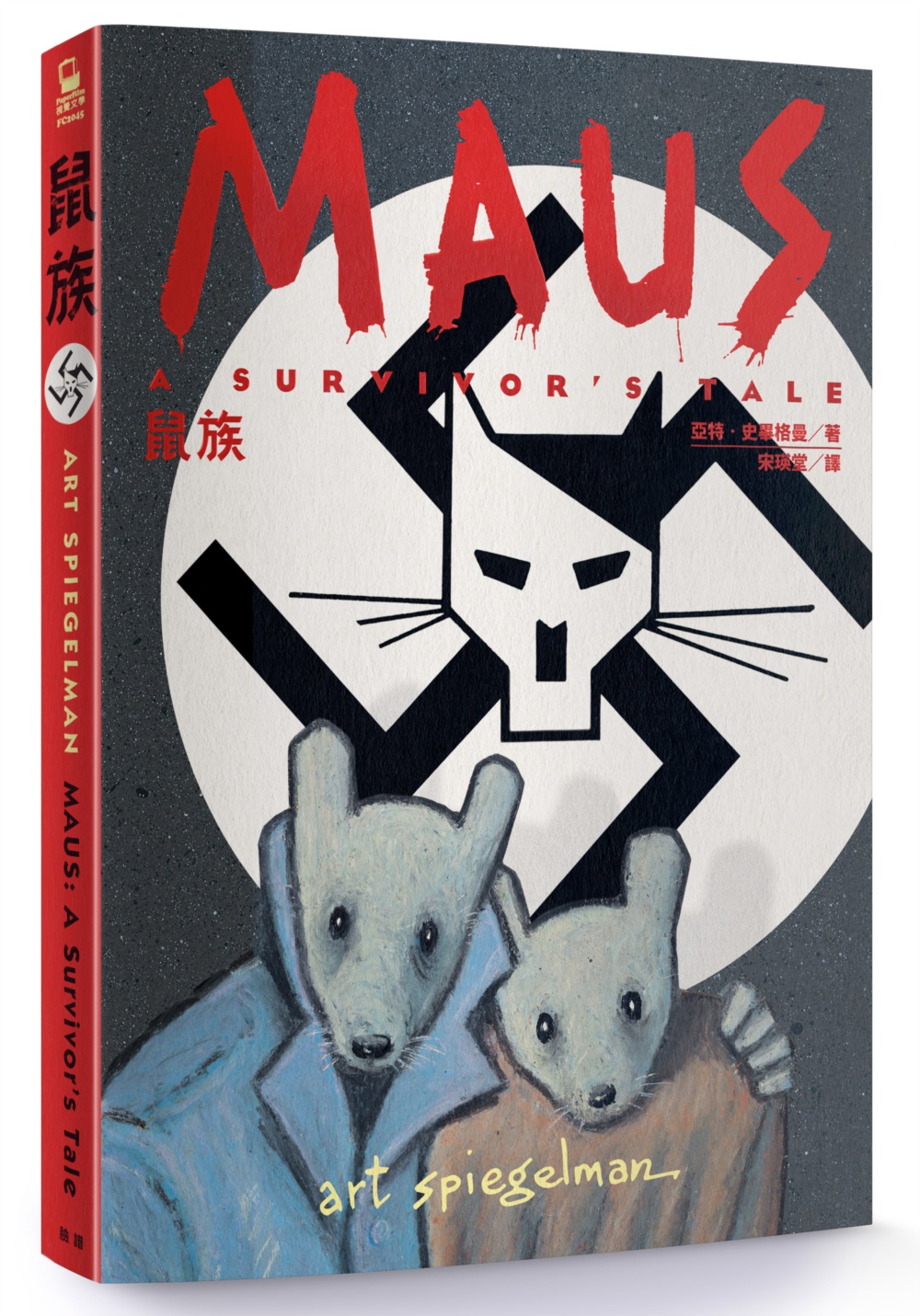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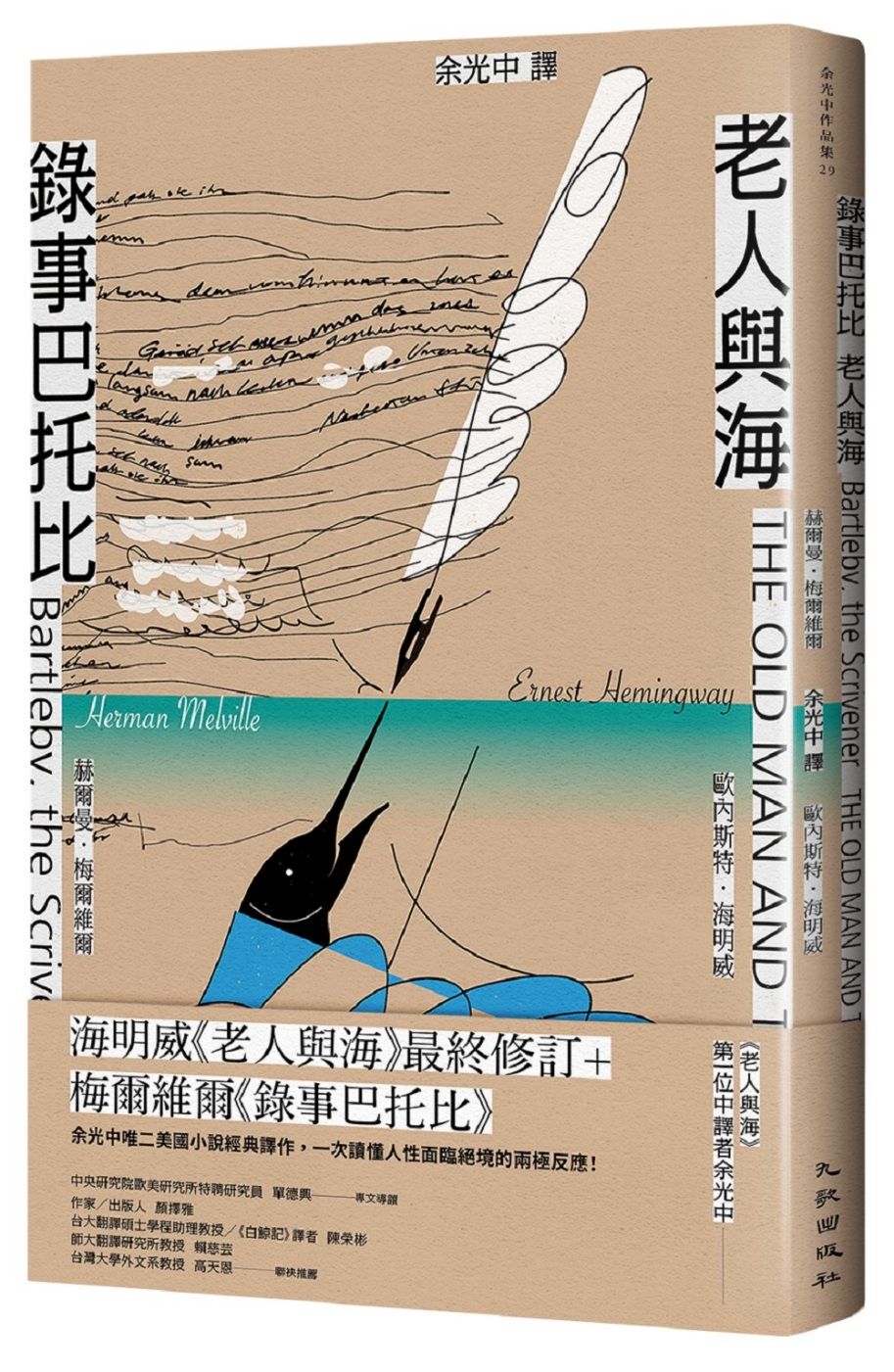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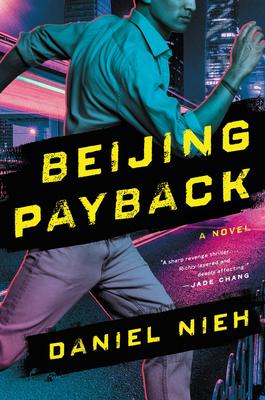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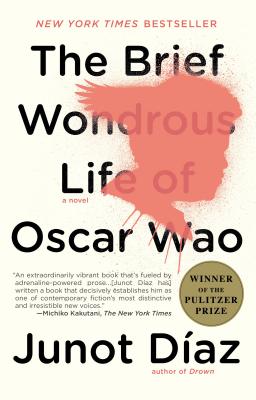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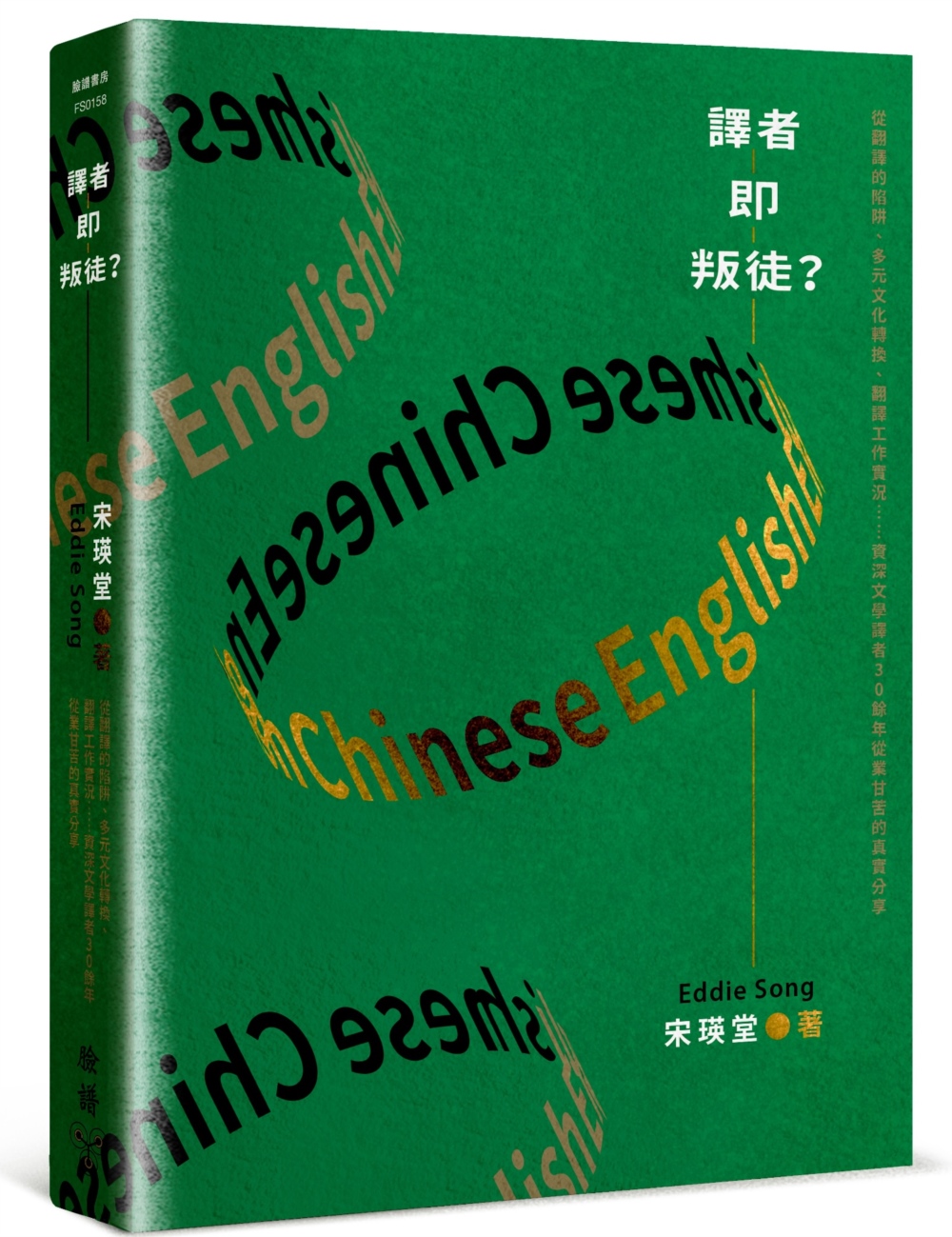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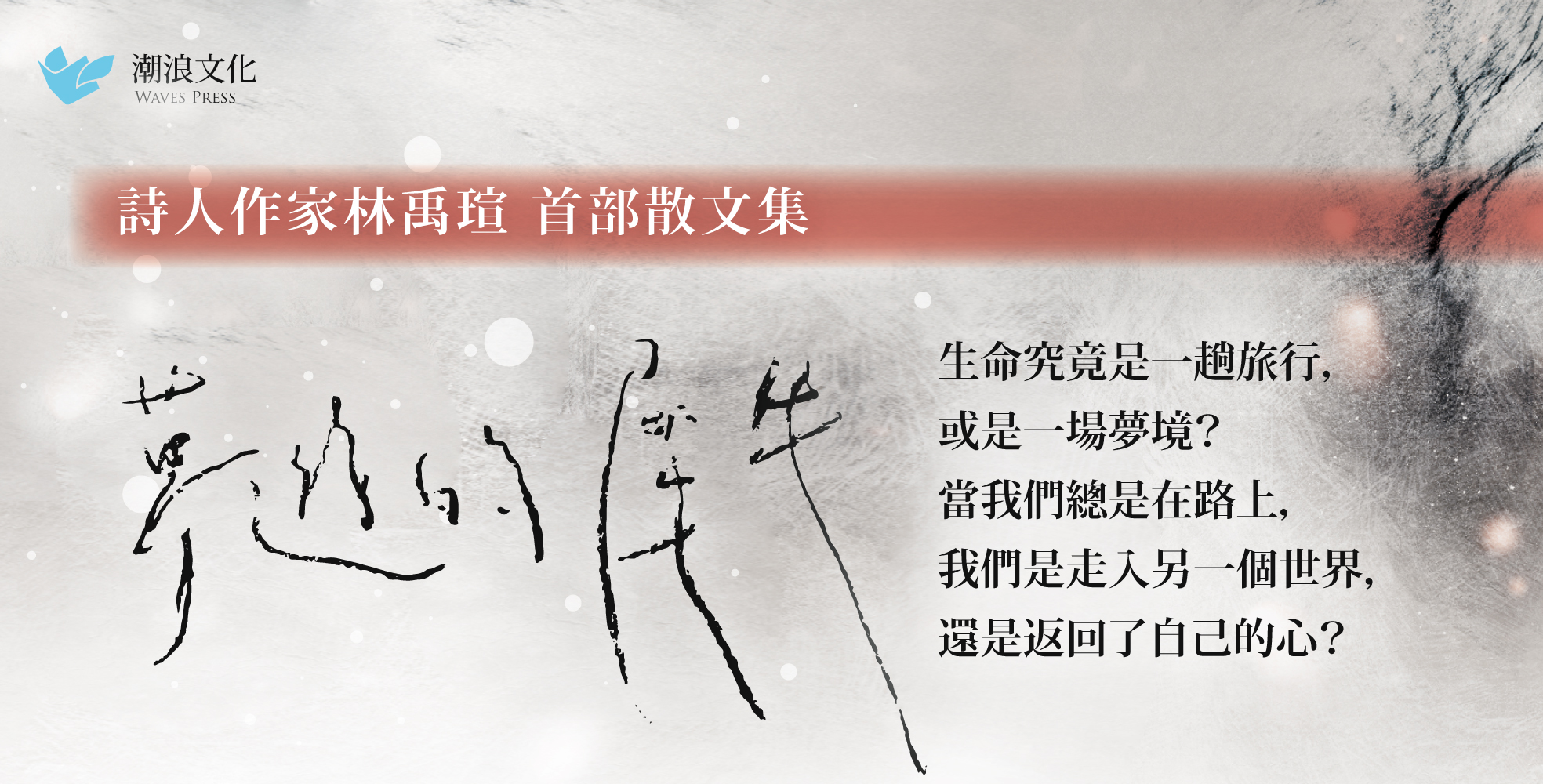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