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從事廣告、設計、印刷等相關產業,一定對Pantone不陌生。這家公司專門開發研究色彩,提供精準色彩選擇,從1963年推出第一本配色系統以來,至今的新版本已超過1114種顏色,顏色之間微小的差異,都可以被準確地辨識並且執行。關於日常的抽象,很可惜的,無法像顏色那樣被歸檔辨認,小愛小恨小情緒之間的微妙轉折,即便人類已經在地球生活過好幾千年,總可以自體增生出更多模糊地帶,關於那種曖昧不明,那種小小的陰暗處,那些是《太陽照不到的地方》,洪茲盈繼2008年短篇小說集《無愛練習》之後,再度遞上十個短篇,更加世故鮮明,書寫十種人生,更加美好安靜、更加寂寞疲憊。
「有時候是你也沒有失去什麼、也沒有得到什麼,就是有個地方被消掉了。」洪茲盈說,除非是經歷巨大的悲傷,例如失戀、失業,不然日常生活中其實有很大部分是沒辦法跟別人大說特說的,可能只是遭遇小小的不順,可能就是一早醒來什麼都不對勁,很多東西都難以跟別人談論,太複雜了以至於難以分享,「我想把無法言說的、太陽照不到的這些記錄下來,有時候打開來看一下,噢,好,然後再蓋回去。」
認為自己是個悲觀的人,即使朋友們都覺得她是諧星,洪茲盈說是個性使然,不管遇到再慘的事,她會加入戲謔、加入笑點,「可以用別的方式去說它,就表示已經過了那個狀態。」看出悲慘世界裡的戲劇化,事情有多慘,故事就能有多好笑,「我不相信世界上有樂觀的人欸,面對挫折說什麼我好了要向前邁進,我就是要爛掉啊!」從日常生活實際歷練來的能力,讓悲觀主義的土壤也能長出諧星,那些上一本書還沒有辦法處理的事情,現在可以正面迎接。
「有些很小的心情是沒有被照顧到的。」她說,即使可以感受悲傷,但常常不知道怎麼去安慰別人,「你也經歷過那個狀態、知道那樣很難受,因為你知道安慰沒有用,所以更難說出口。」不完全悲傷、不完全喜悅,很難精準定義,那就記錄下來吧,「於是我把那個無以名狀放進寫作裡,像是煙,設法把它框起來。」
為了捕捉那些無以名狀,她的祕訣是「快」。「靈感來了要抓住,叫它不要離開,應該是創作人會有的共同經驗。當靈感來,你當下卻無法寫它,只好眼睜睜看它先走。」洪茲盈說自己不是擬大綱式的作家,她習慣先把點子固定住,寧可錯抓不可縱放,即使現階段放不進來,以後也有調度的可能,「今天去某家咖啡店,大概知道我要寫什麼,坐下來先寫寫開頭,有感覺就往下寫,沒感覺就丟掉了。」像是打開某種收音頻道,捕撈經過的、正確的頻率,材料的感覺對了,就可以開始想菜色。

洪茲盈的正職是廣告文案,雖然說現在走感性路線的廣告比較少,不過偶爾也能夠放一些自己的故事,例如桂綸鎂的City Café廣告之一,故事就來自她在花蓮租的信箱。她有時候心情不好會從台北寫信過去,有時候會從國外寄明信片過去,大概一年去收一次信,「做這件事不是出於浪漫,而是想要有個黑洞,一個可以收集東西,並且跟自己有點距離的地方。有點像時空膠囊,隔一段時間再去看,會有個回想的空間,比較有沉澱的感覺。」
書中一篇小說〈末班夜車〉正準備改編成電影,由《到阜陽六百里》的導演鄧勇星執導,劇本仍舊由洪茲盈負責,故事裡的夫妻要被搬上大螢幕,由於篇幅較短,她正努力多加入一些肉,劇本不像小說可以大量地自由調度,要考慮更多現實層面,加上她跟導演希望「電影時間」可以貼近「現實時間」,故事的空間也限制在火車車廂,有點像是做實驗,幾個變因都被控制住了,最後的成果讓人期待。
洪茲盈對於出書這件事很低調,希望不要被任何同事發現,但在《太陽照不到的地方》出版後,有日常生活中認識的、非常內向的人跑來跟她講話,因為有篇故事寫出對方小小的擔憂,這個舉動讓她感動,「寫下這些,希望有一種陪伴的作用,讓一些在這些狀態裡的人,感覺到自己並不那麼孤單。」在那些無以名狀的曖昧裡盡力捕捉煙霧,在那些太陽照不到的地方,也許還留有溫度。
〔洪茲盈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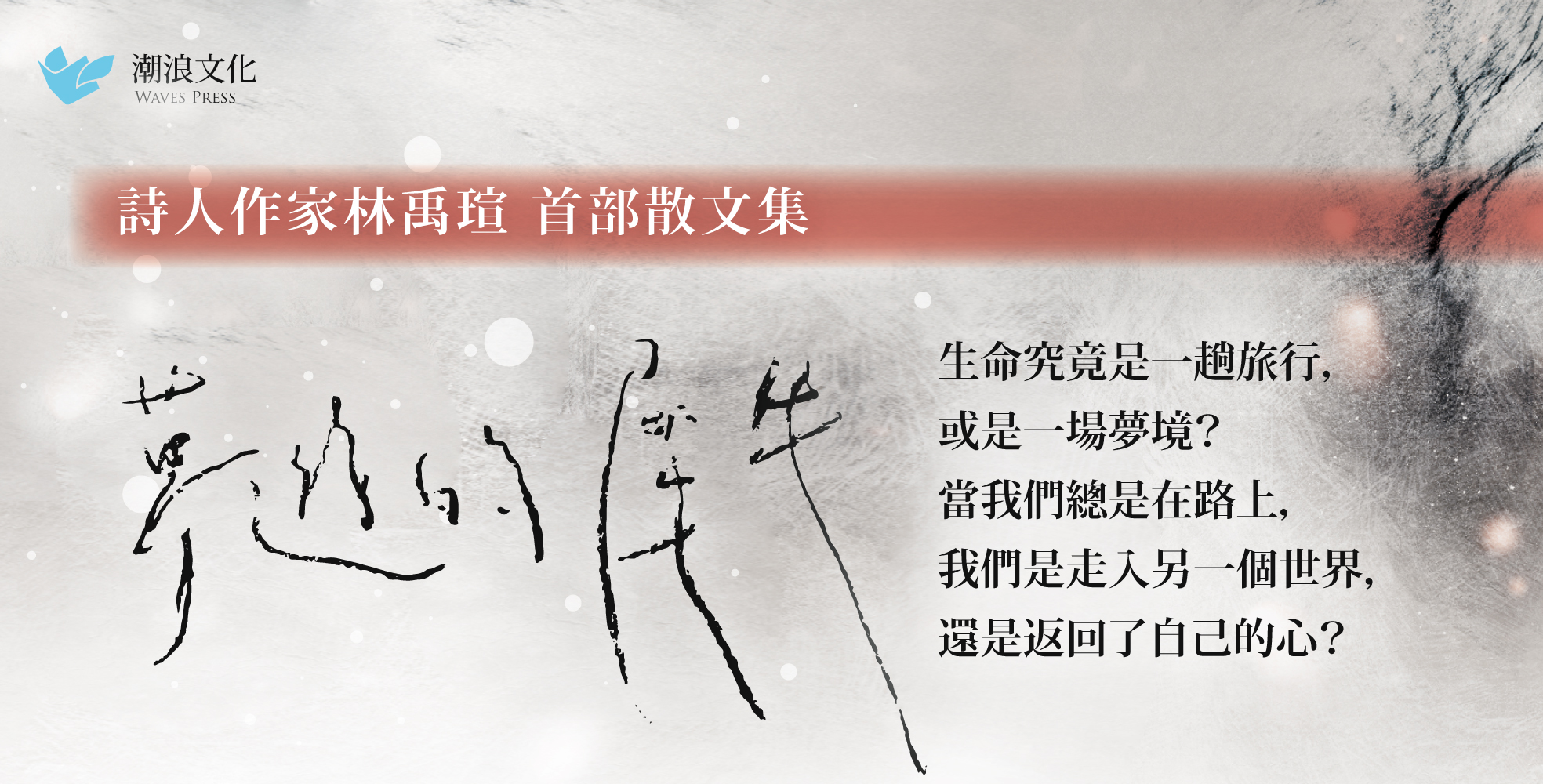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