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常,我們評價媒體人成不成功,是看影響力。用這個標準,李怡是非常成功的。
哪一份華文刊物像他主編的《七十年代》(一九八四年改名《九十年代》)那樣,連連以獨家驚動兩岸三地?它最早披露《雷震回憶錄》,最早預言鄧小平復出,也最早挑起九七議題。
在戒嚴時期的台灣,黨外雜誌至少書報攤買得到,《七十年代》卻只能偷偷夾帶進海關。不過,拜黨外雜誌經常引述之賜,許多沒看過《七十年代》的台灣人都知道它的存在。
 《九十年代》雜誌,原名《七十年代》,是一份頗具影響力的中文政治、歷史雜誌,由李怡創辦,創刊於1970年2月香港。初期接受中共的資助,1981年脫離左派,1984年更名為《九十年代》。( Source:維基百科 )
《九十年代》雜誌,原名《七十年代》,是一份頗具影響力的中文政治、歷史雜誌,由李怡創辦,創刊於1970年2月香港。初期接受中共的資助,1981年脫離左派,1984年更名為《九十年代》。( Source:維基百科 )

還有李怡那隻筆。六四後,北京官方檢討「動亂的醞釀」,就特別挑明是他在《信報》的文章。他論析文革的書有英、日、法、西班牙文版,寫香港的書也多種都有日文版。時論結集頻頻受到外國出版社青睞,這在華文世界絕對是空前,也極可能絕後。
他那麼成功,書名《失敗者回憶錄》就有必要解釋了。他從前也寫過不少回憶文章,但第一次以失敗者自居,卻要等到《蘋果日報》「世道人生」專欄最後一篇,文中說他不打算再寫時評:「將向愛護我的讀友,細說我一路走來的失敗的人生。」刊出日期是二○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九天後他就飛來台灣了。
所以,這種自我認定,必須跟他移居台灣的決定一起看。決定的背後,當然是香港自由空間緊縮。李怡過世後,有人寫說他「一生追求自由」。但光看回憶錄開頭,我們就知他本人並不做如是想。開頭寫的是一九七○年三月的遭遇,那是《七十年代》創刊第二個月。成功男性回憶事業起飛,印象鮮明的不都是意氣昂揚那一面?怎麼李怡卻大寫特寫自己的軟弱?
當時,他妻子正被隔離審查。文革期間,隔離審查把人打死是常有的事。妻子被挑中,只因造反派想逼她供出李怡是特務。都經歷這麼離譜的事了,怎麼李怡還繼續留在左派陣營?
看來他主編的《七十年代》對中共極有價值,不管在宣傳還是情報上面。這些都是第一次披露。那段歲月的李怡身在自由中,卻不知自由可貴,只因自由在當時的香港就像空氣和水。李怡一生,正好見證香港自由是如何「無可奈何花落去」。
這故事李怡特別有資格講。他當年崛起,個人因素當然是他獨具編輯天才,但環境因素也一樣重要:台灣缺乏的自由,香港多到滿出來。台灣當年雖位居冷戰前線,卻因為言論管控,不可能進行思想上的冷戰。思想上的前線只可能在香港。
正是拜思想冷戰之賜,《七十年代》才可能立足於香港。它一開始屬於左派陣營,其資金、行銷、印刷都是黨國張羅,方向也符合黨國需求。它報導美國民權運動,美其名是介紹進步思潮,骨子裡卻是暗示美帝就是紙老虎。它報導國民黨如何做票,如何把手伸進台大哲學系,也是為了台灣重回祖國懷抱,不是為了台灣人當家作主。
到了文革晚期,《七十年代》每期出刊都要事先經過審查。李怡並非「一生追求自由」,這是另一例證。
真的開始追求自由,是一九七九年,四十三歲了。脫離左派,完全獨立則是一九八一年。之後他才成為今天我們所熟悉的李怡:最洞知中共思惟的銳眼,最頑強抵抗暴政的脊梁。
脫離左派的過程也是本書第一次披露。嚴格說起來,所謂的思想冷戰前線也不是劃在《七十年代》、《今日世界》等左右刊物之間,而是穿過李怡這種知識人的靈魂。台灣沒發生過思想冷戰的損失也正在此:台灣的左派都是跟中共「因誤會而戀愛」沒多久就被「白色恐怖」了,所以缺乏「因了解而分開」所帶來的真知灼見。
這種真知灼見,在書中真是不勝枚舉。一例:李怡主張只要〈中英聯合公報〉(一九八四年)之前香港有百萬人上街,中共是不見得敢收回香港的。那民族大義怎麼辦?李怡援引中蘇邊界的前例,說這對中共來說只是換說法的問題。情勢需要的話,「自古以來中國領土」完全可以被「歷史遺留問題」取代。
 《中英聯合聲明》是中英兩國於1984年共同發表的一份聲明,承諾香港現行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在「一國兩制」下享有不同於中國內地的自由與司法獨立。(圖片來源:BBC)
《中英聯合聲明》是中英兩國於1984年共同發表的一份聲明,承諾香港現行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在「一國兩制」下享有不同於中國內地的自由與司法獨立。(圖片來源:BBC)

李怡脫左之前,需要重新認識中國。這裡,他特別著墨梁麗儀對他的影響。別人追悼亡妻都是回味共處的美好,李怡卻獨獨難忘聚少離多的苦澀。的確,李梁姻緣最奇特的一點,就是青春年華長期相隔天涯。兩人是十六歲相識,十九歲魚雁往返開始戀愛,二十四歲結婚,終於住到同一屋簷下卻要等到三十八歲。
再來,別人都是感念「顧我無衣搜藎篋」之類的辛苦持家,李怡感念的卻是精神成長。大學落榜後的關懷來自她。文筆得以精進,是跟她頻繁通信。他最重要的兩種筆名都跟她有關,「李怡」跟麗儀同音,「齊辛」則代表夫妻齊心。他因為政治立場需要忍受圍剿,益加感謝亡妻對他的始終信任。
李怡相貌英俊,風度翩翩,很有女人緣是一定的。書中描述亡妻「對我與異性朋友來往從不過問」,卻沒寫是哪一種異性朋友。喪妻那年李怡七十二歲:「她離去後,我在困難時刻,仍然會在冥冥中聽到(她支持我的)這聲音,於是挺起身繼續走自己的路。」
數一數,他與亡妻天人永隔剛好十四年,正是婚後兩地相思的年數。也許,老早習慣天各一方的他們並不曾被死亡真正分開。
許多人惋惜李怡沒寫完回憶錄就離去。我卻不這麼看。他儘管脫左,奉獻精神卻始終如一,總覺得自己做的不夠。他無論活多久,都會有作品沒寫完的。這本書已寫完他最重視的二○一九年抗爭那部分,某種意義算是寫完了。
重點是,我們讀到年輕人勇武帶給他的震撼,就更了解他為何會在八十五歲之齡,突然以失敗者自況,為何他要把自己三十四歲的軟弱放在最開頭。他用首尾對比,來襯托他對今日香港感到的自咎。這種自咎之情貫穿全書。
新一代香港人會不會把過往的自由忘得一乾二淨?李怡絕對不希望這種事發生,才會在人生最後十八個月移居台灣,為了好好寫書。
飛來台灣是二○二一年四月九日,原本指望還可以回去,帶來行李不多。兩個月後壹傳媒高層大搜捕,他曾一度激動想飛回香港,是別人勸退。十一月底,心臟問題緊急住院。這些,都更加堅定他寫回憶錄的意志。所以他就持續地寫,直到最後倒下。
到頭來,他終究無法重回香港。但既然他以「唯有勇氣才是永恆」為本書主旨,那表示他把成敗看很小,生死也看很小。他把他的證言,他的自咎,他對二○一九抗爭世代的敬佩,都寫進這本書了。
更重要的是他的期許,他的未了心願。我們在台灣把這本書編好,付梓,只算是幫他完成他未了心願的一部分。其餘,只能等有勇氣的香港人去替他完成。一代完成不了,就把勇氣傳遞給更年輕的一代,像李怡那樣。
作者簡介
2014年金鼎獎雜誌專欄類、2018年九歌年度散文獎得主。
著有《愛還是錯愛》(親子天下,2015年)、《向康德學習請客吃飯》(印刻,2016年)、《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天下雜誌,2018年)。譯有珍.奧斯汀《理性與感性》(印刻,2017年)。編有《余英時評政治現實》(印刻,2022年)。
2002年創辦雅言出版公司。
【OKAPI專訪】雅言文化發行人顏擇雅:我不跟著流行讀書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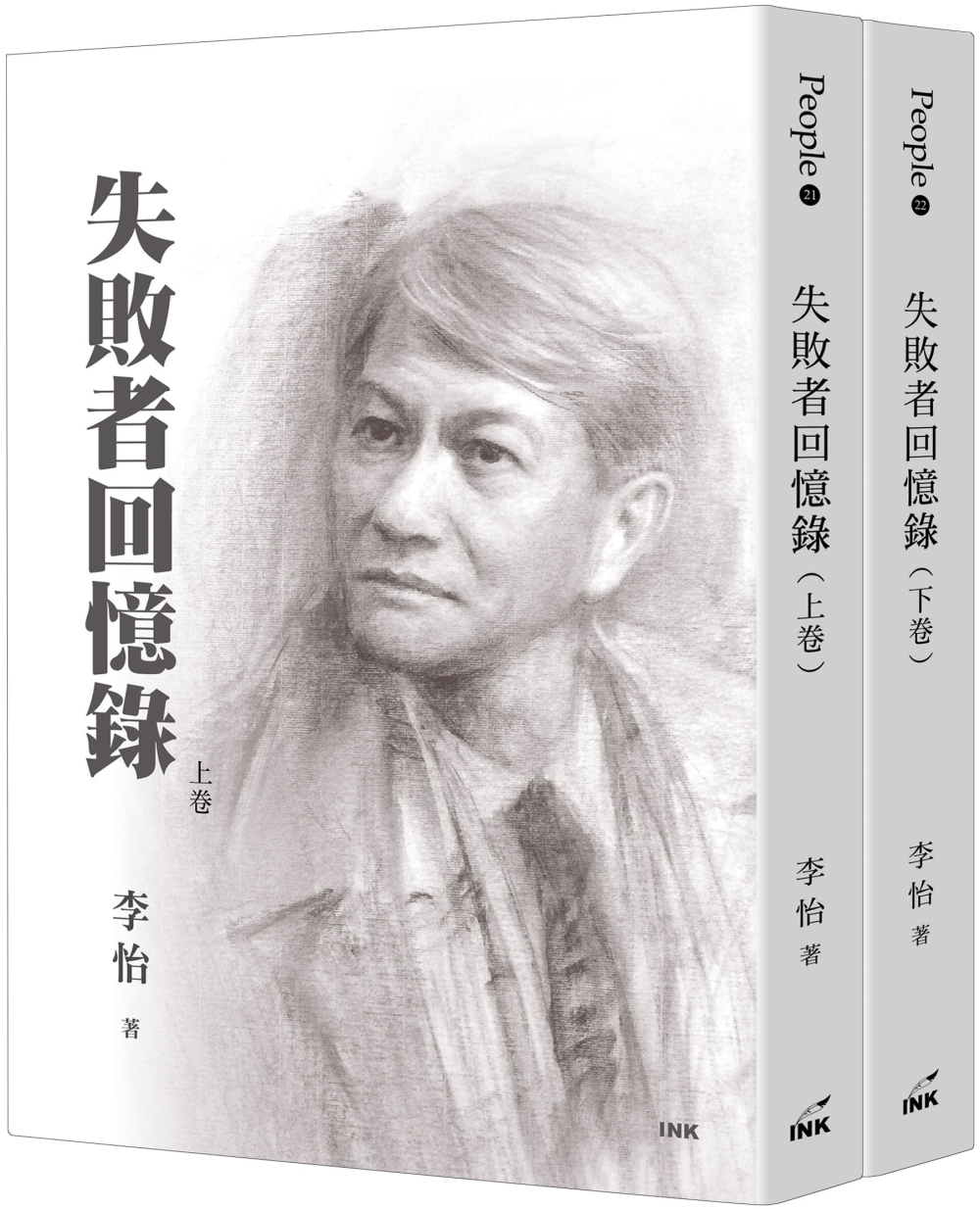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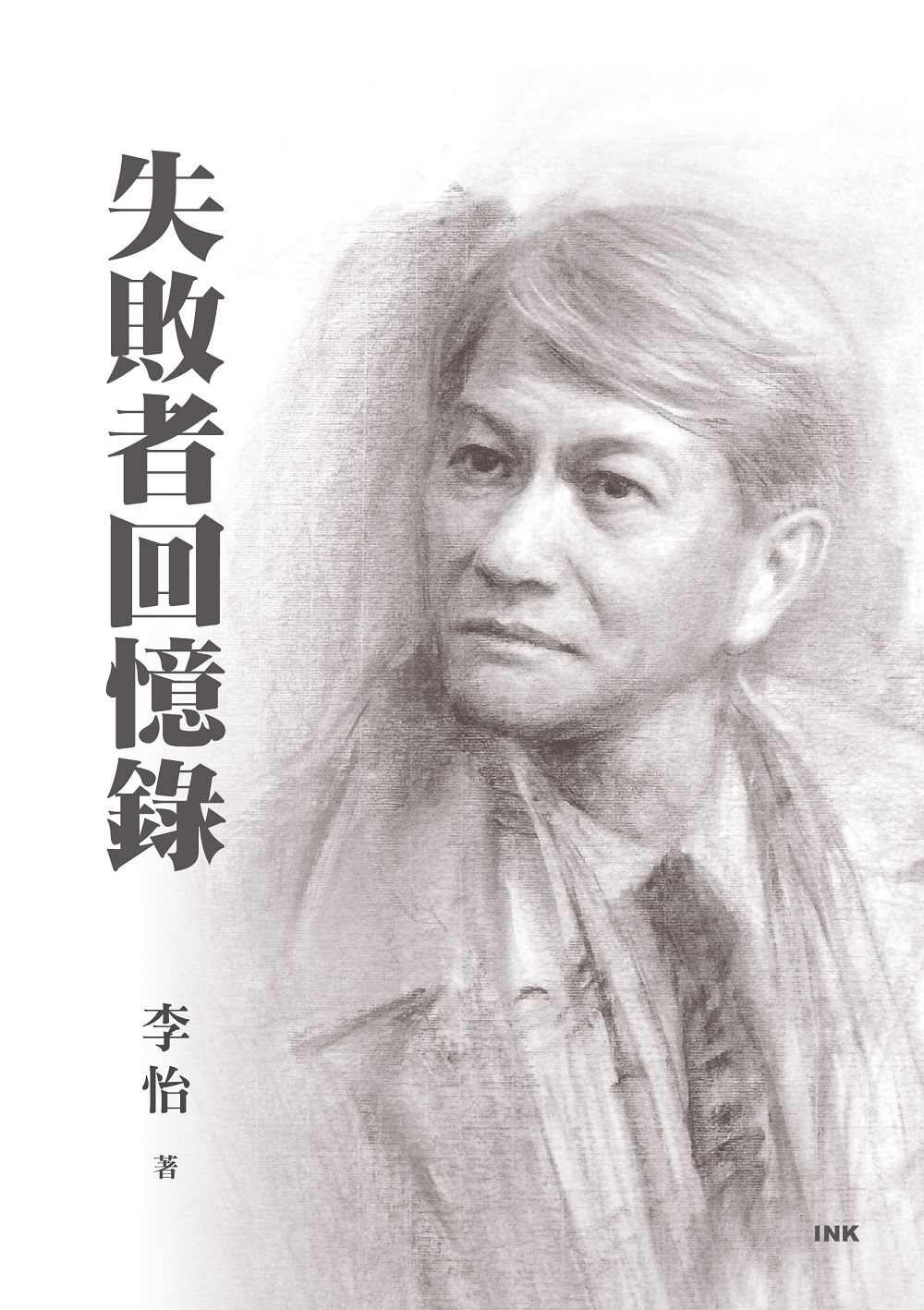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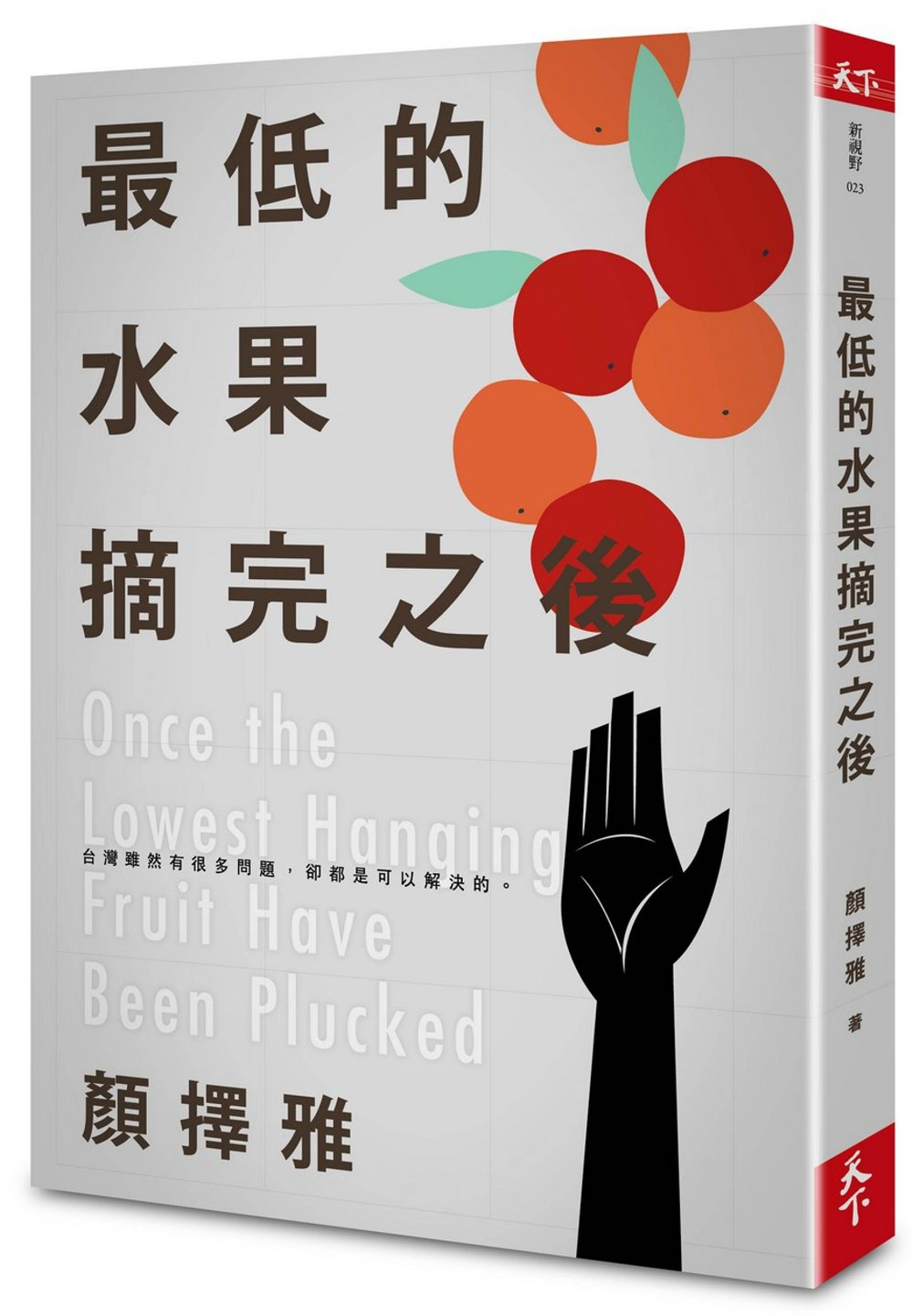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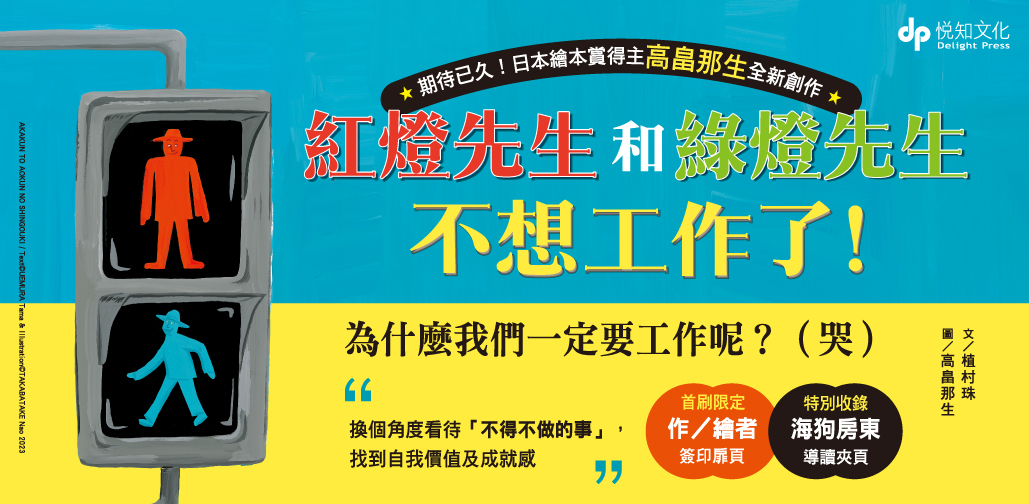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